文:水木史记
编辑:水木史记
——《前言》——
他死的时候,手里握着一瓶冰镇可乐。
在此之前,他制造过手榴弹,操盘过黄金,主导过新中国的第一条可乐生产线。
这不是小说,这是他的真实人生。
——《壹》——
一个大学生的叛逆选择
他是工程师,却不去造桥,他制造炸药、藏身上海、手握自制的发报机,躲在废弃厂房里发报,目标:国民党警察局对面的特务站。
1925年,他还在上海大学读土木工程。
书包里有课本,也有一把匕首,他说,“土木没什么用,炸掉比建起来更快。”他不是玩笑,他自己配炸药,用的是实验课偷出来的硫磺。
成分严格按比例配比,还做了几次试爆。
爆炸成功那天,他兴奋到一夜没睡,第二天,他就把配方送进了工人武装队,这个大学生,成了起义现场最危险的那个人。
负责“火力支援”,也负责“临时撤退路线规划”。
这不是浪漫主义,那时候,街上是警察,屋里是线人,情报得靠人送,一次送信的工人被抓,拷问三个小时后跳楼。
他亲自把人从巷子里拖出来,脚骨已经碎了。
从那一刻起,他知道:光靠人,活不久,得靠机器,他开始琢磨“无线电”,没人教,他就去租书,英文看不懂,他抄单词,一页页翻。
他说:“字典看完了,才能看懂书。”
他把一本英文无线电教材背下来了,边学边画电路图,两个月后,他造出一部可以收报的“机器”,外壳是各种零件拼出来的,线路是铜丝缠的。
就是它,改变了整个上海特工战局。
周恩来看了之后,只说了一句话:“你就负责这个。”他点头,转天被调入中央特科,这是1927年。
——《贰》——
一个特工工程师的极限试验
当时,中国还没有一台成型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技术封锁,书买不到,材料也没人卖,“不让你造,偏要造。”他一句话就定了这个死局。
他跑遍废品市场,找来旧电容、旧变压器,回去就拆。
试了七次,第八次点火,线路短路烧了半边电板,他咳着烟尘说:“至少今天烧得比昨天慢。”没人理解他,也没人敢靠近他。
屋里天天冒火光,墙上贴着英文草稿纸,一地铁丝和玻璃渣。
有人说他疯了,他说自己是“搬砖的”,但砖是电波,房子是战争要用的秘密武器,三个月后,他造出中国第一台可以双向收发的无线电通讯设备。
收报准确率达到98%,试验地点在一间防空洞里,深夜试报,北京站成功接收。
同年,他被派到苏联,他走得很急,只带了一本手写的技术手册,还有一页未完的电路图,到了苏联,他直接住进实验室,不说俄语,只用图纸交流。
实验室主任看了三天,说:“这人比我们还懂。”
他写了两篇论文,一篇讲天线结构,一篇讲频率干扰,被列入苏联无线电专家名单,这是他们的荣誉,但对他来说只是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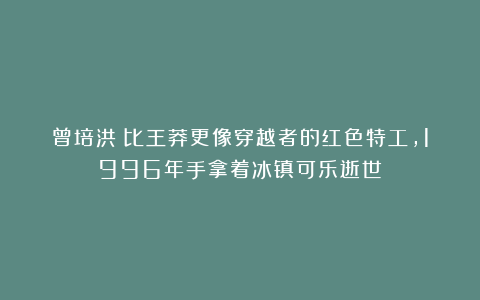
他还做了一件没人理解的事。
他在莫斯科地下黑市买了五种黄金合金样本,烧成粉末,用短波照射,“金属在电波里暴露弱点,人也一样。”他说,别人不懂,他不解释。
这个电波特工在苏联六年,留下了三个发报站模型和一套情报加密规范。
回国时,他只带回一台小型收发设备和一本自编教材,名字就叫《发信菱形天线》,这是后来新中国情报战的根基之一。
——《叁》——
一支军队的后勤被他撑起来了
他到延安的第一天,就问:“这里有铁吗?”没人理解,他自己去找,找到的是一段废旧铁轨,生锈、断裂,被丢在山沟里。
他笑了,说:“够用了。”当时八路军最缺的,不是人,是枪。
枪管炸膛、子弹打光,有人上战场带着棍子和信仰,他看了之后,把手卷起,说,“那是等死,不是打仗。”
他带着一群木匠、铁匠和学生,把铁轨锯开、烧红、拉丝。
做出一批“无名氏马步枪”,没编号、没铭牌,但能打得响,能打得准,每做一支枪,都要打三发子弹测试,失败的枪拆掉重做。
失败的弹头倒回锅里重熔,他说:“打一枪少一颗铁,做错一发子弹,就是一个战士倒下。”
他干了将近五年,做出一万多支枪,220万发子弹,他说,“我不做英雄,我只做工具。”但这不是全部,他还搞出了一种掷弹筒。
不是图纸画出来的,是靠炸药试出来的。
他蹲在院子里,一次次试爆,有一次炸药提前引燃,他的手掌被炸出裂口,血流一地,他只说一句:“还不够远,要再飞五米。”
第二天又继续,有人说他疯,他反问:“打仗要的不就是疯子?”
就是这些“疯子”造出的掷弹筒,在华北战场上撑过了一个又一个前线据点,他不说感谢,他只说:“别再给我废铁了,能不能来点钢。”
——《肆》——
不是外贸部长,是操盘手
1970年代,他已经六十多岁,头发花白,走路也慢了,但他眼睛还亮,当他坐上外贸部长的位置,第一句话不是“搞经济”,而是:“中国有多少黄金?”
没人答得上,他自己去查,翻报表、进金库、挖十年前的合同。
他一边查账,一边问:“为什么还不进期货?”没人理解,他解释也不多,三个月后,他亲自下单,买入大批黄金和铜期货。
有人说:“这是赌博。”他说:“战争不是赌命?这是赌国家命运。”
那年,中国还没有期货法,也没有交易团队,他自己建了一个团队,十几个人,一间小屋,三台算盘,没人敢报名字,全靠代号通信。
他用这些操作,赚回30亿美元外汇,是当年中国出口总额的83%。
没人知道这钱怎么赚来的,只知道账上突然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这还没完,1979年,他接待了一个美国团队,是可口可乐。
他让他们带样品,拿起来,喝了一口,说:“这个,中国人会喜欢。”
会场一片寂静,他说:“我们可以引进,不光是配方,还有机器,还有生产线。”别人反对,说这不是糖水,是美国文化。
他说:“这是经济,是工业,是市场,不是情绪。”
他说完,把那瓶可乐放进冰箱,谁也没动,第二年,中国第一条现代化饮料生产线落地,可口可乐成了第一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
这件事让很多人不理解。
他不解释,他只说了一句话:“你不站在明天看今天,就永远只能过昨天的日子。”多年后,他去世,手里握着的,是一瓶冰镇可乐。
那不是偶然,是选择,是一个工程师的注脚,也是一个时代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