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红与黑:
一个天才的沉沦与不朽
作者︱万伟恒
当雍正五年的冬天,江宁织造衙门的朱漆大门被贴上交叉的封条时,那个躲在乳母身后、睁着惊恐眼睛的十三岁少年还无法理解,曹氏家族自曾祖母孙氏以来积累的百年荣华,竟会在顷刻间灰飞烟灭。曹雪芹——这个当时还叫做曹霑的孩子——注定要用一生的颠沛流离来消化这场浩劫,最终在贫病交加中将家族记忆炼就成了照耀千古的文学奇珍。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这场毁灭性的抄家,意外地为中华文明催生出了一部空前绝后的伟大小说。
康熙二十三年春,苏州织造李煦的密折中首次出现了关于曹寅的记载:”奴才妹丈曹寅,蒙皇上天恩,现管江宁织造…”这看似平常的公文背后,隐藏着一个包衣奴才家族崛起的秘密。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作为康熙帝的乳母,为家族赢得了”从龙入关”的特殊地位。当这位满洲皇帝在1684年南巡时,特意在江宁织造署召见年迈的孙氏,当面称她”此吾家老人也”,并赐”萱瑞堂”匾额。皇权与奴仆之间这种看似温情的关系,为曹家三代四人把持江宁织造这一肥缺长达六十年奠定了基础。
曹寅时代的江宁织造署堪称东南文化中心。这位兼任两淮巡盐御史的织造大人,不仅四次接驾康熙南巡,更主持刊刻《全唐诗》,收藏宋元书画真迹,与朱彝尊、尤侗等文坛巨擘诗酒唱和。现藏于北京故宫的《楝亭图咏》四卷,记录着当时名流对曹氏家族的赞美。康熙五十年,曹寅在扬州书局校勘《佩文韵府》时染疟疾去世,康熙帝特命其子曹颙继任,并亲口叮嘱:”尔父效力年久,朕深悉知。”这种超越常规的皇恩,埋下了日后政治风险的种子。
雍正元年的政治清洗如秋风扫落叶。新皇帝对康熙晚年的财政亏空展开彻查,而曹家历年接驾造成的巨额亏空达数百万两之巨。更致命的是,曹家与雍正的政敌胤禩集团过从甚密。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谕以”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为由,将曹頫革职抄家。档案记载,这次抄家仅得”银数两,钱数千,质票值千金而已”。曾经堆满宋版书的藏书楼,转眼间只剩下贴着封条的空荡书架。
乾隆九年的某个雪夜,北京蒜市口十七间半老宅里,三十岁的曹雪芹裹着破旧的毡毯,就着微弱的油灯重读祖父的诗集。窗外呼啸的北风让他想起南京旧宅的暖阁,那里曾有西洋自鸣钟整点报时的清脆声响。而今全家靠着”鬻画沽酒”度日,连他最珍视的《楝亭夜话图》也早已典当。这种天壤之别的生活体验,正在他心中酝酿着一场文学革命。
曹雪芹的落魄轨迹在清代文人笔记中留下零星记载。敦诚《寄怀曹雪芹》诗注提到:”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裕瑞《枣窗闲笔》则记载:”其人(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这些片段拼凑出一个从贵公子沦为市井文人的形象。他在右翼宗学当过差,结识了敦敏、敦诚兄弟;据说还在南京两江总督尹继善府中做过幕宾,但始终无法重现家族昔日的辉煌。
西郊黄叶村的岁月是曹雪芹创作的关键期。张宜泉《题芹溪居士》诗云:”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在这里,他将记忆中的大观园与眼前的破草堂奇妙地融合。现存《废艺斋集稿》残篇显示,这位落魄文人不仅精通绘画、扎风筝,还研究编织、印染等工艺。这种对物质文化的痴迷,在《红楼梦》中转化为对服饰、饮食、建筑近乎人类学式的精细描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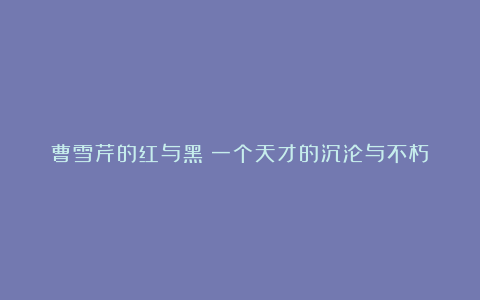
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开始在北京文人圈流传。这部”字字看来皆是血”的小说,用”假语村言”包裹着最残酷的人生真相。第一回那首”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题诗,道出了文学史上最复杂的创作心理——作者既要逃避文字狱的罗网,又渴望知音理解其苦心。
曹雪芹的创作方法堪称文学炼金术。他将祖父曹寅《续琵琶》中的戏剧元素、舅祖李煦家族的政治遭遇、自家抄家的惨痛经历,与对清代贵族社会的观察熔于一炉。大观园元宵夜宴的繁华对应着康熙南巡的盛况;元春省亲的仪仗暗藏着曹寅接驾的记忆;而贾府被抄的描写,几乎就是雍正五年事件的文学转写。这种将个人创伤转化为普遍人类经验的能力,使《红楼梦》超越了家族小说的范畴。
脂砚斋批语揭示了创作过程的艰辛:”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漫长过程中,作者不断调整叙事结构。从早期《风月宝鉴》的情色小说框架,到后期融入政治寓言、哲学思考,最终形成”大旨谈情”而实则包罗万象的宏大文本。这种创作轨迹,印证了苦难如何被艺术驯服的过程。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3年)除夕,当京城百姓忙着贴桃符、放爆竹时,西山脚下的破屋里,四十八岁的曹雪芹在贫病交加中走到了生命尽头。敦诚《挽曹雪芹》诗记载:”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这位文学巨匠死时,身边只有续弦妻子和几叠未完成的手稿。据传他因幼子夭折悲伤过度,又无钱延医而逝,草草葬于西山某处,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
曹雪芹的死亡方式构成残酷的历史反讽。他笔下贾宝玉最终”悬崖撒手”的结局,竟以更悲惨的形式在作者身上应验。现存所谓”曹雪芹墓碑”不过是1971年在北京植物园发现的粗砺石块,上面仅存”曹公讳霑墓”五个模糊刻字。正如他的小说永远缺失后四十回,他的坟墓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迷失之物”之一。
当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回望曹雪芹的一生,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历史悖论:正是那些摧毁曹家的政治风暴,阴差阳错地造就了《红楼梦》的诞生。就像但丁需要流放才能写出《神曲》,陀思妥耶夫斯基必须经历死刑赦免才有《罪与罚》,曹雪芹的文学天才恰是在家族没落的黑暗中迸发出最耀眼的光芒。
《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完成了双重超越:既是个人苦难的升华,又是时代局限的突破。曹雪芹将包衣世家的记忆转化为对封建社会的全景式描绘,使私人叙事获得史诗品质。从”好了歌”到”飞鸟各投林”,他构建的不仅是某个家族的衰亡史,更是对人类存在困境的哲学思考。这种将”黑”转化为”红”的能力,正是天才区别于常人的根本特征。
今天,当我们在北京植物园的曹雪芹纪念馆看到那些粗糙的瓦罐、煤油灯复制品时,很难想象它们曾见证过怎样惊心动魄的文学创造。历史反复证明:伟大往往诞生于衰败之中,而文明最璀璨的花朵,常常绽放在废墟之上。曹雪芹用他红与黑交织的人生,为这个历史命题写下了最动人的中国注脚。
作者简介
万伟恒,网名玄机子,自由职业者,往来于城乡之间,无所谓宠辱沉浮。热爱读书,喜欢写作,偶有佳作,自娱自乐,偶然获奖,纯属巧合。个人微信号:wanweiheng
原创作品
未经授权禁止盗用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