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与戏曲,本是中华文化里两株并蒂而生的奇葩,在那副戏班对联里完成了最精妙的相拥。
看那笔锋游走,何尝不是舞台上的身段流转?狂草的飞白如净角甩动的翎子,骤然发力时带着 “哇呀呀” 的怒吼气势;行笔的婉转恰似花旦的云步轻移,腕间一旋便漾出三分羞怯七分娇憨。
提按顿挫间藏着锣鼓经的节奏,重笔落下如板鼓敲碎寂静,细锋牵丝似月琴漫出余韵,连墨色晕染的浓淡,都暗合着脸谱上油彩的层次 —— 朱砂的热烈、黛黑的沉郁、白粉的诡谲,在宣纸上重演着生旦净丑的善恶交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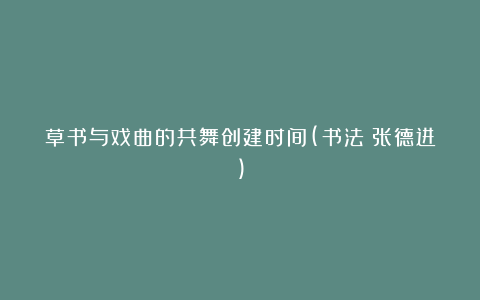
草书的章法更是一场无声的大戏。字与字的揖让呼应,像极了舞台上的对手戏,你进我退间藏着攻防的智慧;行与行的疏密交错,恰似戏文里的起承转合,密处如两军对垒剑拔弩张,疏处若月下独酌空庭寂寥。那看似随性的笔误涂改,倒有几分像名角临场的即兴发挥,一个错步反成经典,一点飞墨偏生妙趣。
当戏班学员在晨功时瞥见墙上的联语,会忽然懂了师父说的 “台上一分钟,笔下十年功”。草书的酣畅从不是肆意妄为,正如戏曲的洒脱从不是放浪形骸,二者都在规矩与自由间寻得平衡,用最奔放的形式,守护着最传统的魂。墨痕干涸处,犹闻水袖拂过的轻响;唱腔停歇时,似见笔锋破空的残影。
当学徒们对着对联临摹草书,笔锋的提按顿挫里,渐渐悟透戏曲的真意:油彩画得出脸谱,却画不尽人心深浅;曲调唱得出悲欢,却唱不完世事浮沉。唯有这副对联,以最凝练的笔墨,将戏里戏外的千情万态,都收进了那跌宕的笔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