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县城的街角,仰望一幢幢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而如果登上楼顶,则可以极目远眺,所见是连绵的屋顶,如灰色的波浪,涌向远方的天际。
街角所见不过是行人的脚,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偶有一二驻足者,目光也未必落在我身上。我看见的是尘埃,在阳光下飞舞,如同微小的精灵,不知从何处来,亦不知往何处去。
我攀上县城南的天门山,山上草木茂盛,一条公路从山麓盘旋而上,直通山巅。站在山巅最高处的泰山庙,视野豁然开朗,脚下的甘谷城如棋盘般展开,街道细线,车辆如甲虫,行人则连甲虫也不如了。我看见云影掠过大地,看见渭河如银带,缠绕在陇原大地的腰间。
我来到山村,农人荷锄而过,抬头望我,目光中满是疑惑。他们终日低头耕作,所见是方寸之间的泥土,与作物的嫩芽。他们看见的风景,是泥土的湿润,是禾苗的拔节,是雨后泥土的气息。
我来到咸阳机场乘飞机,咸阳是秋雨绵绵,然而,当飞机腾空而起,穿过云层,到云层之上的时候,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色。
云海在下方翻腾,如雪浪,如棉絮。耀眼的阳光从舷窗斜射进来,瞬间看到的云层又是金色。大地如一幅巨大的画卷,山川、河流、城市,都缩小成微缩的模型,清晰而又遥远。
邻座的旅客睡着了,他的脸上映着云层的白光,显得格外安详。他或许梦见了什么,或许什么也没有梦见。他所见的风景,与我不同,或许在他梦中,风景是另一种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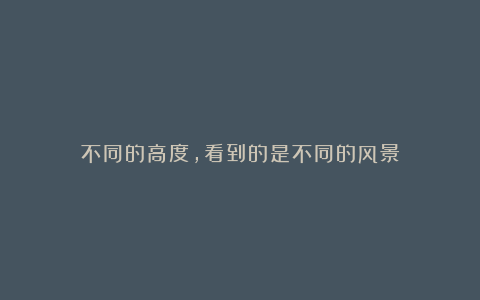
在地面所见是秋雨连绵,在云层看到的是云雾缭绕,而我们在云层之上看到的是艳阳高照,晴空万里。所处的高度不同,看到的是不同的风景。
假如我是宇航员,进入太空的时候,看到的风景又是另外一个景象。在太空回看我们居住生活的地球,不过是一个蓝色的星球,在太空中呈现出鲜明的蓝色。从空间站约400公里的高度俯瞰,地球表面被蔚蓝色覆盖,海洋的深邃与陆地的翠绿、金黄相互交织,宛如一颗镶嵌在宇宙中的蓝色宝石。晨昏线附近,阳光穿透更厚的大气层,地平线上会浮现出温柔的粉橘色光晕,仿佛给地球戴上了一圈温暖的光环。
从太空俯视地球的云层,呈现出变幻莫测的形态。厚密的积雨云因水滴对光线的米氏散射,呈现出均匀的灰白色;薄纱般的卷云则透出淡淡的冰蓝色。雷暴云形成的高耸砧状云顶,在阳光照射下,云层底部的水滴和冰晶会形成明暗对比强烈的“阴影区”,而云顶的冰晶因阳光折射呈现出珍珠母贝般的虹彩光泽,被宇航员称为“太空中的天然棱镜”。
从太空看,一半是白昼,一半是黑夜。夜晚的地球,城市密集的灯光通过大气散射形成橙黄色的光晕。不同城市的光污染轮廓差异显著:东京湾的光带呈现连续的亮白色,是高密度LED照明的结果;欧洲城市多使用暖色调的高压钠灯,在太空中形成柔和的橘色斑块。
从太空俯瞰,地球上的山川湖泊不再是地图上的简单标记,而是生动讲述着地质变迁、气候流转的宏伟史诗。宇航员可以看到江河的蜿蜒,山脉的雄伟,以及沙漠、雨林等不同地貌的壮丽。
不同的高度,看到的是不同的风景。而人心的高度,决定了风景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