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神分裂症中的“虚空”
面对大他者的虚空
蒂博(我们给他取了这个化名)是一位24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他是一个“工作狂”,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他的专长是绿化工作:修剪、砍伐、割草、拔草,等等。他来工作就是为了工作,因而他不可能接受自己的某些同事可以“轻松度日”(se la coulent douce),就像他所说的那样,他们相互之间开玩笑,在手机上打发时间,等等。与此同时,他们的工作却没有完成。于是,他会侵占他们的工作,替他们完成工作,而当工作完成之后,他也总是会找到更多的事情来做。这便造成了他与其同事们之间产生了一些强烈的紧张关系,但他别无他法,他无法停止,此种律令的强大远胜于他自己。同事们针对他的种种评论,他都会立刻将其当作指责,他甚至觉得他们的言辞、微笑、欢笑和目光都是真正针对他的迫害。他知道自己不应该去做超出要求的工作,以免精疲力竭,譬如避免癫痫发作,但他就是做不到。他必须不断处在活动之中,总是忙碌不停,因为他只能从字面上来理解那些经常被重复灌输给工人们的话语:“你们在这里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娱乐、休闲或偷懒”。对他来说,不可能不去完全充分地响应这句命令。不可能工作得更少,不可能工作得更慢(他如是说道:“如果我必须放慢速度,我就会毁掉自己的精神”),不可能不去填满自己的时间,不可能忍受“虚空”。我们都知道,所有精神病患者都无法忍受无所事事,每逢周末、节假日和寒暑假,在生活节奏上的所有这些中断时刻都会迫使他们面对一种令人焦虑的虚空……在精神分裂症中,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虚空感尤其常见,因此,我们必须看看这种虚空是什么,它指向了什么,它又告诉了我们关于精神分裂症的什么。
欧仁·闵可夫斯基《精神分裂症》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27年,现象学精神病约家欧仁·闵可夫斯基就已经在其《精神分裂症》一书中强调了事情的这个面向,他写道:“患有精神分裂症和分裂样人格的病人,常常不知道什么是休息……生活里的这个元素在他们的精神中似乎是不存在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并不拥有必要的感官来享受此种放松。要么他什么都不做,因而他真的什么都不做;这是他内在的虚空,一种冰冷而阴郁的虚空,恰恰处在休闲的相反一极。要么他会固守于某种观念,凝固在其想象的一副画面上反刍,总是不断重复一个单一刻板的动作。又或者,最后,由于他没有能力来欣赏时间中的自由间隔的积极价值,他会试图用其活动填满所有的时间,而不给自己留下丝毫喘息的瞬间,不给自己留下丝毫空闲的空间”(Minkowski, 1927)。
闵可夫斯基《精神病理学专著》
蒂博所处的恰恰就是这最后一种情况。欧仁·闵可夫斯基继续说道:不需要太多东西就能让“个人的冲劲(élan)脱离周围环境的生成变化,变得停滞不动和完全破碎”(在2020年3月的第一次疫情隔离期间,蒂博便出现了此种非常焦虑且极度不稳定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精神分裂症患者会沉入虚空,陷入虚无。工作为蒂博提供了坐标、框架和限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将会看到,它恰恰给“大他者的虚空”划定了边界。倘若没有工作,他便可能会失去依凭,并在焦虑中预感到自己可能崩溃松解的风险。对蒂博而言,此种令人焦虑的虚空不同于忧郁症患者的虚空[1],工作勉勉强强——但终究还是——构成了一个“周围”,从而给令人焦虑的虚空划定了一道边界。后来,欧仁·闵可夫斯基又在其1966年的《精神病理学专著》中多次回到了这个“虚空”和“虚空感”的概念上来进行讨论,任何临床从业者在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相遇中都可以体验到此种“虚空”。例如,他提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在虚空中言说”,他还补充说道:“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我们察觉不到任何共鸣,在精神分裂症的音域中,我们发现不了能够与我们自身和周围环境产生和谐共振的任何和弦,因此我们撞上了虚空”(Minkowski,1966)。
亨利·埃伊《精神分裂的概念》
亨利·埃伊(Henri Ey)在1975年也同样强调了这一点,他当时写道,我们在此撞上了“一种绝对的缺失,一个无底深渊的洞口,它是如此之绝对,以至于我们只能将其定义作’充满虚空’”。临床从业者在其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相遇中的这种如此特殊的关系,这种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虚空”转移到临床从业者身上的这种运动,保罗—克劳德·拉卡米耶(Paul-Claude Racamier, 1980)用以下措辞来对其表达:“只剩下了一个充满虚空的躯壳”,他将“这种特殊的体验”称之为“空乏”(inanité),亦即:“一种空洞的状态,缺乏意义……没有承载意义的能力,被剥夺了意指性”。
保罗—克劳德·拉卡米耶《精神分裂症患者》
然而,让我们强调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在虚空中言说”,也反映了主体在面对大他者时的一种独特的主体性立场。而就对话者而言,我们在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相遇或交流中感受到的此种“虚空感”,可能仅仅是一种“感觉”〔sentiment,正如拉康所言,是“谎觉”(senti-ment)〕。因此,我们可能不该太快地将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让人看见和听见的东西,他们与世界、他者、语言之间的关系,他们的思维及其情感等等——与(内部的、智识的、情感的)“虚空”联系起来。他们的妄想观念、幻觉声音、行动宣泄和发明创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的艺术天赋或科学天才,都表明这种明显的“虚空”或被他者体验的“虚空”,并不是真的那么空洞。对于精神分裂患者的所谓“情感空洞”(vide affectif),罗杰·让蒂斯(Roger Gentis, 1969)在这个主题上显得相当具有批判性,他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无情感性’(inaffectivité)是在精神病学的’科学’权威下传播开来的蒙昧与误认的绝佳例证之一……相信这种’无动于衷’(情感淡漠),接受他们’情感空洞’的幻象,就等于掩盖了其深层焦虑和这种焦虑的原因”。相反,我们可以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他者是虚空的。大他者没有缺失,而是空洞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大他者不存在”[2]。
罗杰·让蒂斯《精神分裂症患者》
与拉康派精神分析家阿尔弗莱多·泽诺尼(Alfredo Zénoni)一道,如果我们假设说在精神分裂症中,“缺少大他者维度的基础与一致性”,“大他者在那里就是一个既没有价值也没有实现的维度,就像一个不再有任何人会玩的游戏,或是没有人知道其规则的游戏”,“大他者的游戏及其规则在其根本性不一致中被遭遇,如同一个空洞的诡计,没有对象”(Zénoni,2004),那么我们便可以理解,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面对虚空可能是多么的可怕。因为这个虚空并不是“现实”的虚空。这才是整个问题之所在。当然,每个主体都在面对“虚空”,例如癔症患者的“空虚感”,但在神经症中,这种空虚是被能指所包围的,换句话说,是被象征界所框定的。知道如何应对虚空(savoir y faire avec le vide),意味着主体可以支配“假象”(semblant)的范畴。在蒂博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范畴是深深缺失的。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当他工作时,“他不是在假装”。这要在字面上来看待。他不懂如何假装(造假)。对此,让·乌里说道:“假象……在我看来似乎就是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遭到摧毁的东西……;他的假象完全崩坏了”(Oury, 2016)。
让·乌里《精神分裂的原发症状》
过满与虚空
在这个故事中,表面上的悖论便在于,“虚空”——亦即精神分裂症患者所体验到的这种虚空感——来自于一种“太满”,一种“过剩”:正是因为不存在结构性的虚空,精神分裂症患者才无法忍受生命的虚空,现实的虚空,“身体的虚空”(Artaud,1974)。例如,安托南·阿尔托就曾写道:“一切都是多余的,一切都是这个不断加重存在的过剩,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多余的观念”。他体验到了“虚空的极其可怕的悲伤,那是一个里面什么都没有的空洞”(Artaud,1978)。加藤敏(Satoshi Kato)在一种现象学方法中非常准确地描述了我们想要在这里突显的东西,他写道:“我们可以用’力量’这个术语来可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体验,它呈现出两种特征:其一是未知性,其二是神秘的他异性……我提议将这种力量称作:’无意义的力量’……这种无意义的力量会以强度极大的压力而压垮精神分裂患者,以至于他几乎没有自己的主体空间。换句话说,无意义的力量会以一种过度充盈状态的模式而出现。但这种模式基本上是以虚空为特征的。因此,无意义的力量便可以被定义作虚空的过满状态。换句话说,无意义的力量是由虚空存在的过度占位而构成的。这便是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病理学的根本特征之一”(Kato,1993)。事实上,在我们看来,这些话特别准确地描述了精神分裂症的“体验”,它们强调了精神分裂症问题中的(过度)“充盈”(plein)与“虚空”(vide)这些基本概念。在这方面,它们可以与一种结构主义的方法相印证。精神分裂症的结构没有“被掏空”(évidée),也就是说,借用拉康的话来说,没有“对象(a)的拔除”,没有象征性阉割。在其《论精神病的任何可能治疗的一个先决问题》(Lacan,1958)一文中,拉康这样写道:“现实的场域仅仅是以对象a的拔除为支撑的”[3]。只有在有缺失,即“存在的缺失”(manque-à-être)的情况下,现实才能得以建构并得以维系,才能被“框定”和被“限定”——这便是拉康所谓的“缺失的结构性功能”(Lacan,1964)。但在精神病中,象征性阉割的操作显然并未发生,结果便导致主体没有与这个对象分离——主体反而被对象所“塞满”或“封堵”[4]——因此,现实便是无边界和无限制的,因而也是令人不安、令人焦虑,且往往带有威胁性的。神经症特有的这种结构性空缺——此种空洞构成了现实的界限,并给它赋予了一个框架——在精神病中是缺失的。这种无安全性边界的现实,这种无象征性界限的实在的虚空,有时会迫使主体在一种绝对茫然的位置上来体验现实。主体所遭遇的“排除”之洞,并非神经症患者的那种“包围”之洞,后者构成了一种有框架的现实。让娜·格拉农—拉丰(Jeanne Granon-Lafont,1990)写道:“在明显的精神病中,这个洞不存在。没有边缘,它是空的,这便是精神病患者所体验到的痛苦”[5]。此种虚空也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和不同的辖域中被观察到,例如在语言的层面上:阿涅斯·梅顿(Agnès Metton,2005)因而强调,“空洞的缺失,通过冻结话语的运动,不断地将精神分裂主体带回到某种起点的格子,一种回归初始的状态。这便为其反复出现的刻板行为和循环往复给出了线索,无论是在言语上还是在行动上的循环往复。回到起点,以试图挖掘出一个缺位”。这种虚空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因为它没有界限,因此主体便会通过各种尝试来“填补”这个虚空,或是给它划定一道边缘:各种增补或发明(语言、文字,等等),全身心投入到某种特定研究之中,投入到工作之中,投入到在社会上扮演某种角色之中,投入到完成某种任务之中,投入到某种大规模的认同之中,等等[6]。
蒂博无法停止工作,否则就会面对令人焦虑的虚空,他是名副其实的“工作狂”,而他也在其动作及其话语中突显出了其工作的“阳刚”面向[7](另外,当他的一位男同性恋同事跟他说话时,他会感到相当受迫害),这便很好地呈现了拉康在其《精神病》研讨班上所说的东西,亦即:在某些精神病主体那里,存在着整个“一系列纯粹从众的认同,这些认同让他能感受到必须做些什么才能成为一个男人”(Lacan,1955-1956)。换句话说,对蒂博而言,绿化工人(劳动者)的“理想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与“阳具意指”的虚空重叠了起来。
精神分裂症患者所体验的虚空感,源自于一种过度充盈的“太满”或“过剩”。
意义的虚空
所有这一切——用本文开篇引用的让·乌里的话来说——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逃离虚空”亦或“开垦虚空”的方式。对蒂博而言,工作允许了“虚空被包围起来,而没有逃逸”(Oury,1989),至少在他有工作的时候是这样,这是他不断把自己投入进去的事情。因为无法忍受虚空,就像在很多精神病患者那里一样,我们在他身上也见证了“一种填满的强制”(Oury,1989),这使他能够“保持一种允许生活的平衡”(Oury,1989)。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在这个虚空上建造或搭建一些东西。至于偏执狂患者则通常能够通过其妄想性建构或是其妄想性解释而做到这一点。正如萨迦·纳什特与保罗—克劳德·拉卡米耶(Sacha Nacht & Paul-Claude Racamier,1958)所言:“一切都变得充满了无限的意义,它们将会在意义再次出现于虚空中心的那一刻上瞬间绽放”。至于莫德·马诺尼(Maud Mannoni)则提到:“在某一刻上与外部现实之间出现了裂隙”,并强调妄想恰恰“填补了由此种现实丧失所留下的虚空”。她还强调了妄想在某种程度上的保护性功能:“这是主体为了不陷入虚空而紧紧抓住的意指链接”(Mannoni,1970)。精神分裂症患者无法建构系统的“妄想隐喻”以供自己使用。他们只可能抓住一些零星的思想碎片,但这些碎片往往并不足以帮他们来应对意义的虚空。精神分裂症患者是那种无法“凭借象征界来抵御实在界的人……因为对他来说,整个象征界都是实在的”(Jacques-Alain Miller,1993)[8]。因此,面对“虚空”确实令人恐惧。正如拉康在其《精神病》研讨班中所言:“没有什么是比接近虚空更加危险的事情”(Lacan,1955-1956)。
莫德·马诺尼《精神病学家,其“疯子”与精神分析》
在精神分裂症中,让我们注意到,结构性的“虚空”从根本上主要涉及到“意义的虚空”。拉康曾在其1958年的文章中提到了这一点。关于那些表现出被称作“妄想性直觉”的基元现象的精神病主体,拉康写道:“意指的效果在那里预期了此种直觉的发展。事实上,它涉及的是一种能指的效果,因为其确信程度(第二程度:意指的意指)的比重与最初出现在意指本身位置上的谜样虚空是成比例增加的”(Lacan,1958)。因此,起初的“谜样虚空”便在呼唤着某种对主体而言可以呈现出确定性价值的意指。因此,在意义的虚空与精神病的确信之间便存在着某种关系。因而,在评论拉康的这段话时,雅克—阿兰·米勒也给出了如下的序列:“谜题—困惑—焦虑—行动—确信”,他还明确指出:“首先,是虚空;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然后,是确信:我知道这意味着某种东西。我越是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就越是知道这意味着某种东西”(Miller,1997)。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更多涉及的是精神病的偏执狂面向。因而,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精神病的虚空便指向了“除权”的空洞:拉康因而谈到了“从原初的排除(Verwerfung)中突然察觉的虚空”(Lacan,1958)。
结论
面对虚空对于精神分裂主体而言是一种特别令人痛苦,甚至令人难以忍受的考验。这种虚空,从结构的视角来看,根据拉康的教学,直接指向了“父名”能指遭到排除的“空洞”。在这里,它被命名作“意指的虚空”。世界、生活、他者、身体、词语、话语、现实……在其整体上都携带着一个根本性的谜团。对于整个象征界都是实在界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生活中的假象都在他那里无法构成假象。换言之,大他者是空的,不一致的,因此,对某些精神分裂主体而言,便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来“填满”这个虚空。处在虚空边缘、深渊边缘所体验到的恐惧,有时也会推动主体找到一些解决方案,以便给此种虚空赋予某种边界或限制,从而将其框定,并给主体赋予在现实中的某种基座,正如让·乌里所言,某种允许主体能够“继续生活”的平衡。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痛苦中感受到的这个“虚空”,源于一种“太满”和“过剩”(正如安托南·阿尔托所言:“一切都是多余的”),用拉康的话说,这便是“拔除对象小a”的失败。在神经症中,正是对象(a)的拔除——亦即“象征性阉割”——给现实赋予了其框架。倘若没有这种“掏空”,虚空就始终是没有边界,没有边缘的“无限”,因此特别令人不安和焦虑。象征界——词语、能指、语言——未能代表世界的意义,词语和事物的世界在其整体上仍然是一团迷雾,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来“开垦”这片虚空,以便能够围绕此种虚空而创造出一些界限;他需要给这个虚空赋予一个“围场”,一个“围墙”,而我们看到年轻的蒂博在其工作中便“全身投入地”(à corps perdu)致力于此。倘若没有这种全身投入,倘若没有解决方案,精神分裂症患者就可能会像安托南·阿尔托一样感到自己“没有内在”,“绝对无根”,而体验到纯粹的“活着的虚空”(Artaud,1988)。
安托南·阿尔托画作
文本注释
[1] 在忧郁症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说,是自我变得空洞(Freud,1917)。
[2] 在精神病中,“大他者遭到了真正的排除”(Lacan,1955-1956)。拉康的这个表达更多对应着精神分裂症而不是偏执狂。
[3] 让我们不要忘记,这篇文本虽然可以追溯至1958年,但涉及“对象(a)的拔除”的这段话则是在1966年《著作集》出版社增加的一则脚注。
[4] 让娜·格拉农—拉丰在这个意义上写道:“这个太过固着的对象便是大他者的符号、结果或原因,这个大他者并不缺乏虚无,他没有空洞,也不会留下任何空间来让主体在其中上演其自身的问题”(Granon-Lafont,1990)。
[5] 安托南·阿尔托恰恰说道:“就我而言,我会谈到洞的缺位,这是一种冰冷而无形的痛苦”(Artaud,1956)。
[6] 根据布里斯·马丁与玛丽—奥德·皮约特,欧仁·闵可夫斯基所描述的那种“病态理性主义”(rationalisme morbide)恰恰便在于“以损害生命活力为代价而用空间层面上的一些元素来充盈精神生活的饱和”,它使主体得以“填补精神分裂的虚空,这种虚空与在周围世界中缺乏出路有关”(Martin & Piot,2011)。
[7] “父之名的除权”会导致“阳具性意指”缺位的结果。用拉康的代数学来表示,亦即:Po => Φo。让—克劳德·马勒瓦尔因而明确指出:“正是因为精神病患者并不拥有阳具性的回答,接近大他者的洞口才是让他无法忍受的。当他遭遇这个令人焦虑的谜题之时,他便会发觉自己不得不努力去堵住这个空洞”(Maleval,2000)。
[8]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整个象征界都是实在的”(Lacan,1958),拉康如是说道,而他在后来又强调说,“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它排除了意义”(Lacan,1975-1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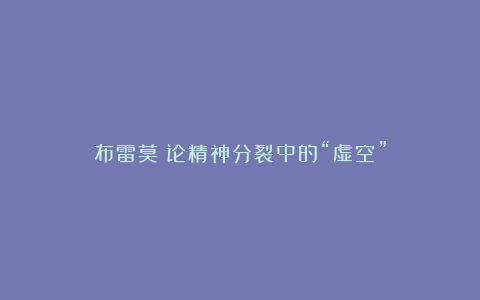
参考文献
安托南·阿尔托《全集》第1卷,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56。
安托南·阿尔托《全集》第11卷,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74。
安托南·阿尔托《全集》第14卷,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78。
安托南·阿尔托《全集》第24卷,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88。
亨利·埃伊《精神分裂的过程》,见:亨利·埃伊指导《精神分裂的概念》,1975年2月至6月的蒂伊研讨班,巴黎:德克雷·德·布劳沃出版社,1977。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哀悼与忧郁》,见《元心理学》,巴黎:弗利奥出版社,1986。
罗杰·让蒂斯《精神分裂症》(1969),图卢兹:埃雷斯出版社,2002。
让娜·格拉农—拉丰《拉康拓扑学与分析的临床》,巴黎:圆点出版社,1990。
加藤敏《精神分裂患者那里的死亡与割裂主题》,载于《精神病学演进》杂志第58期,1993:第727~742页。
雅克·拉康《回应让·伊波利特关于弗洛伊德的“否定”的评论》,见《著作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
雅克·拉康《研讨班三:精神病》(1955-1956),巴黎:瑟伊出版社,1981。
雅克·拉康《论精神病的任何可能治疗的一个先决问题》,见《著作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
雅克·拉康《研讨班十一: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1964),巴黎:瑟伊出版社,1973。
雅克·拉康《研讨班二十三:圣状》(1975-1976),巴黎:瑟伊出版社,2005。
让—克劳德·马勒瓦尔《父之名的除权:概念及其临床》,巴黎:瑟伊出版社,2000。
莫德·马诺尼《精神病学家,其“疯子”与精神分析》,巴黎:帕约特出版社,1970。
布里斯·马丁与玛丽—奥德·皮约特《精神分裂症的现象学方法》,载于《精神病学通讯》杂志第87期,2011:第781~790页。
阿涅斯·梅顿《重复的步伐:精神分裂症与原始象征化》,载于《拉康领域临床学院杂志》第4期,2011:第41~48页。
雅克—阿兰·米勒《反讽的临床》,载于《弗洛伊德事业》杂志第23期,1993:第7~13页。
雅克—阿兰·米勒主编《昂热秘密会议:精神病中的惊讶效果》,巴黎:纳瓦林出版社,1997。
欧仁·闵可夫斯基《精神分裂症》(1927),巴黎:帕约特出版社,1997。
欧仁·闵可夫斯基《精神病理学专著》,巴黎:PUF出版社,1966。
萨迦·纳什特与保罗—克劳德·拉卡米耶《妄想的精神分析理论》,载于《法国精神分析杂志》第22期,1958:第417~532页。
让·乌里《创造与精神分裂》,巴黎:伽利雷出版社,1989。
让·乌里《精神分裂的原发症状》,巴黎:太一出版社,2016。
保罗—克劳德·拉卡米耶《精神分裂症患者》,巴黎:帕约特出版社,1980。
阿尔弗雷多·泽诺尼《精神病的尺度:关于所谓精神分裂症的评论》,载于《第四》杂志第80-81期,2004:第17~24页。
米勒|反讽的临床:世人皆疯狂
没有什么是比接近虚空
更加危险的事情!
——雅克·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