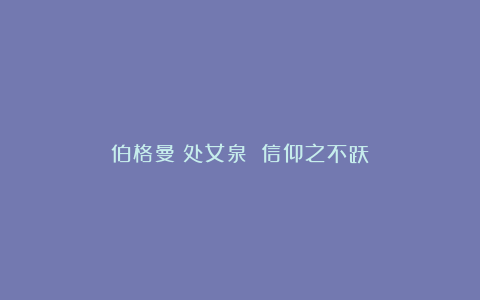分析伯格曼的电影无法绕过其中强烈的宗教意识。几年前我看过伯格曼对电影的见解的书,作为牧师之子的他看起来是如此憎恨宗教。而这强烈的恨,反使其对于宗教的刻画更为深切,甚至达到某种超验性。
由于我也是没有信仰,但曾经试图有信仰的人,所以我才拥有了深刻体验《处女泉》的视角。
小时候我在城市里上希望小学,二年级和三年级,学校旁边的教堂圣诞节会来学校送礼物。周日我会为了教堂给小朋友发的饼干糖果和本子去背圣经。我不理解亚伯拉罕的信仰之路,他年纪很大,老来得子,上帝为了考验他的信仰叫他烧死自己的儿子。
那时我亲眼见过妹妹出生,孩子是从母亲的子宫里,伴随着大量的鲜血与痛苦来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显现任何神的奇迹。我认为孩子的父亲并没有权力让孩子成为他信仰的证据,因为他并不曾体验孕育生产的肉体之痛。
这里提到亚伯拉罕的故事,也是因为《处女泉》这部电影某种意义上类似于这样的献祭。只是“上帝”在这里安排的是三个底层流浪者,执行并完成这个过程。电影中的男主角托尔更像14世纪的亚伯拉罕。不同之处是亚伯拉罕是主动献祭,他是被动受害。影片开篇中有好几个细节也点出来托尔并没有那么虔诚,更世俗化的细节。比如一大早他和妻子祷告,他念完了祷告词立刻抽身。
这部电影一度使我非常痛苦。尤其是林中少女与牧羊人遇见的镜头,每每想起都会崩溃落泪。整部电影的节奏看似枯燥,镜头的移动也是跟随着人物行动缓慢横移,多数时候甚至是远离角色。某种意义上这构成了双重无力感,它时刻提醒你,悲剧要发生了,你无法阻止,美好会被摧毁,邪恶一定会降临这片看似优美宁静的土地。
9岁的夏天我在村里见过类似的事。当时我们村有一个初中生强暴了一个两岁不到的女婴,我在马路上刚看见他爸抱着下体流血的她恸哭,吓得跑回家,看到罪犯正躲在邻居家的柴房,我和他对视上了,我看见了那个人眼里野兽般的餍足与凶光。如今那个女孩的心智没有长大成人,只剩下肉体的本能在活着。那个初中生经历了5年少管所,出社会后成为了一个仍然没有良知也没有认知的垃圾。
托尔在复仇前独自在林中徒手拔起一棵桦树,接着动手前又用桦树枝抽打自己的肉体。我跟着紧张和愤怒。他最终毫无悬念的杀了这三个人,没有血肉横飞的场面,只有火光,影子在画面里坚决又利落的收束。
直到他们全家人在林中跪拜卡琳尸体下涌出的清泉,我才从愤怒中出离。我不断的回到9岁那年的那天,我不断在想为什么。
强暴事件摧毁的并不是一个人的肉体健康,而是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意志的主体性。男权社会为什么会指向于认为是女性的过错,或者将责任与痛楚推卸给受害者。是因为他们自己无法面对,由他们的意志和语言所建立的秩序可以轻易的被他们内部弱者无秩序的混沌力量摧毁。
所以,某种意义上他们必须抹去受害者,以此来掩盖他们所建立的秩序的无能和偏狭。
《处女泉》的另一层意义也由此而来, 托尔在原地建立了一座教堂,他此前公式化的信仰在他质问上帝的时候消失了,他真正的有关于人的良知,对于爱和善的信仰从此建立了起来。
这也给观众带来了真正的疑问。要经历过何种痛楚,我们才能真正得到信仰的眷顾?
电影中英格丽的存在是另一面镜子。她的身世不明,怀了一个也身世不明的孩子,电影里有的时候甚至还在暗示,是她带来了灾祸。她是无序之恶的相对面,有迹可循的嫉妒,不加掩饰的欲望,懦弱与虚伪。
她用卡琳尸体流出的清泉洗干净了从来没洗干净的脸,她在想什么?她曾经的遭遇是什么?她作为新生命的引路人,是否有领悟出生命的来之不易,短暂的欢乐,和深刻的痛苦?
1994年由格鲁吉亚女导演娜娜.裘杨兹所拍摄的《摇篮曲》与这个故事有些类似,但是电影里的母亲面对被乞丐拐走又被找回来的女儿,用无尽的美好、温暖与爱,去重新滋养女儿的肉体和心灵。
我想某种意义上人的信仰是一个普通的人类母亲对于生命的信仰,就像玛利亚之于基督,不管基督的父亲是谁,她都愿意承担痛苦与骂名,笃定的认为她的孩子来自于天赐,背负着神圣的使命,要将福音广传于充满苦难与不确定的人世。
很小的时候我见过那个女孩儿的母亲。她在女儿一岁左右就得子宫癌去世了。有一天放学的时候我看见她在家门口哄女儿睡觉。像玛利亚一样。
这才是真正的超越理性的信仰之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