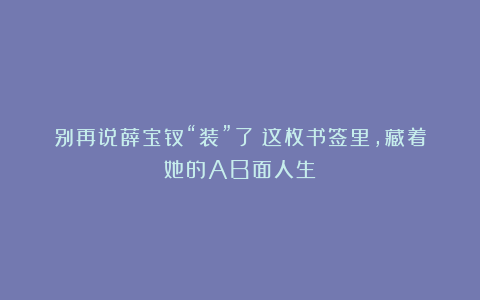|
张杰宇
在《红楼梦》所塑造的众多女性当中,薛宝钗无疑以其性格的复杂性、行为的矛盾性与评价的争议性,成为红学研究中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她既是“行为豁达,随分从时”的封建淑女,又是“金蝉脱壳”事件中机心深藏的世故者;既有“任是无情也动人”的冷艳超然,又有“宝钗扑蝶”时流露的少女天真。清人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第38回的批语中如此谈论他对薛宝钗的观感:“全书那许多人写起来都容易,唯独宝钗写起来最难。因而读此书,看那许多人的故事都容易,唯独看宝钗的故事最难。大体上,写那许多人都用直笔,好的真好,坏的真坏。只有宝钗,不是那样写的。乍看全好,再看就好坏参半,又再看好处不及坏处多,后复看去,全是坏,压根儿没有什么好。一再反复,看出她全坏,一无好处,这不容易。但我又说,看出全好的宝钗全坏还算容易,把全坏的宝钗写得全好便最难。读她的话语,看她的行径,真是句句步步都象个极明智极贤淑的人,却终究逃不出被人指为最奸最诈的人。”因此,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就使得任何试图以单一视角或扁平化形象来概括她的艺术再创作,都显得力有不逮。
基于此,我的书签设计提出以“一体两面”作为核心的创作理念——“一体”指薛宝钗作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文学人物存在;“两面”则指其身上并存的两种主要倾向:即以“冷香丸”为象征的理性克制和从娘胎里带来的“热毒”,并通过具体的艺术设计实践转化为一件可触可感的物质文化产品——书签。
本设计采用垂直双层复合结构,将书签分为“上层:动态之境”与“下层:静态之魂”,分别对应薛宝钗性格的外在行为表现与内在本质象征。
(1)材料:选用具有良好韧性及古雅肌理的优质仿古宣纸。
(2)核心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竹编技艺的纸艺转化。特选取两种色调的薄型手工纸,裁切为均匀的细条:
浅淡冷色系纸:象征其冷静、内敛、理性的“冷”的一面。
温润暖色系纸:象征其圆融、温和、入世的“热”的一面。
视觉图案:利用AI赋能,给豆包输入指令:采用工笔与写意相结合的国画技法,精绘“宝钗扑蝶”经典场景。画面聚焦于薛宝钗执扇、俯身、追逐玉蝶的瞬间动态,辅以玲珑山石与烂漫花草为背景,让其生成一张图片。
(1)步骤一:竹编编织。用剪刀将两张仿古宣纸裁剪为大小、粗细相同的八张纸条。将双面胶贴至桌面,将纸条逐一并列粘贴在双面胶上,相邻纸条之间保持紧密贴合,避免出现空隙。从已排列好的纸条一段开始,采用“挑一压一,压一挑一”的原理进行,持续穿插至纸条另一端,如此重复以上步骤。在编织过程中,刻意使冷色与暖色线条相互穿插、覆盖、依存,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视觉肌理。此工艺过程本身,即是对薛宝钗身上中两种特质相互交织、难以剥离的状态的模拟。
(2)步骤二:图案叠加与融合。将AI生成的“宝钗扑蝶”打印出来,并叠加于编织成型的竹编基底之上。使人物仿佛活动于一个由理性与感性共同编织成的无形网络之中,暗示其一切外在行为,均无法脱离其复杂的内心世界。随后进行固色、压平等处理,保证作品的耐久性。
(2)视觉图案:同样利用AI赋能,给豆包输入一段指令:雍容盛开的牡丹与一只姿态昂扬、羽翼华美的雄鸡,让其生成相应图片。
首先,确定牡丹与雄鸡在画面中的布局。牡丹作为主体,取其饱满丰腴之态;雄鸡作为点睛之笔,取其昂首立姿,二者形成富贵与英武、静美与动势的呼应。运用没骨法与勾线法相结合。以饱含水分的淡彩侧锋铺染花瓣,表现其肥厚丰盈,再以稍浓之墨线精准勾勒花瓣形态轮廓。关键在于通过色彩与姿态的控制,营造“艳冠群芳”却“任是无情”的视觉感受——花色虽艳,但整体色调可偏冷;花形虽盛,但花头可微垂或转向,流露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感。雄鸡在传统文化中是“文、武、勇、仁、信”五德之象征,尤以其司晨报晓的特性,“功”与“公”谐音,暗喻“功名”。以浓墨重彩勾勒其挺拔的身姿、华丽的羽毛,尤其强调其高耸的鸡冠与锐利的眼神,以此视觉符号暗合薛宝钗内心所持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入世志向与儒家德行规范。
将上下两层打孔,并用白色丝线穿连,牢固整合为一枚完整书签,配以蓝紫色流苏。上层的轻盈、动态与下层的沉稳、静态,共同构成了对薛宝钗其人的完整视觉叙事,使其在方寸之间,承载起厚重的文学内涵。
“宝钗扑蝶”是红楼梦中典型的场景之一,这是《红楼梦》中为数不多的薛宝钗对自己的少女天性不加限制的场景,展现了鲜活的少女形象。我选用此景,旨在展现那被严密礼教规训的躯壳之下,偶尔抑制不住、自然流露的属于青春生命的“热”与“情”。
“宝钗扑蝶”出现在《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宝钗)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来扑。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来来往往,穿花度柳,将欲过河去了。倒引的宝钗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娇喘细细。
此段文字中,“十分有趣”、“意欲扑了来玩耍”、“蹑手蹑脚”、“香汗淋漓,娇喘细细”等一系列词汇,充满了生命的动感、天真与热情,是薛宝钗少女天性在无人窥见时最为本真、最为珍贵的流露。
不过再次细读此段,却能品出曹公“真事隐,假语存”的笔法。 在文学艺术的长河中,蝴蝶承载着深厚的爱情意蕴,从庄周梦蝶的哲学思辨,到韩凭夫妇、梁祝化蝶的凄美传说,再到唐宋诗词中“双双花上飞”的缠绵意象,蝴蝶已成为“集体无意识”中爱情,尤其是自由、浪漫乃至悲剧性爱情的经典象征。因此,“美人扑蝶”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暗示性的事件。在文学传统中,成双出现的蝴蝶明确指向男女相爱的状态或愿望。这“一双”蝴蝶,在此语境下,极易让人联想到宝玉与黛玉的“木石前盟”,而宝钗,恰是那个意外的“扑者”。“玉色”之“玉”,正与宝玉、黛玉两人的名字暗合。太平闲人评点此处即批注:“蝴蝶双飞,海豚好梦,乃宝、黛也,其如扑者从旁至乎?看’玉色’二字是眼。”此说精准地道出了其中的象征关联。古时美人以团扇遮面,以此形容蝴蝶之大,足以见蝴蝶的大小,这是一种文学上的强调,意在凸显这两只蝴蝶在叙事中非同寻常的象征意味。
因此,宝钗扑蝶,表面是少女忘情的天真流露,深层却是她潜意识中对爱情的渴望与追寻。然而,追寻的结果是“将欲过河去了”——蝴蝶翩然远引,未能扑得。这未果的追寻,正巧妙地预示了宝钗在“金玉良缘”中最终失落的爱情命运。
再次回到原文,在此诗情画意之后即刻发生的、堪称全书最富争议性的情节之一——“金蝉脱壳”事件。当薛宝钗在滴翠亭外无意窃听到小红与坠儿的私密谈话时,她的内心活动与外部行为发生了急剧转变:
宝钗在外面听见这话,心中吃惊,想道:“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这一开了,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况才说话的语言,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东西。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思虑已定,她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颦儿,我看你往那里藏!”
上一秒,我们还在欣赏宝钗身上洋溢的青春,下一秒却看到了一个如此城府极深的少女。她并非基于道德是非,而是纯粹从利害关系出发,确定了对自己最有利的解决方案。她“故意放重脚步”、“笑着叫道”,言行自然流畅,毫无破绽,正是她“无情”的表现。
此情节与片刻前扑蝶的天真烂漫形成了对比,体现了其“一体两面”心性在瞬间的转换与共存。书签设计通过将“扑蝶”场景置于“双色竹编”基底之上,正是以一种视觉隐喻方式来呈现这种复杂性:她这片刻自然流露的、源自生命本能的“热”,其发生背景与最终归宿,始终被那个由理性与人情算计所共同编织而成的、无形却坚韧的框架所笼罩与制约。
在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众人行抽花名签行酒令,宝钗便抽到一枝牡丹:
宝钗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个什么来。”只见签上画着一支牡丹,题着“艳冠群芳”四字,下面又有镌的小字一句唐诗,道是:任是无情也动人。”
花名签上的唐诗出自罗隐的《牡丹花》:“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身。”诗人借咏花抒发内心的感慨,借此讽刺那些靠趋炎附势、飞黄腾达的人。而出现在花名签上的诗句则隐寓着宝钗的性格、命运。蔡义江先生认为,“宝钗也就象被韩令所弃的牡丹一样,只能’辜负秾华’寂寞地了却余生。
宝钗便是一朵令人芬芳陶醉的牡丹,“艳冠群芳”综合了其“面若银盆,眼如水杏”的丰美姿容、博学宏览的才识以及“行为豁达,随分从时”的处世风格所带来的综合吸引力;而“任是无情也动人”则一语道破其魅力中那种超越个人私情的、近乎于“理”的冷静与克制气质。书签下层的水墨牡丹,正是对这一判词的诗意化与视觉化阐释,它力图让观者感受到,那看似“无情”的姿态,非但没有减损其魅力,反而构成了其动人心魄的的核心部分。这种气质在她对金钏投井后的理性开解、对尤三姐自刎与柳湘莲出走后的淡漠反应体现得淋漓尽致,呈现出一种超越寻常悲欢的、近乎“太上忘情”的冷静。
对于“雄鸡”所代表的志向与德行,其文学依据潜藏于薛宝钗的诸多言行之中。她是大观园中唯一一位屡次不失时机地劝谏贾宝玉留心“仕途经济”的正统角色,这是其入世思想最直接的表现。而其《临江仙·柳絮》词中“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豪句,更是将其不甘平庸、力求上进的雄心壮志表露无遗。其判词“可叹停机德”,此典出自《后汉书》乐羊子妻中断织布以劝夫求学立业的故事,旨在激励男子建立功名,光耀门楣。“雄鸡”与象征个人品貌风姿的“牡丹”一同,构成了薛宝钗作为儒家文化理想中“德言容功”俱全的淑女之完整画像:既拥有牡丹般的动人风仪与内在品德,又怀抱雄鸡所代表的积极用世之志向与对世俗功业的追求。
不过,牡丹虽贵为花王,但它亦是“群芳”之一,终将随同百花凋零,这暗合了薛宝钗虽最终成就了金玉良缘,却并未获得真正的幸福,落得“金簪雪里埋”的冷清结局。雄鸡司晨,象征着对秩序的呼唤与坚守,但在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终极悲剧中,这种对世俗秩序的追求显得何其渺小与徒劳。因此,下层设计在彰显其华贵与志向的同时,水墨技法所固有的氤氲与空灵质感,也在无声地传递着一种“终究是空”的悲凉感。
薛宝钗性格中“冷”与“热”的交织并存,其根源可追溯至《红楼梦》中关于“热毒”与“冷香丸”的独特设定。这一设定并非简单的病理描写,而是曹雪芹用以揭示人物内在矛盾与命运轨迹的核心隐喻。书签设计中对这两种特质的视觉化呈现,其依据正植根于此。
据书中所述,薛宝钗身患“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此“热毒”并非寻常病症,实为其天性中积极入世、关切现实的内在驱动。这种天性具体体现于两个方面:其一在于人情练达,她善于体察他人心意,无论是顺应贾母喜好,还是周全抚慰黛玉,乃至关照赵姨娘、贾环等边缘人物,皆能做到面面俱到,其行为背后蕴含着对世俗人际关系的深切关注;其二在于功利追求,她屡次劝导宝玉致力于仕途经济,其自身亦曾待选宫中才人,体现出对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自觉认同与积极追求。凡此种种,皆是其“热毒”之外显。
为医治此症,薛宝钗需服用“冷香丸”。此药方取材极为讲究,须集四季之白花蕊,并雨水之雨、白露之露、霜降之霜、小雪之雪,其性至寒,正为克制“热毒”而设。若言“热毒”是其先天本性,那么“冷香丸”便是后天社会规训的绝佳象征。它所代表的,正是那一整套需要被内化、以约束个人天性的礼教规范与处世准则。每当宝钗因内在情志或外界纷扰而致“热毒”发作之时,此丸药便起到清解冷却之效,使其复归于理性克制之态。长此以往,药性之“冷”便逐渐内化为其人格底色,塑造出其外在温婉周全、内在却理性疏离的特质。
然而,“冷香丸”仅能暂抑“热毒”,却无法根除病源。这就注定了薛宝钗其人格结构中永恒的内在张力:一方面是源自天性的、对情感与世俗价值的自然向往(热),另一方面则是后天习得的、以理性克制为主的处世之道(冷)。
书签上层设计中,“扑蝶”所展现的片刻天真与鲜活,恰如“热毒”的偶然流露;而将其笼罩其下的、以冷色为基调的竹编肌理,则宛如“冷香丸”那无时不在的理性约束。二者之间的持续拉锯,不仅构成了其行为的矛盾性,也深刻揭示了其在社会规范与个人天性之间的困境。她的悲剧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源于这种无法调和的自我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