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占峰
在20世纪中国画坛的星河中,傅抱石是一颗兼具传统深度与时代锋芒的巨星。他以’抱石斋主人’为号,将清代画家石涛’笔墨当随时代’的艺术箴言刻入创作生命,从江西南昌的贫寒少年到’新山水画’的代表巨匠,从美术史论的研究者到国画教育的开拓者,62年的人生轨迹里,他用笔墨丈量传统与现代的距离,用作品书写艺术与时代的共鸣。当我们回望他的《江山如此多娇》《屈原》《煤都壮观》等传世之作,看到的不仅是笔墨的酣畅,更是一位艺术家在历史变局中对中国画现代性的突破性探索。
傅抱石
1904年深秋,傅抱石生于江西南昌一个贫苦家庭,原名’长生’的他,或许从出生起就带着对生命韧性的隐喻。少年时他随民间师傅学刻章、绘丹青,粗粝的笔墨实践里藏着对艺术的本能热爱。彼时江西画坛多承袭’清初四王’的程式化山水,层叠的皴法、规整的构图虽显精致,却少了几分自然的野趣与精神的张力——直到他偶然在旧书摊翻到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那句’搜尽奇峰打草稿’如惊雷般击中了他。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
石涛一生颠沛却始终保持艺术革新的勇气,其’我自用我法’的创作主张,与傅抱石骨子里的叛逆与求真不谋而合。他开始疯狂搜集石涛散佚的题跋、画作,甚至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抱石斋’,’抱石’二字,既是对先贤的致敬,更是对艺术理想的明志。他曾依据石涛’萧然放艇学渔人’的题诗创作同名画作:远景山石以斧劈皴快笔挥就,墨色在生宣上晕染出雨雾朦胧;近景枯柳以中锋勾勒,线条如剑刃出鞘,带着不受束缚的飞动之势。此时的傅抱石,已不是简单模仿石涛的笔墨,而是借先贤之境,探自己之心。
这种对石涛精神的承袭,在他早年的美术史研究中更显深刻。20世纪20年代,他在南昌一家裱画店当学徒时,便利用工余时间整理石涛年谱,后又撰写《石涛上人年谱》,以史学家的严谨考证石涛的生平与创作。他发现石涛’笔墨当随时代’的主张,本质是艺术对生命体验的诚实——石涛画黄山,是因黄山的奇松怪石刻入了他的生命;石涛画渔樵,是因市井的烟火气温暖了他的漂泊。这一发现让傅抱石明白:传统不是僵化的笔墨程式,而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逻辑。
1932年,在徐悲鸿的举荐下,傅抱石赴日留学,师从东方美学权威金原省吾。在东京的三年,他穿梭于美术馆与书店,既研究日本浮世绘的色彩韵律,也关注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探索,但始终锚定中国传统的根脉。金原省吾曾问他:’为何执着于石涛?’他答:’石涛教我的不是如何画山,是如何让山有灵魂。’这种清醒的认知,让他在东西方艺术的碰撞中始终保持自我——他借鉴日本南画的水墨晕染技法,却不用其柔媚笔触;他吸收西方构图的透视原理,却不丢中国画的’散点透视’之灵。留学归来时,傅抱石的笔墨里已藏着传统的骨、时代的气。
1939年,抗战烽火蔓延至江南,傅抱石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寓居西郊金刚坡下。那是一间简陋的茅屋,窗外是蜀地的崇山峻岭——雨后的竹林雾霭弥漫,晨起的峰峦云气蒸腾,暮色中的江涛拍岸惊弦。这片从未被程式化笔墨’驯化’的山水,成了傅抱石笔墨革命的试验场。
传统山水画的皴法,无论是披麻皴的温婉还是折带皴的规整,多以’线’为核心,讲究笔笔分明。但金刚坡的山是’活’的:岩层被雨水冲刷出纵横的沟壑,草木在云雾中若隐若现,若用传统皴法,根本画不出那份’元气淋漓’。傅抱石索性打破常规,他改用长锋山马笔,将笔头、笔锋、笔根同时蘸墨,趁湿在纸上快速皴擦——笔锋擦出岩石的棱角,笔根晕出云雾的朦胧,笔头的浓墨点出草木的苍劲。墨色在生宣上自然渗化,浓淡干湿瞬间交融,竟生出’崩裂感”流动感’,如金刚坡的山雨骤至,似嘉陵江的浪涛奔涌。这种后来被称为’抱石皴’的技法,不是刻意设计的程式,是山河本身的肌理借他的笔流淌而出。
《万竿烟雨》是’抱石皴’的代表作。画中竹林在雨中倾斜,傅抱石以侧锋横扫出竹秆的柔韧,又用’抱石皴’的晕染技法表现雨雾的弥漫——近处的竹墨色浓黑如铁,远处的竹在水墨渗化中渐成淡影,仿佛伸手就能触到雨丝的微凉。他曾在题跋中说:’金刚坡有竹千竿,一日遇雨,避于竹林下,见雨打竹叶,墨气蒸腾,方知前人画雨,未得此趣。’正是这份对自然的诚实感知,让’抱石皴’超越了技法层面,成为’情景交融’的艺术语言。
金刚坡时期的傅抱石,不仅在山水画中突破,更在人物画中注入精神力量。彼时国难当头,他画《屈原》《苏武牧羊》《文天祥正气歌图》,不是为了复刻历史,是借古人之境抒今人之愤。他笔下的屈原,身着长袍立于江畔,衣袂用’飞白笔’扫出,如被狂风撕扯;面部仅用三笔勾勒,却能从紧蹙的眉头里读出’路漫漫其修远’的悲怆。他曾对学生说:’画屈原,要画出他的’孤’——不是孤独的孤,是孤高的孤,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骨。’这种对人物精神的精准捕捉,源于他将山水画的笔墨融入人物画:用’抱石皴’的笔触画山石背景,让人物在山河间更显挺拔;以书法的笔力勾勒衣纹,让线条自带’气脉’。
1945年抗战胜利,傅抱石在重庆举办画展,郭沫若观后挥笔题诗:’南石北齐各千秋,笔底江山造化游。’此时的他,已凭借’抱石皴’与’高古人物’确立了画坛地位,但他并未停留在金刚坡的成就里——他知道,笔墨既要随自然之变,更要随时代之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给中国画坛带来了全新命题:如何让传统国画表现新社会的风貌?有人认为国画只能画古松高士,有人尝试用传统笔墨生硬拼接工厂烟囱,傅抱石却提出:’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不是丢了笔墨,是让笔墨长出新的筋骨。’
1959年,人民大会堂需要一幅表现’江山如此多娇’的巨幅山水画,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定傅抱石与关山月合作。这幅高5.5米、宽9米的作品,要在有限的空间里展现中国山河的壮阔,还要体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时代气象。傅抱石打破传统山水’一角构图’的局限,采用’全景式构图’:左侧画东北的林海雪原,白雪皑皑中藏着苍松的绿意;右侧绘江南的青山绿水,梯田层层间映着杜鹃的嫣红;中间以黄河、长江贯穿,云雾缭绕中露出长城的轮廓。更妙的是他对’光影’的处理——传统山水多以墨色分阴阳,他却在水墨中调入淡赭石,模拟日出时’霞光映山河’的效果,让画面既有传统的雅致,又有新时代的明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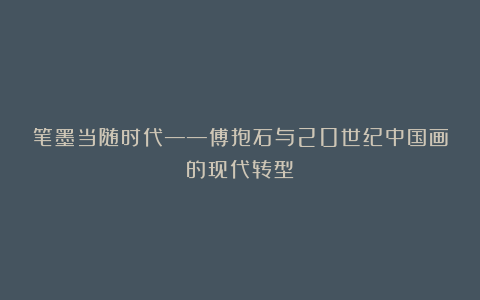
这幅画完成后,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字’江山如此多娇’,如今悬挂于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成为新中国美术的象征。但傅抱石并未将此视为终点,他深知’笔墨变’的根基是’生活变’。1960年,他带领江苏省国画院画家开展’二万三千里写生’,从江南水乡到西北高原,从煤矿工地到农田地头,他一路走一路画,笔记本上记满了’煤矿的烟囱如何用焦墨表现”梯田的线条要学老农插秧的节奏’。
在抚顺煤矿,他创作《煤都壮观》:画面下方是乌黑的矿坑,用’焦墨皴’画出煤层的厚重;上方是高耸的烟囱,以直线勾勒出工业的挺拔;中间用淡墨画工人的身影,虽小却如脊梁般直立。他说:’以前画山是’搜尽奇峰’,现在画烟囱也要’搜尽生机’——煤矿的烟不是污染,是新中国的烟火气。’在东北镜泊湖,他画《镜泊飞泉》:用’抱石皴’的晕染技法表现瀑布的水雾,却在水潭边画了两个穿工装的游客,草帽上的红五星在水墨中格外醒目——传统的’飞泉图’多画隐士观瀑,他却让新社会的劳动者成为画面的主角。
这次写生让傅抱石总结出’游、悟、记、写’的创作方法论:’游’是走进生活,’悟’是感受时代,’记’是捕捉细节,’写’是笔墨表达。他带学生写生时,从不让照搬自然,而是要求’画眼中景,更画心中情’。在韶山写生时,他画《韶山冲》,不刻意渲染建筑,而是用浓墨画韶山的松柏,说:’松柏是韶山的骨,这骨里有共产党人的气。’这种将时代情感融入笔墨的创作,让他的’新山水画’有了灵魂。
傅抱石的卓越,不止于绘画创作——他是美术史论家、教育家,更是篆刻家,多维的艺术视野让他的笔墨有了更深厚的根基。他曾说:’画是’表’,史是’里’,不知史,画便成了无根的花。’
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出版了《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以’社会变迁看绘画变迁’的视角重构美术史。他提出:’汉代绘画的雄浑,是因国力强盛;魏晋绘画的飘逸,是因玄学盛行;宋代绘画的精致,是因士大夫文化成熟。’这种将艺术置于历史语境中的研究,打破了传统画论’重品藻、轻分析’的局限。他对顾恺之《画云台山记》的考证、对谢赫’六法’的现代解读,至今仍是美术史研究的经典文献。1957年,他出版《中国古代绘画之研究》,书中既有对笔墨技法的细致分析,也有对艺术家精神世界的深度挖掘——他写八大山人,不只说其’白眼向人’的笔墨,更说’那白眼是对山河破碎的痛’;他写吴道子,不只谈其’吴带当风’的线条,更谈’那线条里有盛唐的气象’。
在教育领域,傅抱石是’授人以渔’的良师。从中央大学到江苏省国画院,他讲课从不用讲义,常带学生在画室看他作画:’你们看我画山,不是学我怎么运笔,是学我怎么看山——看山的阴阳,看山的呼吸,看山和人的关系。’他反对学生模仿自己的’抱石皴’,说:’我的皴法是金刚坡的山教我的,你们的皴法要让你们走过的山教你们。’画家亚明曾回忆:’傅先生带我们写生,见我总模仿他画竹,他夺过我的笔,在纸上画了棵歪脖子树,说’画你想画的,哪怕画歪了,也是你的’。’正是这种尊重个性的教育理念,培养出了一批新金陵画派的中坚力量。
篆刻是傅抱石艺术的’隐线’,却藏着他笔墨的密码。他少年学刻章,初学浙派的方劲,后融皖派的灵动,又将绘画的笔墨意趣注入篆刻。他刻’抱石斋’印,’抱’字用圆笔,如毛笔的中锋勾勒;’石’字用方笔,似’抱石皴’的棱角;’斋’字留白透气,如画面的虚实相生。他说:’篆刻是’方寸里的山水’,一刀下去,要像画一笔那样有浓淡、有节奏。’这种将篆刻与绘画打通的思维,让他的笔墨线条既有金石的硬度,又有水墨的柔度——看他画人物衣纹,线条如刻石般劲挺,又如水墨般流畅,正是’书画印同源’的生动体现。
1965年9月29日,傅抱石在南京逝世,享年62岁。他的人生不算长,却如一部浓缩的20世纪中国画转型史:从传统画坛的’破壁者’到新山水画的’开创者’,从战火中的’呐喊者’到新时代的’歌者’,他始终用笔墨回应着时代的呼唤。
他的作品里,藏着一个艺术家的赤诚。画《屈原》时,他为了体会’上下而求索’的心境,在金刚坡的夜里独自行走,看星月在云里穿梭,说’屈原的孤独,是所有求真者的孤独’;画《抢渡大渡河》时,他走访老红军,听他们讲当年的激战,画面里的浪涛用’焦墨’横扫,说’这浪是战士的血化成的’;画《虎踞龙盘今胜昔》时,他站在南京长江大桥工地,看工人挥汗如雨,用’湿墨’画新楼的轮廓,说’这墨里要透着新中国的光’。
他的影响早已超越时代。如今的中国画坛,无论是写意山水的笔墨探索,还是主题创作的时代表达,都能看到他的影子。南京傅抱石纪念馆里,《江山如此多娇》的复制品前总有观者驻足,人们看的不只是笔墨的酣畅,更是一位艺术家如何让传统艺术在新时代’活’起来。正如他曾说:’我不想做画史上的’过客’,我想做笔墨的’桥’——让古人的笔墨走到今天,让今天的笔墨走向明天。’
傅抱石的一生,是对’笔墨当随时代’最好的诠释:时代不是笔墨的束缚,是笔墨的土壤;传统不是笔墨的枷锁,是笔墨的根脉。他用62年的艺术实践证明:真正的艺术家,既能在传统里挖深井,也能在时代里种新花。当我们再看他的画,看《林海雪原》里的苍松,看《天池林海》里的云涛,看《镜泊飞泉》里的浪花,会明白:那些笔墨里藏着的,不仅是山河的美,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那是永远向上、永远求真、永远与时代同行的力量。这力量,便是傅抱石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
乙巳年春 张占峰于京华云海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