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七年,汴京以西百里外的官道上,尘沙卷着枯叶打在李清砚的青布长衫上。这位年仅二十的书生紧了紧背上的书箧,望着被暮色吞噬的岔路,喉间泛起干涩 —— 他已在这片丘陵绕了三日。
行囊里的干粮见了底,腰间的水囊只剩半袋。恍惚间,他想起临行前老父塞给他的那卷泛黄《异闻录》,其中一页记载着 “秦溪之南,有桃林三百亩,林尽水源,得一洞,入则异世”。当时只当是古人妄言,此刻却见前方山坳里竟真的浮起一片绯色云霭,风过处,隐约有落英如雪。
后来汴京的古籍馆里,抄书吏们常会说起这段奇遇。他们说李清砚并非第一个误入桃源者,却偏偏是那个撞破了时间玄机的人。就像檐角的铜铃,总要等到某个特定的风向,才能摇响被遗忘的旧音。
第一章 洞开时见避秦村
李清砚是被一阵孩童的笑声拽进现实的。
穿过那片遮天蔽日的桃林时,他的指尖还沾着花瓣的甜香。洞口仅容一人侧身,石壁上布满湿漉漉的苔藓,仿佛刚被晨露洗过。待他踉跄着钻出洞口,眼前的景象让他攥紧了书箧 ——
田垄如碧绸铺展,农人驱着水牛犁地,牛铃叮咚;溪边有浣衣的女子,鬓边簪着淡粉桃花,笑声脆如银铃;远处茅舍炊烟袅袅,檐下晾晒着素色麻布,竹篱笆上爬满紫色的牵牛花。更奇的是村民的衣着,竟带着秦汉时的宽袍大袖,见了他这青衫儒巾,也只是含笑点头,并无半分惊奇。
“客官可是迷路了?” 一位挎着竹篮的老丈递过一块麦饼,饼上还印着桃花纹,“前面就是我们桃花村,进来歇歇脚吧。”
李清砚接过饼的手微微发颤。他寒窗苦读十余年,熟知历代典章服饰,可眼前这些人的衣袂飘飘,分明是《史记》里记载的形制。更让他心惊的是,田埂上插着的木牌,刻着的竟是早已失传的大篆。
村中央的老槐树下,白发老者们围坐弈棋,棋子是圆润的桃核。见他来,一位老者抬眼笑道:“秦末避乱至此,不觉已数百年。客官既来,便是缘分。”
李清砚喉头滚动,终于问出那句:“敢问老丈,今夕是何年?”
老者捻须大笑:“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只记得初来时,外面正闹着焚书坑儒呢。”
焚书坑儒?那已是近千年的事了。李清砚望着满地灼灼桃花,忽然觉得书箧里的科举文章,竟比这花瓣还要轻飘。
第二章 桃花源里不知岁
李清砚在桃花村住了下来。
村民们待他极好,将东头的空屋打扫出来,窗台上每日都换着新鲜的桃花。他教孩子们识简体字,帮农人们记录收成,渐渐忘了汴京的功名,也忘了来时的路。
村里有个叫阿禾的姑娘,总爱坐在他窗下的石阶上绣桃花。她的指尖灵巧,丝线在素绢上勾出的花瓣带着晨露的润意。“李大哥,你看这朵像不像今早落在你砚台上的那朵?” 她仰起脸时,鬓边的绒毛会被阳光染成金粉色。
李清砚的心,就像被春风吹软的泥土。他开始跟着阿禾学酿桃花酒,看她将新采的花瓣撒进陶罐,说要等 “满了三个花期” 才能开封。他以为 “三个花期” 不过三载,却不知桃源的日月,原是按另一种刻度流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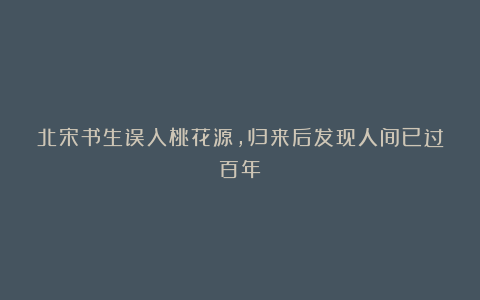
那日他在溪边浣纱,见水面漂来一片枯叶,忽然想起老父的病,想起书箧里那封未寄的家书。夜里辗转难眠,他披衣走到村口,那道曾让他进来的洞口竟隐约透着微光。
“想走了?” 阿禾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手里捧着那坛刚开封的桃花酒,酒液泛着琥珀光,“我知道你不属于这里。人间的烟火,终究是你的牵挂。”
李清砚接过酒坛,一饮而尽。酒液入喉,带着说不清的甜与涩。“我还能回来吗?”
阿禾摇摇头,将一块桃花木牌塞进他手心:“缘来则聚,缘去则散。你若回头,便再也寻不见这桃花了。”
第三章 出洞方知岁月改
钻出洞口的刹那,李清砚被刺目的阳光晃得睁不开眼。
身后的洞口轰然合拢,再回头时,只剩陡峭的石壁和几丛干枯的荆棘。他慌忙摸向手心,那块桃花木牌已变得冰凉,上面的纹路竟像被岁月磨平了一般。
官道上的尘沙依旧,却不见了来时的荒僻。远处传来车马声,他迎上去,见一辆装饰华丽的马车驶过,车帘掀起的瞬间,他看见车内女子穿着的襦裙 —— 那是他从未见过的款式,领口绣着繁复的缠枝莲。
“敢问小哥,此处离汴京还有多远?庆历七年的秋闱……” 他话未说完,便被赶车的壮汉打量怪物似的瞅着。
“庆历七年?那是多久的老皇历了!” 壮汉啐了口唾沫,“如今是元祐三年,小哥怕不是睡糊涂了?”
元祐三年。李清砚只觉天旋地转 —— 从庆历七年到元祐三年,竟是整整四十六年?可他在桃源明明只住了不足两载。
他跌跌撞撞地往家的方向走,却见记忆中的村落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陌生的庄园。守门的老仆听他报出父亲的名字,摇着头说:“老主人?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早入土啦。他儿子李二郎,十年前也迁去江南了。”
李清砚踉跄着后退,撞在门柱上。他想起临行前老父咳着血说 “等你金榜题名”,想起书箧里那封写了一半的家书,字里行间全是少年人的意气风发。
街角的酒肆里,说书人正讲着 “前朝庆历年间,有书生误入桃源,归来时已换人间” 的故事。座中有人笑骂 “荒唐”,有人举杯叹 “若真有那样的地方,倒不如不回来”。
李清砚站在人群外,手心的桃花木牌已凉透入骨。他忽然明白阿禾那句话的意思 —— 有些牵挂,一旦被时间碾碎,便成了剜心的利刃。
汴京的雪落了又融,转眼又是三十年。
人们常看见一位白发老者,拄着拐杖在城南的桃林里徘徊。他的长衫洗得发白,怀里总揣着一块光滑的木牌,谁也说不清上面刻着什么。
有人说他是前朝的遗老,疯了;也有人说他就是当年那个传说里的书生,在等一朵不会再开的桃花。
元符三年的春天,桃林里开出一株奇异的桃花,花瓣半边绯红,半边雪白。老者坐在花下,就那样睡着了。村民们发现他时,他怀里的木牌上,终于显出一行模糊的字:
“人间百年,不及桃源一春。”
后来那片桃林被一场大火烧尽,灰烬里竟挑出几块桃花纹的陶片,形制与秦代的瓦当一般无二。而关于李清砚的故事,便随着说书人的铜板声,在汴河两岸流传了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