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8年冬天,北大荒的天气冷得刺骨,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生疼,就像恋人们离别时那般刻骨铭心。
这天,周远接到回城通知,欣喜若狂之余,第一时间告诉了女友沈月,二人相约在知青宿舍外的柴垛旁会面。
两人面对面站着,沈月双手不停地摩挲着衣角,眼睛里满是不舍,话未出口,眼眶已经红了:“周远,这一去,你……你还能回来不?”
周远伸出右手,轻轻擦去沈月眼角的泪,安慰道:“小月,你别哭,我回北京处理完家事,一定马上回来接你,你放心就好了。”
说完,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用旧布包着的小物件,递给沈月:“你看,我把家里传了两代的银镯子带来了,你先收好,等我回来那天,就用它当聘礼娶你。”
沈月接过镯子,也从兜里掏出一块绣着并蒂莲的手帕,塞进了周远手里:“手帕你带着,看到它就像看到我一样,我,我等你回来。”
周远眼含热泪,紧紧攥着手帕,突然张开双手,一把抱住了沈月。沈月也伸手搂住他的腰,脸蛋贴在他的胸口,任由泪水静静流下脸颊。
两人就这样在寒风里站着,谁都不说话,只听得到彼此的心跳声和呼啸的风声。
过了好一会儿,有人打着手电筒朝这边走来。周远赶紧松开沈月,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说:“小月,等我,记得一定要等我。”
沈月用力点点头,看着周远转身走进黑暗里,直到再也看不见,才慢慢走回了村子。
谁也想不到,他们这一次匆匆离别,竟成了今生最后的告别。
周远回到北京后,不久被安排进了一家国营机械厂工作,每天朝九晚五,日子过得倒也充实。
他下班回家后,不是惦记着给沈月写信,诉说思念之情,就是呆呆坐在家里,期盼着沈月的回信。临睡前,他还会把那一块藏在枕头底下的沈月送的绣着并蒂莲的手帕,拿出来看一会儿才安心入睡。
这天,周远下班回家,刚走进院子就听见母亲喊道:“小远,快来,今儿有你的信!”
他顿时心里一喜,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一把接过信揣入怀里,兴冲冲地回到自己的卧室。看到信封上沈月那熟悉的字迹,周远迫不及待的打开来读,脸色却瞬间变得惨白。
沈月在信里写道:“周远,我已经变心了,找到更合适的人了,你别再来找我,咱们也别再联系了……”
周远的眼睛死死盯着信上的每一个字,反复读了十几遍,这才相信是沈月亲笔写下的“分手绝交信”。
他颓然坐在床上,喃喃自语:“不可能,小月,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然后把信揉成一团,又展开读一遍,再揉成一团,来来回回很多次……
最后,他把信撕成了碎片,用力扔在了地上,转身扑倒在床上,蒙着头开始低声抽泣。
母亲在客厅听到了哭声,走到门外敲门:“小远,你怎么了?小远,发生了什么事?”
“妈,我没事儿。”周远带着哭腔回应道,“今天上班太累了,休息一会儿就好。”
“哎,这孩子,”母亲摇摇头走开了,“这么大个人了,干活累点都要哭鼻子,真是的。”
从这天起,周远再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沈月,永远把这段感情连同撕碎的信一起,埋葬在了自己心底最深处。
二
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春风,吹进了千家万户,人们喜笑颜开,纷纷张开怀抱迎接新生活。唯有周远的生活,却像被按了暂停键,仍然沉浸在古旧的回忆里。
每天清晨,他都会把沈月送的那块绣着并蒂莲的手帕,轻轻叠好,塞进上衣内袋,仿佛这样就能把那段美好的回忆带着。
周远性格温和,踏实勤奋,机械厂的工友老张挺欣赏他,于是想着给他牵线做媒:“小周,京西纺织厂新分来的姑娘水灵着呢,周末一起去吃个饭吧?”
周远却予以婉拒:“不了,我周末约了朋友去钓鱼,还是下次吧。”
时间一年年过去,周远从车间学徒终于熬成了技术骨干。
同事们给他介绍对象的频率,从每月几次变成每年几次,最后连最热心的王阿姨都直摇头:“这孩子,心里怕是住了一座坟,只有他自己才能走出来,否则……”
1996年,父亲临终前,攥着周远的手,浑浊的眼睛里满是遗憾:“小远,别再等了,开始新生活吧。”
周远低头盯着父亲手背上的老年斑,欲言又止,不停点头,然而生活却依旧如故。
2004年,母亲也走了,临终前看着周远泪眼婆娑:“傻孩子,你怎么就不听劝呢?往后的日子,你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唉,没个伴儿,我走了也不安生呐。”周远含泪拼命点头,握着母亲的手忍不住号啕大哭,久久不愿松开。
此后,周远会把北大荒的照片整齐摆在书桌的抽屉里,褪色的手帕叠得方方正正放在最上面。
每个加班的深夜,他都会倒一杯凉白开,就着台灯的光翻看照片,直到困意袭来,才和衣睡去。
2013年,已经退休的周远终于有了闲余时间,他鼓足勇气,买了一张前往北大荒的火车票,想着去看看以前的乡亲们和沈月,想知道她现在的生活近况。
三十多年过去了,周远再次踏上北大荒的土地,恍如隔世,眼前的砖瓦房代替了记忆中的茅草屋,村口的老槐树却还在,只是树干上多了几道深深的裂痕。
“大叔,您找谁?”一个清脆的女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周远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剪着短发的中年女子,正推着自行车站在他后面,车筐里装着刚摘的豆角。
周远对着她微笑,张了张嘴,声音沙哑得连自己都吓一跳:“我……我以前在这儿插队。”
女子上下打量他几眼,指着远处的砖房说:“那您可得找李主任问问,他会比较熟悉。”
周远刚想说“谢谢”,一抬头看见那个女子已经骑上自行车,回头对他说道:“您去找他吧,我还有事,就不带你过去啦。”
周远冲着她挥手点头,提着行李向李主任家走去,远远看见晒谷场旁边的墙根下,几个老人坐在一起聊闲嗑。
等他走近了,其中一位颤巍巍站起来,眯着眼端详他:“你是小周?真的是小周!”
“您……您是李主任?”
“我是李福田,”老人布满皱纹的手紧紧抓住他的胳膊,“你可总算回来了,这都多少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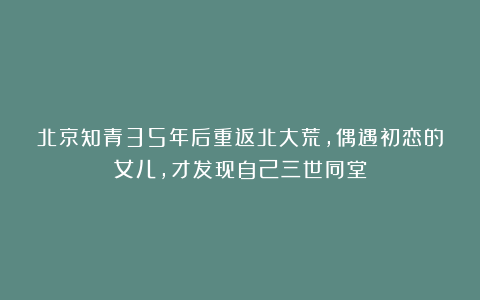
当下,两人忍不住长吁短叹,边走边聊进了屋喝茶,继续聊着往昔岁月,这些年村子里的巨大变化。
夕阳西下,不知不觉天就黑了,周远挡住李主任的热情招待,晚上就在他家里住下了。
三
第二天一大早,周远就跑去了集市上,想着买点水果之类的礼物,借此谢谢李主任的款待。
他漫无目的地逛了一圈,买好了东西往回走,路过一处菜摊前,看到昨天指路的女子。她正在低着头熟练的分拣豆角,扎成一捆捆摆到摊位上,而她戴着手腕上的银镯子似曾相识……
周远不由放慢了脚步,呼吸几乎停滞,这个女子,怎么越看越像记忆里的初恋情人沈月,只是比当年的沈月要“老”上一些。
“大爷,是你啊。”女子察觉有人注视她,抬头看是周远,主动搭话,“您要买什么菜呢?”
周远这才回过神来,走近仔细端详她手上的物件,喉结动了动:“你、你这银镯子……”
女子低头看了一眼手腕:“哦,这是我妈留给我的……刘大妈,你这么早就来了,今天想买点什么?”
“你妈叫什么名字?”周远忍不住问道,满脸期待着等着回应。
“叫沈月,您认识她吗?……刘大妈您要多少,我这就给您称。”女人转头继续招呼顾客。
周远顿时愣在原地,菜摊前又围过来六七个买菜的妇女,瞬间就把他硬生生挤了出去。
“欢迎您去我家做客,大叔。”女人站在人群里,朝他大声喊道。
周远没有回答,转身提着东西,快步离开了集市。
回到李主任家里,堂屋里飘着玉米粥的香气,王婶手里拿着擀面杖跑出来:“小周,你跑去哪里了?你福田叔到处找你呢?哎呦,你说你去买什么东西啊,这孩子!”
周远放下东西,连忙抓住她的胳膊:“王婶,我问您一件事,咱村那个叫沈月的姑娘你还记得不,她,她后来嫁给谁了?我在集市上看到她女儿了。”
王婶的身体突然僵住,拉着周远在木凳上坐下:“那是小芳,沈月的闺女。沈月走了十几年了,肺癌。临终前还攥着你的照片……”
周远立刻如遭雷击,顷刻间耳朵嗡嗡作响,得知沈月的坟地在村后的山坡上,魂不守舍地独自前往。
墓碑前,周远的手指轻轻抚过“沈月”两个字,简陋的石碑,冰凉的触感,让他禁不住眼眶发烫。
“小月,我回来了。”他从兜里掏出褪色的手帕,轻轻放在墓碑前,“当年我真该再等等……”
四
下午,周远走进了沈月闺女小芳的家里,提出想去看看以前沈月住的老房子。
小芳看着这个远方的来客,越发觉得似曾相识,心里也掂量出了分量,她压抑着内心深处翻涌的情感,故作平静地领着周远打开了老房子的木门,只见堂屋墙上,还挂着他临走前拍的合影,照片的边角卷起,玻璃上蒙着一层薄灰。
“这些年我定期来打扫。”小芳说着走进卧室,不久抱着一个旧樟木箱出来。打开后,樟脑丸的气味混着旧布料的气息扑面而来。
她把上面叠得整齐的蓝布衫一件件取出,然后取出最底下压着的一本线装日记本。
周远伸手接过,翻开日记本,发现中间突兀地缺了几页,断裂处参差不齐,而本子里都是沈月生前写下的尘封往事。
“1978年12月20日,晴。今天偷偷去看周远的宿舍,他窗台上的冰花又结了新的形状。”
“今天,爹爹拿着农药瓶,愤怒地砸在墙上,说我再等周远的话,就立刻打断我的腿。”
“小芳终于会翻身了,眼睛特别像你,总爱盯着窗户看,是不是在等爸爸回来呢?”
……
周远正泪眼婆娑地看得出神,突然耳边传来小芳的叫唤:“我是该叫你爸吧,爸,这是妈妈临终前给您写的信。”
周远猛地抬头,有些吃惊的看着小芳,老花镜滑到了鼻尖,露出布满血丝的眼睛。
小芳含着眼泪蹲下来,递给他一个好似当年“分手信”的信封,然后把憋了三十年的话说完:“我等了好久,终于能叫你一声爸。”
周远颤抖着接过,展开信纸,真的是沈月的字迹:“周远,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小芳找到你了。当年我拗不过父亲,违心给你写了信,其实撕碎真心的不是我啊,是那个时代。这些年来,我一直守着秘密,守着咱们的女儿,从来也不曾后悔。只盼你别像我一样,别把自己困在回忆里……”
“我该早点回来的。”周远伸手将小芳的头揽在怀里,声音呜咽,再也说不出话了。
不久,父女俩停止哭泣,回到了小芳和丈夫盖的新房子里。
周远坐在褪色的布艺沙发上,膝盖上摊着日记本,听着女儿小芳回忆当年往事。
“当初你走后妈妈才知道自己害了喜,开始还偷偷摸摸的,自从生下我后,日子过得特别难,因为队里总有人在她背后指指点点,说她未婚生子。姥姥姥爷也气她不听劝,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跟她来往,也不允许别人帮她。”
周远捏着茶杯的手紧了紧,茶水在杯中轻轻晃荡,心里更加难过了。
小芳继续说道:“那时候有好几个男人托人来说媒,条件都挺不错,说不介意她带着孩子,但是妈妈都拒绝了,说是自个儿心里装不下别人,也不能坑了别人。”
“为了供我上学,妈妈什么零工都抢着干,年纪轻轻就患上了肺癌,生活就更加困难了。”
“有一次农场小学招民办老师,本来都要录取她了,可有人说闲话,怕影响不好,最后名额给了别人。她只能继续在地里干活,每天回来还要给我补习功课……”
周远听着听着,眼眶红了,赶忙别过头去,偷偷抹眼泪,不想让小芳看见自己的脆弱。
小芳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突然就哭出声来:“妈妈总说,等我长大了,要是能找到你,就告诉你,她从来没有变心,现在,我终于能说了。”
周远站起身,伸手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发,就像三十多年前他摸沈月的头发那样。
突然,院子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大门被猛地推开。
“妈,我回来了。”一个十几岁虎头虎脑的男孩冲进了屋,把书包放在桌子上,“咋回事,你咋还哭了?他是谁?”
小芳抹了眼泪,笑着把孩子拉到身前:“这是你姥爷,快叫。”
男孩眨了眨眼睛,有些害羞地喊了声:“姥爷好。”
周远一下子愣住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涌上心头:“乖孩子。”手轻轻摸了摸外孙的小脑袋,声音有些哽咽,然后把他揽在身前。
周小芳看着父亲和儿子,也擦干了眼泪,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周远望向窗外,突然想起沈月日记里写的一句话:“等待的尽头,总会有新的开始。”
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洒进来,霎时间给屋里的三个人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