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亩麦子总算进了仓,周明轩站在仓房门口,望着满囤黄澄澄的粮食,心头却沉甸甸坠着铅块。往年每到此时,那仇家陈大河必如鬼魅般现身,一把火烧尽周家积攒的希望。如今这仓里堆着的,是他周明轩最后的本钱,也是他周家重新立足的命脉。他不敢松懈,更不敢遗忘。
夏税、徭役银,该交的都咬牙交了,像从身上硬生生剜下几块肉。又卖了几石麦子,才凑够钱,将丘世裕家借来的七八个长工一一结算清楚,送还回去。老管家周忠佝偻着背,很快重新雇来了五个手脚麻利的短工,又添了两个看着老实的长工。
祖宅也终于修葺一新,青瓦覆顶,木柱新漆,院墙补得严丝合缝,连大门那对锈蚀的铜环也换了新的。周明轩站在焕然一新的宅门前,指尖拂过新漆的廊柱,一丝木刺扎进指腹,微疼,也真实。仿佛这祖宅的生气,终于重新回到了周家血脉里。
然而,他心头的硬刺始终未除。“陈大河……”周明轩喃喃自语,这个名字在他心里盘踞太久,几乎成了他夜里惊醒的梦魇。他并非未曾想过复仇,可眼下这点家业,实在经不起半点折腾了。
他疲惫地闭上眼,那场大火烧毁的不仅是粮仓,还有他父亲,以及周家最后的气运。他清楚记得父亲临终前攥紧他手腕的枯瘦指节,还有那双死死盯着仓房焦黑残骸、不肯闭上的眼睛。
“少爷,”周忠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汤饼进来,轻轻放在桌上,小心道,“仇要记,日子也得过。陈大河那头犟驴,咱们……总不能世世代代这样耗下去吧?冤冤相报,何时了结?”
周忠的话像一颗投入死水的小石子,在周明轩心里荡开一圈圈涟漪。是啊,无休止的仇恨,何时能了结?他沉默良久,望着窗外院中那棵老槐树浓密的枝叶,半晌,终于开口,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忠伯,你……明日去陈秋生的石料厂请个好石匠。另外,再找个懂堪舆的先生!”
“少爷的意思是?”
“陈大河那姑娘……葬在野狐坡吧?”周明轩的声音低沉下去,“给她……换个地方,寻块向阳的好地界,立块像样的碑!”
周忠浑浊的老眼骤然睁大,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家少爷,嘴唇哆嗦了几下,终究没再说什么,只是深深作了个揖,转身时,用衣袖飞快地抹了抹眼角。
野狐坡的风,带着平原特有的尘土气。陈家姑娘的小小坟冢,在荒草萋萋的坡地上显得格外孤伶伶。石匠们叮叮当当凿着青石,新挖的墓穴旁,一具薄皮棺材静静躺着,里面是收敛起的陈家姑娘的骸骨。
周明轩亲自来了,他站在几步开外,看着石匠们将一块打磨得光滑的青石碑稳稳立在新砌的坟冢前。碑上刻着“陈氏女桂花之墓”,没有立碑人姓名。他默默看着,心中五味杂陈。
他走上前,对着那方崭新的、尚散发着泥土与石粉气息的墓碑,深深一揖。那一刻,仿佛有千钧重担从肩头卸下些许。他低声道:“陈桂花,安心去吧。你爹与我家的仇怨……今日,算是我周家先了结这一桩!”
新碑竖立,周明轩心头却并未轻松多少。陈大河那头倔驴,会领这份情吗?还是把这修缮当作一种新的羞辱?他不敢想。仓里的粮食,依旧是悬在头顶的利剑。
“忠伯,”周明轩回府后立刻吩咐,“趁着天好,把仓里的麦子都搬出来,过过风!”
“少爷,您这是?”周忠有些不解。
“不能放一处!”周明轩斩钉截铁,“粮商刘太平,刘成文,还有丘家,都熟。你亲自去跑一趟,就说我周明轩租他们的仓廒存粮,按行市给廒租。家里的仓房,只留够一个月嚼用的!”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院中那几个新雇的短工,“还有,跟雇来的人说清楚,夜里轮值,多添两盏灯笼,巡夜勤快些。灶房柴禾,离仓房远些堆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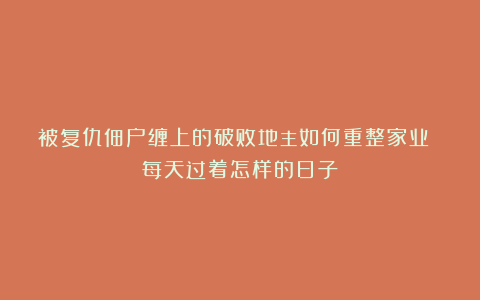
周忠一一记下,忍不住道:“少爷,您这心思……缜密得紧。只是这般分散存放,廒租加上脚力钱,损耗怕是不小!”
“损耗总比一把火烧光了强!”周明轩苦笑,“这点钱,咬咬牙也得花。家里这点存粮,够吃就行。耗子都比咱存得多,那陈大河真要来,也烧不了什么值钱东西!”
周家宅院的日子,在周明轩小心翼翼的布置下,仿佛被重新拧紧了发条。新雇的长工每日早起,踏着露水去巡视佃户的田地和周家自留的二百亩园子。
短工们则在老管家周忠的指挥下,洒扫庭院,担水劈柴,灶房里日日烟火不断。周明轩自己也常在田间地头走动,查看苗情,与佃户说几句话,身上那点破落少爷的浮华气,渐渐被泥土和日头磨去了棱角。
一日午后,周明轩刚从地里回来,在堂屋坐下喝了口粗茶,门外便传来马蹄声。丘世裕那标志性的大嗓门在院门口响起:“明轩!明轩!出来迎客!”
周明轩放下茶碗,迎出去。只见丘世裕翻身下马,后面跟着一辆青篷小车,车帘掀开,露出王世昌那张永远带着和气生财笑容的圆脸。两人都穿着簇新的绸衫,与周家这刚修缮过、尚透着简朴的宅院有些格格不入。
“哟呵!”王世昌大步流星走进院子,环顾四周,厚实的大手用力拍在周明轩肩上,拍得他一个趔趄,“行啊你小子!这宅子拾掇得真不赖!有点你爷爷那会儿的气派了!麦子都安顿好了?”他嗓门也大,毫不避讳。
周明轩引二人进屋,吩咐小柱子倒茶:“托二位的福,麦子收了,税也交了,借的工钱也清了,宅子勉强能看了!”他略过修坟和散粮的事,只拣些面上的话说。
王世昌捻着几根稀疏的胡须,笑眯眯地接口:“贤弟能立起来,我们看着也高兴。这田产家宅就是根本,守住了根本,慢慢经营,总有复起之日!”他啜了口茶,话锋一转,声音压低了些,“只是……那陈大河?近来可有动静?”他小眼睛里闪着精明的光。
丘世裕一听,眉毛立刻拧了起来,天不怕地不怕的眼神看向周明轩:“那老贼还敢来?你跟我说!我丘家庄丁族兵有的是人手!他敢露头,打断他狗腿!”
周明轩心中一暖,随即是更深的苦涩。他摇摇头:“世裕兄好意心领了,他……近来没动静!我也只求个安稳,井水不犯河水罢了!”他不想多提,更不愿让这两位仗义的朋友再为自己卷入这无解的仇怨。
丘世裕的大嗓门和拍胸脯的保证,王世昌那关切又带着精明算计的探问,都像投入深潭的石子,短暂地搅动了一下,旋即又沉入他心底那片名为“陈大河”的冰冷水域。
送走两位好友,周家的院子重归寂静。周明轩独自站在修缮一新的堂屋门口,望着夕阳给青瓦涂上一层暖金。老管家周忠轻手轻脚地走过来,欲言又止。
“忠伯,有话就说!”
“少爷,”周忠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种秘而不宣的意味,“昨儿个……我寻个由头,又去了趟野狐坡!”
周明轩的心猛地提了起来,转过身,紧盯着老管家。
“那坟……新坟,”周忠舔了舔有些干裂的嘴唇,“跟前……有新烧过不久的纸钱灰,风还没吹干净。供着的那碟果子……最顶上那个,像是被人……被人轻轻摸过,挪了点儿地方!”
周明轩呼吸一窒,只觉得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猛地冲上头顶,眼前竟有些模糊。他死死攥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才勉强维持住声音的平稳:“你……看清了?”
“老奴不敢妄言!”周忠垂着头,“那灰烬,那果子……都看得真真儿的。旁边……旁边还有几个新鲜的脚印,不是石匠的,也不是咱们的!”
周明轩没再说话,他慢慢转过身,背对着周忠,目光投向暮色四合中模糊的野狐坡方向。那里,新起的坟冢悄然无声,如同一个沉默的回应,又像一个悬而未决的谜题。纸灰未冷,果品微移,那几枚新鲜的脚印,像无声的叩问,沉沉地踏在他心上。
长夜来临,周家宅院灯火次第亮起。周明轩独自站在院中,仰头望着满天星斗。风吹过新修的屋檐,发出细微的呜咽,像一声悠长而压抑的叹息,在太皇河寂静的夜空里,缓缓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