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1978年冬,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在昏黄的油灯下按下红手印,他们不是在反抗,而是在活命。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决定,这是一次不许失败的冒险,他们把命押在了“包产到户”四个字上。
“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现实
村口晒场上,谷堆稀疏,李老汉蹲在地头,望着收成,没说话,他干了一季,粮食却还不如前年多,他的口粮和那个年年旷工的“懒赵”一样多。
集体干活,“大锅饭”吃惯了,谁也不愿多出力,一个队三十来口人,早上锄地,下午点种,有的干得汗湿衣背,有的边干边歇,一把锄头挑到日头偏西。
“反正干多干少都那样,分不多。”这是村里人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话。
凤阳县农民开始习惯了这种“差不多”,可肚子不认,到1978年,全国还有2.5亿人吃不饱饭,凤阳更严重。
村里开始出现“打发人去城里讨饭”的现象,不是为了可怜,是为了生存,队里记账,“今天赵老五去乞讨,带回半袋糠。”写在公社记录里,堂而皇之。
李老汉的儿子偷偷种了几棵红薯,被队长发现后批评了:“这是集体地,私种是资本主义尾巴。”
可那年他家靠那几棵红薯熬过来了。
每年年初,县里下发生产计划,亩产多少,种哪类作物,写得明明白白。
可天不懂文件,雨少一月,地里开裂;虫来一夜,半田被啃光,但任务不能减,完不成就“记账、通报、批评”。
1978年冬,小岗村,18户人家围坐在破旧的祠堂里,炉火不旺,风从窗缝灌进来,没有官员,没有批文,只有一张契约。
“谁签名,谁按手印。”
“要是出事,孩子就给国家,父母给队里埋。”有人犹豫。
十八个红手印,印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他们决定:每家分地,自己种,自己交粮,剩下归己。
1979年,小岗村的粮食产量从18000公斤飙到66000公斤,人均口粮翻了几番。
“以前没人抢活干,现在天还没亮就下地。”队里不再有人偷种,也没人再去城里讨饭。
肥西县山南公社也动了,干部先是“试试看”,地分到户,产量上涨明显。
1979年,《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十个问题的试行规定》下发,文件没明说“包产到户”,却给了空间。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多种形式。”这句话成了最重要的默许。
干部下乡调研后回报:“农民干劲大了,连牛都精神。”政策开始松口。
包产到户的推广与政策突破
1980年春,北京一场内部会议,有人说包产到户是“倒退”“资本主义苗头”。
邓小平听完,只说了一句:“包产到户,不是走资本主义,是为了吃饭。”
没有长篇大论,没有反驳谁,话说完,会议静了,这句话传回各地,很多犹豫不决的干部松了口气。
同年,中央下发75号文件,头一次写明:“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的责任制形式。”
合法,定性,可推。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文件开头就写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没人再争了,红头文件在手,谁还怕?
包产到户开始迅速推进,安徽是先锋,四川、河南紧随其后,1980年底,包产到户生产队占比仅1.1%。到1982年,超过90%。
连平时最保守的老支书也动了心:“上头都定了,我们不搞就落后。”
1982年,农业总产值增长11.2%,小岗村人均收入从22元升至400元。
400元,意味着能吃米饭了,能穿棉衣了,能买农具了,很多人第一次有了存款。
县供销社的账本上,卖种子、肥料的数量翻倍,有人开始买化肥、租耕机。
“以前我们是求着卖粮,现在是挑着卖。”凤阳县粮站的账房说。
这不是简单的“分田到户”,不是“各人管自己”,地还是集体的,产权归村集体,只是经营权到了农户手里。
土地变成了“责任田”,不是“私产”,这是底线。
“这块地是村里给我的,不是我自己的,但我可以种,我可以管,我也得上交。”。
村里按合同监督,交不够,下一年可能就收回,这不是散乱,而是制度重构。
包产到户的创新性与突破性
有的人家第二年种的,不是小麦是玉米,没人拦他。没人罚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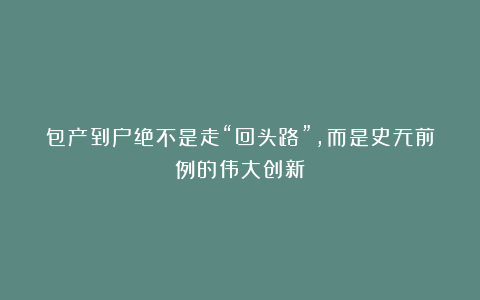
“这块地是我的责任田,我看天气、看地势、看市价,产量好,口袋鼓。”
以前,种什么作物是按文件分配的,选错了,产量跌,没人管,包产到户后,选错了,自己承担,选对了,赚得多。
人和地,重新建立了联系。
村东头的刘婶以前不会种菜,一直在队里扫院子,包干到户后,她腾出一亩地,种辣椒,卖给镇上的饭店,一个月赚十多块,比过去一年多。
“以前队里不让种,说没计划,现在我自己种,没人管,地也高兴了。”
农民开始试新种子、试农药、试水稻和玉米轮作,不是技术指导的指令,是自发的改变。
杂交水稻最早就在这种土办法里被农民接受下来。比干部宣传更管用。
村口小卖部换了新货,糖果、玻璃杯、打火机。这些原来是“供销社才能进”的物资。
现在,有人开始骑自行车去县城进货,回来摆摊。
鸡鸭鹅在村里开始自由交易,饭店多了,做酱菜、磨豆腐、烤烧饼的多了。
队里不再是唯一组织,谁能干,谁能赚钱。
“我做豆腐,一天能挣一块五,比在地里干轻松。”村民老李说。
劳动力重新分配,乡村经济开始自己找方向。
原来三十多人下地,现在只需十几人,剩下的,有人去做副业,有人去镇上办运输,有人去县里当泥瓦工。
不是政策安排的“下岗转岗”,是地里种出粮,人才敢走出去。
凤阳最早办起的缝纫小组,是几个年轻妇女凑钱买了三台脚踏缝纫机。
“我们不想下地,就想坐屋里做活。”她们说,没人反对,以前不允许,现在只要种的地交够了,谁也不多说话。
“只要不偷不抢,干啥都成。”成了乡里默认的规矩。
制度变了,规矩也跟着变了。
乡镇企业开始冒头,从最早的铁匠铺、弹棉花,到后来的砖厂、水泥厂,很多人第一次进厂干活,拿工资,不种地。
1983年,全国乡镇企业产值增长24%,没人组织,没人鼓动,是地里释放出来的劳动力自己走出去。
这不是“跑偏”,是农村经济第一次找到自己的节奏。
这不是全放,也不是全收,土地归集体,经营归农户,底线在,空间也在。
不废公有制,不搞私有地,既不跑偏,又不死守旧路。
这就是“双层经营体制”,集体经济保底,家庭承包主责。
农业部干部曾到小岗调研,回来就写报告:“这种模式能调动积极性,又不失集体控制。”
文件一出,全国照办,不是因为谁命令,而是因为农民看到了实效。
包产到户是基层先走,再由政策追认,不是先有设计,而是先有现实。
粮食上来了,心也稳了
到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4.07亿吨,比1978年多了整整一亿吨。
“以前没粮,现在卖粮。”
“再不用出门要饭了。”村支书说这句话时,眼圈红了。
农村第一次实现了“吃饱穿暖”,不是分发,不是赈济,是靠自己种出来的。
这是基层自己救了自己。
农民有了钱,买东西多了,供销社生意火了,运输多了,副业旺了。
城市商品开始向农村流通,电器、衣物、化肥,农村的钱开始向城市流动。
城市改革还没起步,农村已经自己动了。
“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节奏由此形成,城市商品经济改革,价格机制松动,都是在农村尝试成功后才敢跟进。
包产到户不只是农村的事,它推着全国动了。
1983年后,政策明确:承包制长期不变,农户稳定。
2018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再次确认:“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三十年。”
农民不再担心政策变,地种下去,就是明天的保障。
改革不是一纸文件,是一次次自下而上的探索。
当年小岗村18人签字,没有任何政策保障。只有信念:“只要种下去,总有饭吃。”
这不是回到旧社会,这是走出老路,重新找到出路。
没有演讲,没有口号,只有一纸契约,一块责任田,一个冬夜里点燃的炉火。
那些按下红手印的手,如今写进了史书,可那年,他们只想着活下去。
包产到户不是文件说出来的,是干出来的,不是退步,是前所未有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