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童兆君
暮色如纱,自湘江水面缓缓浸染开来。燕子攥着一张被手心汗水洇得发软的火车票,立在长沙火车站汹涌的人潮出口。风里裹着糖油粑粑甜腻的暖香,与地铁口吞吐的喧嚣混在一处,迎面撞上她自甘肃民乐县带来的、那一身洗不尽的戈壁风尘。空气里,顿时漾开一种无依的陌生。
三年网恋,两年音书断绝。此番南下,是她刚从另一段感情里摔得遍体鳞伤后,一次孤注一掷的出逃。消息框里,只余一句轻飘飘的:“我来长沙了,想见一面。”像扔进深谷的石子,不敢听回响。
她曾无数次在民乐县空旷的戈壁上描摹这场重逢。她想带他去看扁都口盛夏的油菜花,说“你看,这金色比视频里要灼眼得多”;她背包里那个小小的玻璃瓶,装着祁连山脚的沙粒,是她无数次思念时,弯腰拾起的见证。然而,所有滚烫的想象,都在看到他发来定位旁那句附言时,骤然冷却——“刚忙完婚礼的事,在坡子街等你。” 字字如冰,将她五年的期盼,无声洞穿。
相见处,是一家臭豆腐摊氤氲的热气旁。他穿着挺括的衬衫,袖口那枚忘了摘下的婚礼襟花,红得刺眼。看见她,他眼底掠过一丝无处藏匿的慌乱,旋即被一种妥帖的客气覆盖:“一路辛苦了,先吃碗米粉吧。”燕子的手在包里,死死攥住那个小瓶,冰凉的玻璃硌着掌心,所有预演过千遍万遍的话,都碎在喉间,最终化作碗中一片沉默的热气,氤氲了她的视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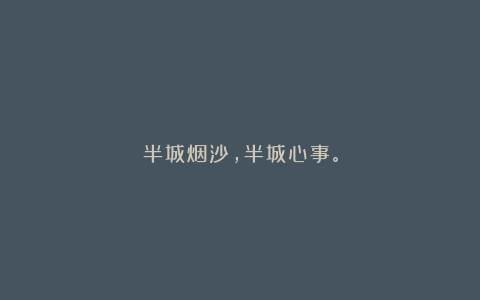
他絮絮说着别后种种:新工作,新婚的妻子,上周刚办的喜宴。手机屏幕上,婚纱照里的笑靥如花。燕子努力弯起嘴角,目光却越过他的肩头,飘向远处暮霭中的天心阁——那是从前视频时,他总指着说“以后带你来看”的地方。湘江的风裹着湿雾吹来,黏稠而温柔。她忽然想起民乐的风,凛冽、干燥,带着沙粒的金石之声,能吹散一切缠绵。而这里的风,太软,像一张无处挣脱的网。
那日后,她的微信再无声息。他去坡子街寻过,问遍她住过的小旅馆,老板只记得“那个带西北口音的姑娘,背着个装沙的瓶子,一早就走了”。有人说,在岳麓山见过她,素色裙子,蹲在落叶里像一尊安静的雕塑;也有人说,在火车站瞥见她的身影,手里攥着去张掖的车票,发梢仿佛还沾着未干的晨露与昨日的尘沙。
那日后,她的微信再无声息。他去坡子街寻过,问遍她住过的小旅馆,老板只记得“那个带西北口音的姑娘,背着个装沙的瓶子,一早就走了”。有人说,在岳麓山见过她,素色裙子,蹲在落叶里像一尊安静的雕塑;也有人说,在火车站瞥见她的身影,手里攥着去张掖的车票,发梢仿佛还沾着未干的晨露与昨日的尘沙。
长沙的暮色,依旧日复一日地将湘江染成暖昧的橘红。他偶尔会想起那个来自风沙之地的女孩,像想起一段被自己遗落的情节。他并不知道,燕子并未离去。
她在离坡子街不远的一条老巷住下,在一家花店找了份工作。每日清晨,她路过糖油粑粑的摊子,让那甜香浸透崭新的日常;每个黄昏,她回到出租屋的小窗边,将瓶中的沙粒缓缓倾倒在掌心,看它们如光阴般,从指缝间无声流泻。
她不再联系他,也未回西北。长沙的雾太浓,足以将一个人的往事与心事悄然消化。她把那半城来自祁连的沙,扬进了这半城湘江的烟沙里。所有未曾启齿的言语,所有奔流又止息的情感,都沉入两座城池交界的缝隙中,无人知晓,亦不再被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