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白求恩,脑子里跳出来的多半是课本里那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战士。但今天要说的,是一个不太一样的白求恩——他确实高尚,确实伟大,但藏在这些标签背后的,是他那双蓝眼睛里喷薄的愤怒。这种愤怒,比任何赞美都更能让我们看清那个年代的真相。
1938年的中国,战火已经烧了七年。北平丢了,上海陷了,南京的血迹还没干,八路军在山西、河北的山沟里打游击,缺枪缺炮更缺医生。就在这时候,一个高个子的加拿大人挤上了从香港到武汉的船,箱子里装着手术刀、止血钳,还有一肚子的火。这人就是白求恩。
他来中国,不是一时兴起。在此之前,他在西班牙待了一年。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佛朗哥的法西斯军队到处杀人,他带着医疗队冲过去,在前线建手术室,跟法西斯硬刚。可后来因为内部掣肘,医疗物资运不上去,伤员死在手术台外,他气得摔过手术刀。听说中国在跟日本法西斯打仗,他二话不说,放弃了北美优渥的生活,给中共驻纽约的代表写了封信:“我要去中国,因为那里的战斗更需要我。”
到了延安,毛泽东跟他聊了三天三夜。他后来跟人说,毛泽东眼里的光,跟西班牙那些反法西斯战士一样。可真到了晋察冀根据地,他看到的景象还是把他惊着了。没有消毒水,手术刀用开水烫烫就接着用;没有麻醉药,伤员咬着木棍做手术;有的战士中了枪,在山沟里躺了三四天,伤口爬满蛆虫才被抬回来。
他的第一把火,是冲着医疗队的“规矩”发的。当时有个不成文的习惯,医生给伤员换药,得先洗手。可水金贵啊,有人就用布擦擦手算了。白求恩撞见了,一把抢过那人的镊子扔在地上,吼道:“你这是在杀人!”他蹲在地上,用冻裂的手捡起镊子,亲自去河边舀水,边洗边骂:“在西班牙,我们缺这缺那,但从没人敢省消毒这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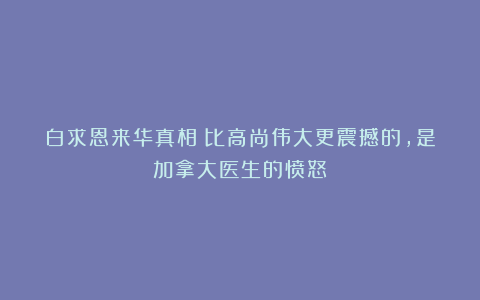
更让他窝火的是资源浪费。有一次,他发现仓库里堆着一批过期的药品,还有些绷带根本没拆封,却有伤员因为没药疼得打滚。他找到负责后勤的同志,把药箱子掀了,指着那些过期药:“这些东西能救多少人?现在它们就是垃圾!你们知道前线的战士是怎么扛过来的吗?”据说那天他气得晚饭都没吃,蹲在村口抽烟,烟蒂扔了一地。
他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里面没说多少自己的功劳,净是提意见:“医疗队的组织太乱,医生护士没经过系统培训,伤员转运要走好几天,很多人在路上就没了。”他甚至直接说:“有些同志把精力放在搞形式上,忘了我们的敌人是日本鬼子,不是伤口上的细菌。”
但他不是只发火,火发完了,他就自己动手改。没有手术室,他在破庙里垒土台,用白布当屏风;没有护士,他拉着卫生员手把手教,从怎么止血到怎么缝合,一遍不对就再来一遍,急了就拍桌子:“记不住?想想那些躺在地上的战士!”他发明了“卢沟桥”手术台,就是把两块木板架在马背上,走到哪儿就能开到哪儿;他还编了本《外科手册》,用土话写的,怕大家看不懂。
有次打伏击战,一下子送来100多个伤员。他在山洞里连做了69个小时手术,中间只喝了点米汤。助手劝他歇会儿,他眼睛布满血丝,指着外面:“歇?等鬼子打过来,想歇都没地方歇!”手术到最后,他的手都在抖,却还是咬着牙缝完最后一针。
可他的愤怒里,藏着的全是心疼。看到小战士因为没麻药,手术时咬碎了牙,他转过头抹了把脸;看到村里的大娘把仅有的鸡蛋塞给伤员,自己啃树皮,他默默把自己的罐头分给大娘。他跟战士们说:“我不是来当英雄的,我是来让你们活下去的。”
1939年11月,他在给一个大腿中弹的战士做手术时,手指被划了个口子。当时没当回事,接着做,后来伤口感染,肿得像个馒头。高烧不退的时候,他还在改医疗方案,说:“等我好了,咱们再建个更大的手术室。”可没等到那天,他就走了,才49岁。
毛泽东写《纪念白求恩》,说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可我们不该忘了,这个伟大的人,也曾为这片土地上的苦难愤怒过。他的愤怒,不是抱怨,是想让这里变好的急;不是放弃,是拼了命也要改变的狠。
现在提起他,我们总说要学习他的精神。可或许,真正该学的,是他那份“见不得人受苦”的愤怒——对不公的愤怒,对低效的愤怒,对漠视生命的愤怒。这种愤怒,才让高尚有了温度,让伟大接了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