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气二三十年而一变,古书亦二三十年而渐稀。——叶德辉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字国瑞, 原名朱重八、朱兴宗。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人。明朝开国皇帝(1368年—1398年在位), 年号“洪武”。
明代(1368-1644),自朱元璋1368年建都称帝,传十六帝,共计276年。初期洪武、永乐、仁宣称治,中期少有中兴,及至末期贪污盛行,吏治腐败,农民起义不断,至崇祯一朝覆亡。
明杭州容与堂刻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引首一卷》,是目前《水浒传》影印出版数量最大的版本,浙派版画。国家图书馆藏本。
在这近乎三百年的统治中,刻书事业得到极大发展。无论官刻、藩刻,抑或是私坊刻,内容丰富,质量惊人。而且,在活字、套印以及版画方面都有极大创新,达到了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度。
按时间划分,明版书可分为三期:初期洪武至正德,中期嘉靖至万历前期,后期万历后期到天启崇祯。按照刻书系统划分:内府刻、藩府刻以及其他官私坊刻书。
明刻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一百回》,每回前附图两幅,绘本回之事,为徽派著名刻工刘君裕、郭卓然所雕刻。国家图书馆藏本。
明代版刻是古籍拍卖场的中坚力量,属于金字塔的上层。在拍卖场上,受到藏家的青睐有加。明版书的价值认可与清代皇家和民间藏书家的鉴藏传统,存世量以及善本的划分标准密切相关。
早在明时,明刻并不为时人所看重,宋元版才是明代宫廷以及藏书家所喜闻乐见、倾其所有的收藏门类。
至清代开始,宫廷正统藏书——“天禄琳琅”将明版纳入主要的收藏体系,再加上民间藏书家的推波助澜,才使得明版书摇身一变,成为时代的宠儿,尤其嘉靖以前的刻本。
乾嘉时期,鉴赏巨匠黄丕烈等一批鉴赏家对明版书作进一步加持,使得明版书的价值得到肯定。
晚清民国,出现专门收藏嘉靖版而著称的藏书家,并形成一股藏书风尚,如邓邦述、吴梅、陶湘。
这种自清代以来的局面扭转,使得明版价值得到重塑,并在清末民初成为风尚,一直延续到当下。这不得不说是明版书的一场近乎几百年的嬗变。
藏书家与宫廷的鉴藏
清乾隆九年(1744),高宗弘历命内廷翰林院检阅内府藏书,选择其中善本进呈御览,并在乾清宫东侧的昭仁殿内列架收藏,取汉朝天禄阁藏书典故,御笔题匾,赐名“天禄琳琅”。
洪武元年,朱元璋建都南京,随即颁诏天下,广求古今书籍。接着,朱元璋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实堂中。洪武三年,朱元璋置秘书监,掌管宫廷藏书。明初以文渊阁、大本堂为中心的宫廷藏书体系建立了起来,宫廷藏书也日益丰富。
明永乐十七年,成祖即遣侍讲陈敬宗前往南京,取文渊阁所藏古今书籍,自一部到一百部以上,各取一部运送北京。共计取书一百柜,装船十余艘,水运到北京,“于是宋、金、元来皇家之旧藏,群集于北京之文渊阁矣”。可见,明初的宫廷藏书观念是以奉宋元旧椠为圭臬,民间藏书家亦是如此。
清初,民间藏书风气尚延续明以来的以宋元版为收藏主体,但对于明版的关注亦未曾减少。清初藏书家孙从添《藏书纪要》中列举了明刻本的版本术语二十八种,反映了当时对明刻本的鉴藏。
康熙著名藏书家徐乾学亦以收藏明版著称。徐乾学,字原一,又字健庵,昆山人,康熙九年探花,官刑部尚书。家有传是楼,藏书之富,为吴中之冠。徐氏藏书非但宋元旧本一时罕匹,即明代刊本亦收藏极富,黄宗羲辑《明文海》,煌煌巨编,阅明人文集几至二千余家,大半取自徐氏传是楼(参《四库提要·明文海》)。
乾隆时期,弘历敕建天禄琳琅,充实内府藏书,明版书占大半。官方的收藏对于鉴藏风气可谓至关重要,具有引领时代风气的功用,对后世藏书也是一种价值导向。除了极力搜求宋元旧本,珍本秘本,明版书也是购求的主要门类。
明崇祯十一年(1638)张采刻本《宋名臣言行录六十二卷》2函14册,2023中贸春拍,成交价1587万。
清宫继承明宫旧藏书籍,并长期征购,特别是乾隆三十七年下诏在全国范围内,遍征遗著,纂修《四库全书》,故而珍本善籍异常丰富。天禄琳琅藏书因作为宫中特藏,是有着极其严格的选取原则和收藏特点。在选取方面,特别注重珍本、善本,要经反复鉴别。挑选虽然严格,但近乎一半的天禄琳琅,却是明版书。
《书目前编》记载,昭仁殿曾藏明版书一百七十七种,二百五十二部,计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五卷九种不分卷,另七十五部,重本卷数不计在内。
《书目续编》记载,昭仁殿续藏明版书二百三十九种,二百九十七部,计一万零七百一十卷,重本卷数不计在内,另十七种不分卷。
清乾隆内府抄本《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以本朝代为纲,再按经史子集分成四部分,共收入宋、元、明版及影抄善本429部。国家图书馆藏。
《前编书》付之一炬,仅存后编。前后编总计藏书八百三十九种, 一千零七十七部,三万七千七百八十一卷(四十二种不分卷。)明版书综合加起来的数量几乎占到天禄琳琅的一半,是清宫藏书的主体,可谓至关重要。
黄丕烈(1763—1825),字绍武,一字承之,号荛圃,绍圃,又号复翁、佞宋主人江苏苏州人,清代藏书家、目录学家。有藏书室士礼居、百宋一廛、陶陶室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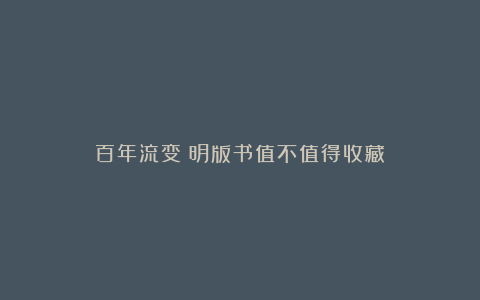
乾嘉以来,藏书家辈出,其中最杰出者是黄丕烈,他为明嘉靖本《子昂集》中提出“往文前辈论古书源流,谓明刻至嘉靖尚称善本。”的精辟论断。以赏鉴派的正统,确定了明代刻本的价值。
及至晚清民国,同时出现了一批以收藏明代嘉靖本著称的藏书家。即“百靖斋”之邓邦述,“百嘉室”之陶湘,“百嘉斋”之吴梅,其藏书楼皆以“百部嘉靖本”命名。其中,陶湘藏大约二百五十部,邓邦述一百五十部,吴梅则数量较少,未见著录。
这些现象表明,自清初以来形成对明版书的推崇,一直贯穿后世始终。人们对明版书的接受,从清初开始转变,皇家以及民间藏书家的购藏使得收藏明版书成为一股风气,至清末民国为最盛。
清代藏书家不再是用单一的文献视角来看待明版书,更多的是以一种赏鉴的心态来审视,并以收藏嘉靖以前的本子为风尚。
存世相对稀少
清嘉庆四年刻本 《文渊阁书目二十卷》。明初官修宫廷藏书目录。作于正统六年(1441),以千字文排次,分39类,著录图书7297部,本书得以窥见明永乐朝前后皇家藏书盛期全貌。
明版书存世有多少?黄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学》:“刻印过的书究竟有多少,已经难做统计,但仅就《明代版刻综录》所著录现存的已有八千多种,实际刻印过的总该达一万几千之数。”
据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上的统计数据,“有明一代,图书出版达3.5万余种,远远超过之前宋元时期的出版量。”国家图书馆研究员赵前先生著《明代版刻图典》中《明代刻书概述》一章,著述明代刻书为3.5万种。
据杜信孚《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所载,明代官方图书出版机构近300家。中央刻书机构有20余家,刻书量以内府和国子监为最。马学良《明代内府刻书考》“如果把每年刊布的《大统历》计算在内的话,明代内府刻书的数量应该在700种左右。”
明天顺内府刻本《大明一统志》,是明代李贤、彭时等撰修的地理总志。成书于天顺五年(1461年)四月,共90卷,体例源自《大元大一统志》。图片源于网络。
除了中央刻书,还有地方官刻和藩刻。明代修志之风盛行,地方政府刻书多为志书,形成了“天下藩镇州邑,无不有志”的盛况。据巴兆祥统计,明代编修的地方志共3000余种。明代各地藩王的刻本,称为藩刻。据统计,明代藩刻本达500余种,内容涉经学、史学、文学、医学、数学等。
家刻在明代刻书业中技术高、质量好。明后期,还有吴勉学、胡文焕、毛晋等,其中最著名的当为毛晋,毛晋一生共刻书600余种。
在明代出版业中,坊刻规模最大,特别是到了明中晚期,坊刻已超官刻和家刻。据相关研究者统计,明晚期坊刻通俗小说300余种,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明代版刻杂剧470种,传奇272种。这只是粗略的统计,再包括其他经史、文集等。几万种是比较准确的。
明铜活字印本 《曹子建集十卷》,三国时曹魏文学家曹植的诗赋文集。国家图书馆藏本。
关于各个时期的刻书数量所占总量百分比统计有:
“据专家、学者估计现存的明刻本中,洪武至正德间刻本约占百分之十四五;嘉靖至万历间刻本最多,约占百分之七十,这与两朝经济、文化繁荣及时间跨度较长(近一百年)有关;天启至崇祯刻本约占百分之十五六。”陈博涵《明刻本的收藏与投资》
与华夏五千年刻书相较,明代刻书数量在所有刻书中,占仅六分之一,并不十分多。
“从汉至清,共出版古籍十八万一千七百四十九部,清代出书十二万六千六百四十九部,约占总数的六成(翁长松《清代版本叙录》)。”
而明代三万五千多部,相比之下,存世量其实稀少。
冠以善本称号
关于善本的划分。按照国际的划分,各大博物馆对中国古籍是以满清入关(1644)为界限,在此之前的古籍一律为善本。而国内制定的标准则是,以乾隆六十年以前(1795)的本子,视为善本。凡是明版,毫无疑问的划入善本的范畴。
曾有资深藏友笑谑道:“凡是明版书在《中国古籍善本总目》都能查阅到。”这当然是笑话,因为不排除极少数没有来得及入编的情况,但大致能体现出学者们对明版书的注重。
于当下,明版书也一直是藏书家苦心搜索的目标,尤其是嘉靖本。明版书的这种极为“优待”,是入清以来民间藏书家、宫廷藏书和文人学者共同推动的结果。其存世稀少,为后来专家学者划定为善本,是明版书价值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