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6-20
1950年,有将近950个安徽村庄被划入山东。这场规模不小的区划调整,放到今天就是实实在在的地理和人心的双重震荡。彼时的中国,刚走过硝烟弥漫的年代,国家版图未曾彻底“定妥”,地方治理与经济发展常常要为国家大局让步。安徽和山东,本来没太多来往,地理上还隔着部分江苏,却因一次次行政命令,被拴在了同一根绳上。
安徽是什么模样?全国中部,毗邻华东——既有起伏分明的地貌,也有割据明显的人情。别看近几年合肥声势很猛,人口数量、地区生产总值皆挤进全国“前茅”,但某些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远比地理坐标上来得深。在合肥、芜湖、安庆这些城市之外,安徽的北边和南头,总有一些与主流文化若即若离的“小世界”。无论饮食、口音还是思路,总让人觉得这省份像是多张拼接的脸——北方人的爽利,南方人的细腻,都有,却始终难以融合成一个完整的轮廓。
砀山县,宿州市北边那个挨着山东的地方,本来属于江苏。可区划一来一回,几年功夫,“主人”换了三拨。回头那些归属变更的村子,成了统计表上一行行的数字。可在土地上的人却是实打实的。“昨天是江苏人,今天成了山东人,明天又摇身一变成了安徽人。”以往皇朝更迭,权力交接之后,地方行政区划也随着动荡;元明清几代,辖属更迭,但始终有一个隐形的传统作支撑——江山未稳,版图就不能死水不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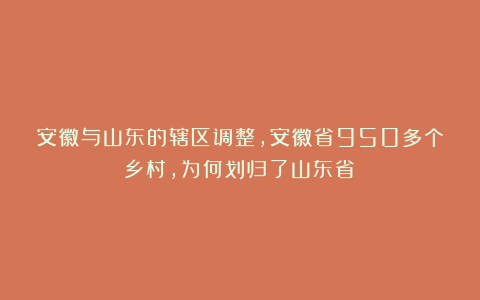
元代行省制铺开,北方土地成片地重新划分。明清时期,“直隶”一度风头正盛。南直隶,后来江南省,分家而成江苏、安徽。权力在动,地图在变。这种大格局影响之下,小地方就像棋盘上反复挪动的棋子。有一种说法——地方的安宁,从来离不开顶层设计的稳定。
20世纪中叶,地级市、县、村庄换主人,最直接的动因不是地方之间的小争吵,而是国家对经济、治水、交通的长远规划。那会儿,三省边界地带成为“调剂池”,因为管理、生产、基础建设等重任,需要一套灵活的区划来兜底。于是江苏、山东、安徽之间频繁交换地盘,徐州一度“出借”给山东,萧县、砀山县成了安徽和江苏的“飞地”,局部的行政归属拉锯反复,自下而上的社会结构却并没有随波逐流。
复杂的区划,往往是为了应对复杂的现实。建国初,萧县、砀山县的调整,是顶层治理的“实验田”。这些村庄、乡镇,被文件一签、地图一划,地理属性发生转移。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山东南部,这些地方在风土与人情上,与所辖省份并不物理契合。徐州话在砀山流行,徐州人习惯去砀山买水果,居民的适应力极强。但无论怎么交换,人们更在乎的,是田里的粮食能否丰收,孩子们能不能在最近的学校读书。安徽的村子划入山东,经济指标上多了,政策口径多了,但本地人的心理归属却未必因此一拍即合。
清末民初,区划的多次变动已成惯例。军阀混战、政权更迭,凡是经济要地更得聚精会神地看住。安徽、江苏之间反复调整,不只是“谁家管谁”那么简单,更多反映了当时对治水、交通和产业布局的追求。“物理位置在变,社会关系未变”,这种错位成了三省接壤地带常年存在的悖论。后来洪泽湖治理,安徽把盱眙、泗洪割给江苏,江苏则用萧县、砀山县抵偿。这不是你说一句来、我答一句还,更像一场没有剧本的博弈,每一次调整都要兼顾经济、地理和政令三根主线——村民的适应能力远超想象,但行政边界却无法成为你情我愿的“调味品”。
1950-55年反复调整,徐州都市圈雏形已现。萧县、砀山在经济、交通等诸多层面,早就成了徐州的“卫星”。安徽、江苏反复“让来让去”,可县城经济、人员流动并未因行政决定而断裂。砀山人跑去徐州做生意,萧县年轻人考学择业看重徐州,这些潜规矩让行政划分蒙上一层模糊色彩。政府层面的归属,不代表社会和文化的归属。官方规划强调一体化,群众选择实际便利——前者要数据,后者要生存。
此处隐约可见的人、地、政的三重错位。一个地方的区划归属更替,乡镇名字不会消失,但集体认同感,却一直在时间里“打补丁”。有专家分析,这片区域虽在政府文件上经历多次转手,地方性群体在生活习惯、亲属流动、产业联系上域外取向明显,这种拉锯会持续很久。你说它是安徽?对,在行政地图上是的。你说它是江苏?对于赶集、打工、上学的人来也是。到了今天,砀山县萧县融入徐州都市圈,现实需求终究胜过规章制度,有些人根本不在乎那条虚线怎么变。
大规模区划调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层出不穷。临时性的“行署区”只是过渡性安排。许多老百姓只记得,某年春天自家的口粮卡突然换了地方章。每次调整背后,跟着的都是国家级项目——洪泽湖治理、铁路修建、经济带协同,行政意志遮盖地方小情绪。在纸上谈兵者眼里,村名数字与归属标签比个体意愿更为重要。
这些变化并未带来永久的宁静。历史经验接二连三地说明区划与经济发展并非简单对应。萧县砀山后来融入安徽,但和徐州的经济与人口纽带,却比和宿州、合肥更深。一旦交通、教育、医疗等工程形成流通网络,昔日的行政归属感便成了模糊地带,人们只认现实利益——你给他方便,他才算你的。就连地方政府也默契承认,“跨区合作”才是出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中国人骨子里,本就不是生硬的“方框切割”。
归根结底,像安徽与山东这样的区划变迁,属于时代烙印下的惯常结果。表面“定鼎一案”。实际呢?归属感是流动的,情感和经济联系才是坚实的土壤。地图上的省界线,只是橡皮擦下的一条痕迹。若问砀山、萧县的村民,“你到底是哪省的人?”答案或许是“都无所谓,关键咱家今年苹果收成咋样,孩子在哪儿上学。”政策可以推演,世道人心,却自有它倔强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