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生活的代价》作者:德博拉·利维
母亲教会我游泳,教会我划船。她生于南非,在“风城”伊丽莎白港长大,在北伦敦生活了四十年,每天都渴望回到大海去。她总说,多丽丝·莱辛的第二部小说《玛莎·奎斯特》精准描述了她自己在贫瘠又愚昧的南非白人殖民文化中成长的经历。母亲在晚年摸索出一种游泳技巧,“把自己全交给水”。她仰面浮在水上,“清空思想,臣服于水流”。在汉普斯特德希思公园可以游泳的阴暗池塘里,她给我展示了她的技巧,与鸭子、野草和落叶一同漂在水面,姿势如奥菲利亚。
如今,我偶尔还会尝试用她的技巧,但漂不过十秒就开始下沉。同样,每每想到母亲的离世,想不过十秒,我的心就开始沉落。
我存着一张母亲二十多岁时的照片。照片里的她坐在一块石头上,正和朋友们野餐。刚游过泳,她头发湿漉漉的。她的表情中有一种内向的自省,如今我觉得这正是她最大的优点。我能看到,在这偶然的一瞬,她如此接近真实的自我。回想童年和少年,那时我大概不曾认为内省是她最大的优点。我们怎么会需要一个爱做梦的母亲呢?我们并不希望母亲把目光投向我们之外的地方,不希望她有去别处的渴望。我们需要她待在这个世界,活跃、能干,有求必应。
我是否曾嘲笑我母亲内心的梦想家,然后又为她没有梦想而羞辱她?
照传统故事的讲法,父亲才是英雄和梦想家。他从妻子和孩子可怜的索求中自我解绑,大步走向世界,做他自己的事。他合该做他自己。当他回到母亲为我们建立的家时,他要么受到热烈欢迎,加入我们,要么成为一个陌生人,对我们的索求最终会超过我们对他的。他向我们诉说他在他的世界的所见所闻,反过来,我们则对他添油加醋地讲述我们日常所过的生活。
母亲跟我们共同度过这段生活,我们凡遇不顺便归咎于她,因为在身边的是她。与此同时,我们会刻意回避有关她自己的性格和人生目标的叙事。然而,我们又需要她能体会到我们的焦虑——毕竟日常生活充满了焦虑。我们时常对她隐藏自己的感受,却又神秘地期望她理解一切。如果她越过我们,试图接近自我,而不再随时为我们效劳,她便僭越了神话所规定的基本任务——她本应是我们的保护者和养育者。但是,如果她太靠近我们,那种具有传染性的焦虑则会侵蚀我们脆弱的勇气,令我们窒息。
父亲在这个世界上做他需要做的事情,我们都理解那是他的使命。但如果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做她需要做的事情,我们却会觉得她抛弃了我们。这种种混杂矛盾的信息,用社会中最致命的毒墨水写成,她能从中幸存已是奇迹。这一切足可令她疯癫。
青春期的我跟母亲起冲突,大多是因为穿衣着装。她不明白我在外在表达之下,内心究竟是怎样的想法。她感受不到也认不出我了。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我正在塑造一个比自我更勇敢的人格。我宁愿在公共汽车上、在我居住的郊区街道上被人嘲笑。我厚底靴的银色拉链暗藏一个秘密信息,那就是我不愿和那些嘲笑我的人一样。有时,脱离归属的愿望和渴望归属的感觉同样强烈。冲突激烈时,我母亲会问我:“你以为你是谁?”十五岁的我答不上这个问题,但我在努力企及一种自由,一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年轻女性在社会上并未拥有的自由。还能做什么呢?做一个迎合别人设想的人可不是自由——那意味着不过为了平息他人的恐惧,就把我们的人生抵押出去。
如果连自身的自由都无法想象,那我们过着的便是一种错误的生活。
母亲在她的人生中远比我更勇敢。她逃离了她所爱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上层家庭,嫁给了一个一文不名的犹太历史学家。她与他一起参与了他们那代人在南非的人权斗争。她聪明伶俐、魅力四射,又幽默机智,但二十岁出头时却和大学无缘。没人认为非要告诉她,她其实才华横溢。她所在阶层的女性,通常应该在离开家后或在找到第一份工作后便立即结婚。那份工作该是名义上的工作,而不是严肃的事业。我母亲学打字,学速记,着装只为让男老板们满意。她倒希望自己的秘书技艺别那么纯熟,但父亲成为政治犯后,正是她靠着一手打字速度确保我们能吃饱穿暖。她那时总为难我,已不止于要求我做一个孝顺女儿,但现在我明白了:好坏不论,那时是我不想让她做她自己。
和女儿们搬到山上公寓过后一年,母亲患了绝症。我彻夜不眠,等医院的电话,每一个清醒的小时都由鸟鸣钟的不同叫声见证。夜莺在午夜前歌唱,仿佛栖息在停车场那棵树的枝丫上。她以前总说,死后她希望自己的遗体被运到山顶,给鸟儿们吃。
去世前的最后几周,她已无法进食或喝水。但我发现她还能舔食和吞咽一个牌子的冰棍。它有三种口味——她的最爱是青柠味,然后是草莓味,最后是可怕的橘子味。冬天的商店可不怎么会储备这种冰棍,但我发现本地报刊经销商的冰柜里有存货,报刊店的老板是三个土耳其兄弟。那冰柜长而矮,放在店中央,上盖上放着几只盒子,装着他们卖的蘑菇。冰柜盖上还放着彩票、降价销售的清洁用品、罐装汽水、鞋油、电池和点心。冰柜中放有冰棍,我母亲临终唯一的安慰。
那时前后不过一年,自己婚姻破裂,母亲确诊癌症,为此心神交瘁的我,无力向土耳其兄弟解释为什么二月份我却每天来买冰棍。我每次来总是面色阴沉,泪湿双眼,自行车停在外面。我一句话不说,开始把蘑菇、彩票、降价清洁用品、罐装汽水、鞋油、电池和点心挪到冰柜盖的另一侧。然后我推开滑门,寻找冰棍——找到青柠味是大获全胜,找到草莓味也不错,找到橘子味勉强可接受。我总是买两根,然后骑车去山下的医院,那里住着我正走向死亡的母亲。
我坐在她床畔,把冰棍放在她嘴边,听到她满足地低吟,觉得很欣慰。她的口渴总是难以缓解。她房间里有一台冷藏冰箱,但没有冷冻柜,所以第二根冰棍会融化,但我总照例买两根。现在回想,不知为什么我没把报刊店的所有冰棍都买下来,放在我家冰箱里,不知为什么,这段困难的日子里我从没想过该这么做。之后有一天,我的冰棍计划遇上了重大变故。像往常一样,我骑车去报刊店,把冰柜盖子上的所有东西飞快地推到一边,在土耳其兄弟疑惑的目光中,滑开冰柜门,结果发现,竟然有第四种口味。他们的青柠、草莓甚至可怕的橘子口味都卖完了。我从冰柜里抬起头,直直盯着三兄弟中的小弟那双亲切的棕色眼睛。
“为什么你们只有泡泡糖味的了?”我喊了出来——竟然有人做泡泡糖味的冰棍,甚至还想把它卖出去?做这种口味有什么必要?他们能不能尽快进购其他口味的冰棍,特别是青柠味?
他没有冲我喊回来,只是困惑而沉默地站着,任我怒气冲冲地买了两根泡泡糖味的冰棍。骑车去医院的路上,我只觉大难临头。大难也真的是临头了,因为几乎只有冰棍能让她再多撑一天。
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又去了另外几家店,但没有一家卖那个容易吞咽的牌子。晚些时候,我坐在骨瘦如柴的母亲床边,撕开泡泡糖味冰棍的包装,递到她嘴边。她舔了一下,脸微微皱起,又试了一下,摇了摇头。我跟她说,我在店里像个疯子一样狂呼乱叫,她听了嘴里发出细小的声音,胸脯上下起伏。我知道她在笑,在最后这段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里,这是我最喜欢的回忆之一。那天晚上,我在她床边看书,懊悔地瞥见盆里的泡泡糖冰棍已融化成一摊粉色液体。书我没怎么读进去,只粗粗扫过,但待在她身边我就安心。医生来做最后一次查房时,母亲举起她瘦弱的手,不知怎么,细若游丝的声音竟透出一种威严。她命令道:“这里要开点儿灯,我女儿在一团暗中看书呢。”
她的葬礼在三月举行,葬礼之后,我想我应该再去一趟报刊店,向土耳其兄弟解释一下我的异常行为。我向他们讲述了我母亲生命最后几周的状况,他们非常难过,这下轮到他们语塞了。他们又是摇头,又是叹息。过了一会儿,三兄弟中的大哥说:“如果你早些告诉我们就好了。”总穿一件时尚夹克的那位接过话头:“如果你当时开口,我们一定现款订购,帮你买一吨来。”而三弟的声调比两个哥哥都高,他手捶额头,说:“我就知道是这样的……我不是说了她肯定是给病人买的吗?”他们都愤怒地看着冰柜,仿佛冰柜该为我母亲在生命最后的时光中还要糟心地遇上不合口味的泡泡糖味冰棍负责。这一回我笑了,也带得他们笑了起来。死亡是恐怖的,但也是荒谬的,认识到这一点,人就从恐怖中解脱了。我们脚下的地板上铺了一层压扁的纸板箱,防止顾客脚上的泥弄脏地毡。纸板箱潮湿又泥泞,我们笑的时候就在我们脚下打滑。跟土耳其兄弟解释过来龙去脉后,我感觉好多了。某种程度上,我真希望自己那时也曾这样跟孩子的父亲好好做过解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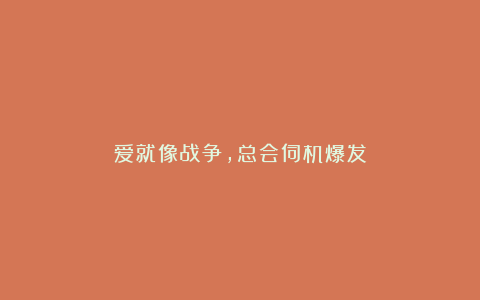
一个星期天,我又去报刊店买蘑菇,就是冰柜上的那些,前几个礼拜我每次去都怒气冲冲地把它们推到一边。三兄弟中的小弟刚从土耳其度假回来,他递给我一件用报纸包着的东西,说是给我的礼物。那是一只小小的白瓷杯,一个镂空雕刻的银制杯托套在杯子外,还附有一只配套的华丽银杯盖。他记得我在店里买过一包土耳其咖啡,当时我告诉他,我用玻璃杯喝咖啡。“但玻璃杯是喝茶才用的,”他说,“这才是用来喝土耳其咖啡的杯子。”
我明白,这是一份表达慰问的礼物。
时至今日,那只杯子依然是我母亲离世的标志。我还没告诉小弟,写稿时,我偶尔会用小铜壶煮土耳其咖啡,再倒在这只杯子里,盖上银盖。这成了我写作日常仪式的一部分。午夜过后,凌晨时分,小口饮用香味浓郁的咖啡,落笔时我总会写出一些有趣的东西。我已成为一个不需离开座位的夜游者。夜晚比白天柔软、安静、悲伤、平和,风轻叩窗户,管道嘶鸣,熵使得地板咯吱作响,幽灵般的夜间巴士来来去去——还有一种永存于城市中的悠远声音,似大海般,但那只是生活,更多的生活。我意识到这就是母亲去世后我想要的东西。更多的生活。
不知为何,我总觉得她既死且生。我感觉她就在那大海般的悠远声音中,那海就是她教我游泳的那片海,但她不在那儿。她已经走了,不见了,消失了。
她去世几个月后,我在柏林的一场文化节上朗读《我不想知道的事》。翻译坐在我身边,我们商量好,我用英语读三句,她就把这三句给听众翻译成德语。我开始读,读到的一段写到我七岁时躺在母亲怀里的情景。这段文字带给我的震撼,是我未曾料想到的,一次幽灵般的邂逅。
我们的头挨在一起,那时我虽然心里痛苦,但同时也感受到了爱。
我一时失声,读到一半就顿住了。照之前的约定,翻译在等我把三句话读完。她被困住了,一个断开的句子悬在我们之间。如果说语流是火车,那么这列火车此刻突然减速,停在了半道。沾满非洲往事尘埃的车最终还是驶入站台,翻译赶忙接上,语气急促,照直翻——这大概是好事。说不出话的焦急场景,让我即刻闪回到童年:曾有一年我一句话都不说。每次别人要求我开口说话、大点儿声,词语就会颤抖着,羞愧地逃走。
寻找语言的挣扎每每让我知道,语言是活的,必不可少,至关重要。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一种观点:能表达自己是一件好事。但是,抑止一句话和找到一句话要花费的力气同样多。真理并不总是餐桌上最有趣的客人,而且杜拉斯说了,对我们而言,自我往往比他人更不真实。
柏林的朗读会结束后,我和我的德国出版人坐在作家帐篷外。她问了我一个问题。
“在出声朗读的时候,你是一个演员吗?”
她是在疑惑我最后那几句表达得极为情绪化。我本可借机向她解释,我的母亲刚刚过世,在书中重新看到她,对我来说不啻一记重击。但我没说。我一语不发。土耳其兄弟们比我的出版人应对得更得体。
“你看起来很苍白。”她说。这句我也不知如何作答。
过了一会儿,我指着文化节广场上一个卖咖喱香肠的小贩,告诉她我想写一个人物,一个男性主角,在落雪的柏林,他站在卖咖喱香肠的小车旁,等待一个他曾背叛过的人。
“咖喱香肠可不是什么浪漫的食物。”她打断我。
“是的,”我答道,“但爱就像战争,总会伺机爆发。”
在我和母亲断断续续的战争中,爱的确瞅准了机会。诗人奥德雷·洛尔德讲得最好:“我是我母亲的秘密诗歌和隐藏怒火的倒影。”1992年,母亲从约翰内斯堡寄了一张明信片给我。她去那里看望一些朋友。在从种族隔离向民主过渡的政治动荡期,这些朋友曾对她和家里人施以援手。
去参加沃尔特·西苏鲁的庆生会,假期华丽开场。见到了像有一百年没见的人。坐在纳丁·戈迪默身旁。她娇小,瘦削,活泼,像只鸟儿。
母亲在明信片正面用圆珠笔画了一个X,并写道:我在X标记处。她所在的街区似乎在一座大立交桥外缘,靠近电话塔和摩天大楼。此刻,这个X深深触动了我——她手握圆珠笔,用力把X画在明信片上,标出她的位置,这样我就能找到她了。
商务合作请联系:阿树(zhidao8782)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