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岭南学报》第十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王锷老师授权发布!
本文转自“书目文献”公众号
《十三經注疏》包括《周易正義》(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周禮注疏》(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禮記正義》(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公羊傳解詁》(漢何休注,唐徐彥疏),《春秋穀梁傳注疏》(晉范甯注,唐楊士勛疏),《論語注疏解經》(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孝經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宋邢昺疏),《孟子注疏》(漢趙岐注,宋孫奭疏),是漢、魏、晉、唐、宋人注釋《十三經》的著作匯集,部分經書附有唐陸德明釋文。《十三經注疏》的經注和疏原本單獨流傳,衹有經注本、單疏本,那麼,《十三經》的經注與疏是什麼時間匯集在一起的?宋代以來,作爲叢書性質的《十三經注疏》是如何校刻的?校刻過多少次?每次校刻都做了什麼工作?隨著古籍整理事業的興盛,《十三經注疏》的整理情況如何?在學術閱讀和研究中,如何選擇《十三經注疏》的版本?等等,就以上問題,我們從宋代經書注疏的匯集、元明清《十三經注疏》的校刻、現代《十三經注疏》的整理等方面,爬梳討論,間陳管見。
《十三經》經注疏文的合刻時間,清代乾嘉學者惠棟、段玉裁、陳鱣、顧廣圻就有討論。惠棟《禮記正義跋》認爲注疏合刻始於北宋[1],段玉裁《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序》曰:
段玉裁認爲經注疏“北宋之際合之”。阮元、陳鱣認爲注疏合刻始於南北宋之間[3]。對段氏等人的觀點,當時學者錢大昕、顧廣圻均提出反對意見[4]。錢大昕《儀禮注單行本》曰:
又《正義刊本妄改》曰:
錢氏謂南宋初有“併經注正義合刻者”“又有合釋文與正義於經注之本”,明確提出注疏合刻始於南宋。
黃丕烈《百宋一廛賦注》曰:
居士前在阮中丞元《十三經》局立議,言北宋本必經注自經注,疏自疏,南宋初始有注疏,又其後始有附釋音注疏。晁公武、趙希弁、陳振孫、岳珂、王應麟、馬端臨諸君,以宋人言宋事,條理脈絡,粲然可尋。而日本山井鼎《左傳考文》所載紹興辛亥三山黃唐跋《禮記》語,尤爲確證,安得有北宋初刻《禮記注疏》及淳化刻《春秋左傳注疏》事乎?今此賦所云,即平昔議論也[7]。
顧廣圻明確提出“北宋本必經注自經注,疏自疏,南宋初始有注疏,又其後始有附釋音注疏”。又撰《陳仲魚孝廉索賦經函詩率成廿韻》曰:
顧氏賦詩,謂注疏合併始於南宋,越中刻本最早。對十行本系統諸版本之評價,高屋建瓴,堪稱《十三經注疏》版本史詩。
日本學者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徴引《禮記正義》黃唐跋文,對於清代乾嘉學者影響甚大,山井鼎將跋文“紹熙辛亥”誤寫爲“紹興辛亥”,誤導清人多年。《禮記正義》黃唐跋文(圖一)曰:
辛亥是南宋光宗紹熙二年(1191),壬子是南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黄唐所言“本司”,即兩浙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司,紹興年間設置,治所在越州(今浙江紹興),黃唐於紹熙辛亥(1191)十一月任“朝請郎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一職[10]。南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即《九經三傳沿革例》之“越中舊本注疏”,學界稱爲“越州本”“八行本”。
八行本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注疏合刻本,先後刊刻有《周易注疏》《尚書正義》《周禮疏》《毛詩正義》《禮記正義》《春秋左傳正義》《論語注疏解經》《孟子注疏解經》等八經,刊刻時間從南宋初至寧宗嘉泰、開禧年間(1201-1207)[11]。《周易注疏》十三卷,今存兩部,一藏日本足利學校,一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尚書正義》二十卷,今存兩部,一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一藏日本足利學校;《周禮疏》(實爲《周禮注疏》)五十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臺北故宮博物館各藏一部,皆有修補,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一部,殘存二十七卷;《禮記正義》七十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兩部,一部全,有惠棟跋,一部殘存二十八卷,日本足利學校藏本殘存六十二卷,另有散存零卷;《春秋左傳正義》三十六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一部;《論語注疏解經》二十卷,臺北故宮博物院、重慶市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均藏殘本;《孟子注疏解經》十四卷,臺北故宮博物館藏一部,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博物院各藏殘本。
八行本經注疏的體例,都是經文+注文+疏文的次序,即注文接經,疏文按注。惟有《周禮疏》的體例是經文+經文之疏+注文+注文之疏,這種體例,將疏文的解經之疏和解注之疏分隔開來,分别綴於經文、注文之下,聯繫書名叫“周禮疏”而非“周禮注疏”,乃沿襲單疏本,顯示出八行本早期合刻的特徵。
除越州所刊八行本之外,四川、福建等地也刊刻有注疏合刻本,經書注疏合刻的情況比較複雜。顧永新先生通過對清劉世珩影刻元元貞二年(1296)平陽府梁宅刻本即元貞本《論語注疏解經》十卷的研究,認爲“在北宋或南宋早期,最早出現了注疏合刻本《論語注疏解經》十卷,以經注附疏,故分卷仍單疏本之舊。這是後來八行本及十行本系統各本的祖本”[12]。就《論語》而言,八行本《論語注疏解經》二十卷,並非最早。
八行本之後,福建建陽地區出現一種新的注疏合刻本,即附陸德明釋文的附釋音注疏合刻本,半頁十行,故稱宋十行本,部分是建安劉叔剛刻本,故又稱劉叔剛本。今存者有《附釋音毛詩注疏》二十卷,日本足利學校藏一部;《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一部藏日本足利學校,另一部分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卷1-29)和臺北故宮博物院(卷30-60),書尾有“建安劉叔剛鋟梓”牌記;《監本附釋音春秋穀梁注疏》二十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一部。《附釋音禮記注疏》六十三卷已佚,清和珅有翻刻本,基本保存了劉叔剛本的面貌。重慶市圖書館藏元十行本《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中,配補七頁黑口版頁,可確認是宋十行本《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的零頁[13]。劉叔剛刻書大致在南宋光宗、寧宗時期(1190-1224)[14]。
《九經三傳沿革例》記載注疏本有“越中舊本注疏、建本有音釋注疏、蜀注疏”[15]三類。越中舊本注疏即八行本,建本有音釋注疏即宋十行本,蜀注疏流傳很少,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一部《論語注疏》十卷,與八行本、宋十行本不同,屬於另一注疏本系統。八行本不附釋文,宋十行本附釋文,體例是經文+注文+釋文+疏文,蜀注疏本《論語注疏》亦附釋文,附入形式與宋十行本略異,且於釋文前圓圈“釋”字提示,形式獨特。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南宋福建魏縣尉宅本《附釋文尚書注疏》二十卷,後四卷配元刻明修十行本,卷一末有“魏縣尉宅校正無誤大字善本”,半頁九行,體例接近元十行本《附釋音尚書注疏》,說明建陽地區的注疏合刻本不止一種[16]。
宋代經書注疏合刻始於南宋初期,就注疏本流傳和今存者看,八行本、宋十行本是有計劃的匯集刊刻,對元代以來經書注疏的校刻,影響巨大。至於蜀注疏和魏縣尉宅究竟刊刻了多少種經書,有待於新資料的發現。
宋周密《癸辛雜識》曰:“廖群玉諸書,《九經》本最佳。又有《三禮節》,其後又欲開手節《十三經注疏》,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17]廖瑩中字群玉,號藥洲,賈似道門客,家有世彩堂,喜藏書刻書,欲“手節《十三經注疏》”,未果。《九經三傳沿革例》有“汴本《十三經》”之稱,然宋代是否刊刻《十三經注疏》,證據不足。
宋十行本《周禮注疏》四十二卷,《禮記注疏》六十三卷,較之八行本《周禮疏》五十卷、《禮記正義》七十卷,照顧經書內容,盡可能將某篇分在一卷或數卷之中,且附有釋文,方便閱讀,備受讀者青睞[18]。所以,自元代以來,元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武英殿本、《四庫》本和阮刻本《十三經注疏》,皆仿效宋十行本的體例,校勘刊刻。
元代泰定(1324-1328)前後,翻刻宋十行注疏本,即元十行本。元十行本與宋十行本,在內容體例、板式行款、字體特徵等方面,非常相似,但也有明顯的區别。張麗娟説:“宋刻十行本區别於元刻十行本最明顯的特徵是:書口爲細黑口而非白口;版心下不刻刻工姓名;版心上不刻大小字數,疏文出文與疏文正文之間無小圓圈標識;多用簡體字等。”[19]經過比較《附釋音毛詩注疏》等,“可以得出如下兩點認識:一、宋刻十行本與元刻十行本之間有直接的繼承關係,後者是根據前者翻刻的。二、宋刻十行本與元刻十行本確爲兩個不同時期的刻本,兩者不可混爲一談。”[20]
元十行本有元刻十行本和元刻明修十行本之别。元刻十行本今存六種: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周易兼義》九卷《音義》一卷《略例》一卷,原劉承幹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附釋音尚書注疏》二十卷,原李盛鐸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鐵琴銅劍樓舊藏;中國臺北“國家圖書館”藏一部殘本,殘存二十八卷。重慶圖書館藏《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一部,其中有八頁宋十行本零頁;南京圖書館藏《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殘存十卷);中國臺北“國家圖書館”藏一部,有抄配。南京圖書館藏《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二十卷(殘存卷十七、十八),日本京都大學藏有一部[21];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孝經注疏》九卷,乃元泰定三年(1326)刻本[22]。另外,上海圖書館藏有《附釋音禮記注疏》元刻十行本卷二十五殘葉十頁[23]。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一部《爾雅注疏》十一卷(殘,半葉九行),“乃元時初印本,絶無補刊之葉”[24]。張麗娟謂“頗疑此本為元刻單行本,而非泰定、致和間所刻諸經注疏之一。”[25]
元刻十行本書板傳至明代正德、嘉靖年間,遞經修補,補版版心刻正德六年刊、正德十二年刊、嘉靖三年刊等文字,與原版有明顯區别,後人稱之爲“十行本”“正德本”,甚者長期被誤認爲宋刻本,我們稱之爲“元刻明修十行本”,包括《周易兼義》九卷《音義》一卷《略例》一卷、《附釋音尚書注疏》二十卷、《附釋音毛詩注疏》二十卷、《附釋音周禮注疏》四十二卷、《儀禮》十七卷《儀禮圖》十七卷《旁通圖》一卷、《附釋音禮記注疏》六十三卷、《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二十卷、《孝經注疏》九卷、《論語注疏解經》二十卷、《孟子注疏解經》十四卷、《爾雅注疏》十一卷,名爲“十三經注疏”,其實缺《儀禮注疏》,用《儀禮》十七卷《儀禮圖》十七卷《旁通圖》一卷替代[26]。元刻明修十行本《十三經注疏》完整保存於今者有四部,北京市文物局、國家博物館、軍事科學院和日本靜嘉堂文庫各藏一部,北京市文物局藏本《中華再造善本》影印,靜嘉堂本是阮刻本之底本。國內外圖書館收藏一些元刻明修十行本之零種,如江西省樂平市圖書館藏《附釋音禮記注疏》殘本一部,殘存卷七至卷九、卷十七至六十三,缺十三卷[27]。
元刻明修十行本較之宋十行本,匯集經書注疏多至十二部經書,雖不完備,然已初具規模,成爲明清翻刻《十三經注疏》的祖本。
從《中華再造善本》影印的元刻明修十行本《十三經注疏》來看,存在板片修補、缺頁、倒裝、墨釘和文字錯誤諸多缺陷。就缺頁而言,分沒有此頁、因版頁重複而缺頁、有版頁無文字、因誤裝而缺頁等情況。如《附釋音禮記注疏》卷三十第六頁和第九頁內容一致,區别是第六頁是明正德六年(1511)補版,第九頁是元代原版,左上角有書耳,內刻“玉藻”二字,導致原本第九頁內容遺失,以阮刻本計算,缺經注疏文和釋文七百八十一字。(圖二、圖三)。第七頁沒有文字,惟見版心刻“記疏三十卷”“七”,當是正德補版,未見文字,日本靜嘉堂藏本此頁是抄配(圖四、圖五)。
墨釘是古籍版頁中方形或長方形的黑塊,表示缺文。元刻明修十行本《十三經注疏》多墨釘,《附釋音禮記注疏》尤爲突出,如卷五十一第二十七頁二十行,有墨釘者占十五行(圖六)[28]。
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除《爾雅注疏》外,其餘十二種是同一時段、同一地域刊刻,各經元板頁刻工基本相同,雕刻完畢,書板收藏於福州路府學經史庫中,府學在城南興賢坊內,遞經修補,多數修補刻工是福建人,也參與了閩本《十三經注疏》的刊刻[29]。明初以來,版片仍存原地,先後經明前期、正德六年、正德十二年、正德十六年、嘉靖三年、嘉靖前期等多次修版,屢經刷印[30],廣爲流傳,影響很大,閩本、監本、毛本、武英殿本、阮刻本《十三經注疏》的校刻,均源自於元十行本。對於翻刻者而言,主要任務就是補足缺文,校正訛謬。
明嘉靖十五至十七年間(1536-1538),李元陽以御史巡按福建,與同年福建提學僉事江以達以元十行本爲底本,重刻《十三經注疏》,簡稱“閩本”“嘉靖本”“李元陽本”。閩本與元刻明修十行本相比,有三個特點:一是用《儀禮注疏》十七卷替換原《儀禮》十七卷《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這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部《十三經注疏》;二是閩本改板式半頁十行爲九行,注文中字,單行居中,初刻本每卷首頁皆有“明御史李元陽、提學僉事江以達校刊”等十五字;三是在沿襲元十行本訛脫衍倒缺外,間有訂補,如《禮記注疏》卷十四頁十五B面第九行“又云地數三十,所以三十者,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故三十也”,“所以三十”四字,元十行本、阮刻本脫,閩本補(圖七)。
圖七:元十行本《禮記注疏》卷十四頁十二A面
和閩本《禮記注疏》卷十四頁十五B面
明萬曆十四年(1586),北京國子監依據閩本奉敕校刻《十三經注疏》,萬曆二十一年竣工,簡稱“監本”“北監本”“萬曆本”(圖八)。監本與閩本差異有三:第一,監本是第一部由國家倡導、奉敕校刻的《十三經注疏》;第二,改注文爲小字單行,空左偏右,與閩本居中者小異,版心單魚尾,上刻“萬曆十六年刊”等文字;三是國子監組織學人校勘,對閩本多有訂補。如《禮記注疏》卷六頁七B面第七行疏文“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后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杖期”,毛本同,元十行本作“■杖”,閩本、阮刻本作“期杖”,非。服喪時使用喪杖稱杖期,不使用喪杖稱不杖期,元十行本有脱文,閩本校補,文字互倒,監本校正。監本於崇禎五年(1632)、康熙二十五年(1686)兩次修版,康熙重修本於每卷改刻官銜,加入重校修者官名,版心改刻爲“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圖九:監本《禮記注疏》卷二三頁二九A面
和毛本《禮記注疏》卷二三頁二九A面
崇禎元年(1628),毛晉依據監本校刻《十三經注疏》,完成於十三年除夕,簡稱“毛本”“崇禎本”“汲古閣本”。毛本與監本的區别有三:第一,這是明代第一部私人校刻的《十三經注疏》;第二,改變板式,注文中字,單行居中,白口,版心由上至下鐫有禮記疏、卷之幾、頁數、汲古閣等,匾方字體,橫細豎粗;第三,校補訛缺,毛本沿襲元十行本、閩本、監本之訛誤不少,亦有訂正者,如《禮記注疏》卷二三頁二九A面第七至八行注文“謂以少小下素爲貴也若順也”十二字,閩本、監本皆缺(圖九)。《爾雅注疏序》頁一B面第二行“豹鼠既辯”,監本及之前的單疏本、元本、閩本、監本“辯”皆作“辨”,阮《校》云“毛本作’辯’,蓋依唐石經《爾雅序》所改”,是(圖十);《爾雅注疏》卷八頁十三A面第一行“植而日灌”,單疏本作“人且日貫”,元本作“人且曰貫”,閩本剜改作“灌且日貫”,監本承之,阮校云毛本是也(圖十一)[31]。毛本《十三經注疏》書板後歸常熟小東門外東倉街席氏,清初以來,或有翻刻,校對不精,錯誤不少[32]。
圖十:監本《爾雅注疏序》頁一B面和毛本《爾雅注疏序》頁一B面
圖十一:監本《爾雅注疏》卷八頁十三A面和毛本《爾雅注疏》卷八頁十三A面
清初以來,學術界對於閩本、監本和毛本《十三經注疏》的評價不佳,顧炎武謂“《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33]。張爾岐曰:“《十三經》監本,讀書者所考據。當時校勘非一手,疏密各殊,至《儀禮》一經,脱誤特甚,豈以罕習,故忽不加意耶!”[34]盧文弨《周易注疏輯正題辭》云:“余有志欲校經書之誤,蓋三十年於兹矣。毛氏汲古閣所梓,大抵多善本,而《周易》一書,獨於《正義》破碎割裂條繫於有注之下,至有大謬戾者。”[35]惠棟曰:“《附釋音禮記注疏》,編爲六十三卷,監板及毛氏所刻,皆是本也,歲久脱爛,悉仍其缺。”[36]張敦仁(顧廣圻代撰)《撫本禮記鄭注考異》云:“李元陽本、萬曆監本、毛晉本,則以十行爲之祖,而又轉轉相承,今於此三者不更區别,謂之俗注疏而已。”[37]“亡於監刻”“脫誤特甚”“有大謬戾者”,監本、毛本“歲久脱爛,悉仍其缺”,“俗注疏而已”等等,對於閩、監、毛本這樣的評價,給人的感覺,幾乎是一無是處。其實,顧炎武所言監本《儀禮注疏》十七卷五處四十六字脫文,閩本以及陳鳳梧刻《儀禮注疏》均脫[38],並非始於監本。正因爲學術界有這樣的認識,乾隆登基不久,便順應學術界需求,下令武英殿校刻《十三經注疏》。
清乾隆三年(1738),因太學庋藏監本板面模糊,無法刷印,國子監請求重新校刻《十三經注疏》,乾隆乃下令設經史館,任命方苞爲總裁,主持《十三經注疏》的校刻,此即武英殿本,簡稱“殿本”。與監本比較,殿本有五點創新:一是給經注疏釋文全部施加句讀;二是每經由專人校勘,撰寫“考證”,如《附釋音禮記注疏》考證近七百條;三是於《孝經》《論語》補入釋文,《爾雅》改換爲陸氏釋文,《孟子》補入宋孫奭音義,成爲第一部經、注、疏、釋文俱全的由政府校刻的《十三經注疏》;四是更改板式,半頁十行,行大字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同,注文中字居中,白口,版心上端刻“乾隆四年校刊”六字,上單魚尾,下刻“禮記注疏卷幾”等文字,下小字刻篇名、頁數;五是改變元十行本以來閩本、監本等疏文的編聯方式,刪除疏文中經文、注文起訖語,將每節經文之疏編排在前,注文之疏連排在後,這樣的變更,解釋經文之疏和注文之疏分開,明白清晰,但當經文或注文較長時,沒有起訖語,不便尋找,且有漏刪、誤排疏文之現象(圖十二)[39]。
清代編纂《四庫全書》時,依據殿本收入《十三經注疏》,散入經部各類。四庫館所校抄《四庫》本《十三經注疏》,有《四庫全書薈要》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等七閣兩大系統,《四庫全書薈要》和《四庫全書》是抄本,在編修時,於《十三經注疏》各經的校勘,皆有專門的辦理人員,吸收校勘成果,整理出優於殿本的《四庫》本,校勘成果反映在《四庫全書薈要》校語與《四庫全書考證》中。以《禮記注疏·曾子問》爲例,殿本自卷十九第二十五頁A面第九行經文“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之疏文“所用土周而”以下,第二十五頁B面、第二十六頁A面,至第二十六頁B面前兩行皆爲空行,第二十六頁B面第三行起續以下經文“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齊召南《考證》曰:“’自史佚始也’注疏’所謂土周而’,下缺。此下疏文全缺,舊本後空二十三行,今仍之。”[40](圖十三、圖十四)然此段疏文不獨殿本空,元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亦缺,《四庫》本則補全缺文(圖十五)。可見,四庫館臣於《禮記注疏》的校勘傳承是有貢獻的[41]。
《十三經注疏》從閩本到《四庫》本,每次整理,都進行了校勘,彌補缺文,校正訛誤,較之前本,均有改進,尤其是閩本替換《儀禮圖》爲《儀禮注疏》,殿本句讀經注疏文,補入《孝經》《論語》等經釋文,確實是創新。但是,因祖本元刻明修十行本經多次修版,缺文、墨釘、錯訛,在在皆有,故閩本、監本、毛本在清康乾時期,備受非議,顧廣圻稱之爲“俗注疏本”。作爲四庫館副總裁的彭元瑞,閱讀的書也是北監本,其《自校禮記注疏跋》曰:
乾隆丙午是五十一年(1786),彭元瑞用金曰追《禮記正譌》校北監本《禮記注疏》,歷時一月零二日,發現北監本“尚未譌者計不下千條,猶是善本”。其《自校儀禮注疏跋》曰:
彭元瑞校完《禮記注疏》,又校《儀禮注疏》,歷時二十七日,苦《儀禮》難讀!可見,監本《十三經注疏》,是學者常讀之書。
惠棟、盧文弨、浦鏜、顧廣圻和日本人山井鼎、物觀利用傳存宋板,校勘閩本、監本、毛本,著有《十三經注疏正字》《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撫本禮記鄭注考異》等校勘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清代校勘學的發展,尤其顯著者,顧廣圻提出“不校校之”的校勘學理論,並付諸實踐,協助張敦仁、阮元、黃丕烈、汪士鐘等人校勘經學文獻,成就“校勘學第一人”之美譽。惠棟、盧文弨、浦鏜和顧廣圻等人的校勘經學文獻的學術活動,直接影響了阮元,阮元開始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
阮元謂閩、監、毛諸本“輾轉翻刻,訛謬百出。毛本漫漶,不可識讀,近人修補,更多訛謬”[44],然於殿本、《四庫》本不敢置喙。嘉慶二十年(1815),阮元在盧宣旬等人襄助下,依據元刻明修十行本,校刻《十三經注疏》四百十六卷,即“阮刻本”,這是清代考據學興盛的代表作。與閩本、監本、毛本和武英殿本相比,阮刻本有六大優點:一是制定凡例,阮刻本於書前有“重刻宋本注疏總目錄”,述刻書緣起,每部經書前有“引據各本目錄”,説明校刻體例;二是選擇版本,自元至清嘉慶初年,成套的《十三經注疏》有元刻明修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殿本和《四庫》本,阮元將元刻明修十行本誤認爲是“宋本”,以“宋本”爲底本校刻,故曰“重刻宋本”;三是彙校眾本,阮元以“宋本”爲底本,對校閩本、監本、毛本,吸收他本和前賢校勘成果;四是撰寫校記,校勘版本,撰寫校勘記,呈現諸本異同,故《書目答問》曰:“阮本最於學者有益,凡有關校勘處旁有一圈,依圈檢之,精妙全在於此”[45];五是更換底本,阮元因閩本《儀禮注疏》十七卷“訛脫尤甚”,乃以宋嚴州本《儀禮注》和單疏本爲據,成《儀禮注疏》五十卷[46],《爾雅注疏》十卷亦是重新匯編者;六是校補正訛,阮刻本底本元刻明修十行本脫漏錯訛極夥,如《禮記注疏》等,墨釘無處不有,阮元參校他本,補足缺文,校正訛謬,去底本之非,集眾本之善,甫一刊刻,廣爲流傳,至今不衰。(圖十六)
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始於嘉慶五年(1800),嘉慶十一年(1806)刊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一十七卷,嘉慶二十一年(1816)於南昌府學刻成《十三經注疏》四百一十六卷。阮刻本彙校眾本,吸收他校,撰寫校記,記錄異同,按斷是非,成爲名副其實的集大成式之《十三經注疏》本。
清阮元《重刻宋板注疏總目録》説:“竊謂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當從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讀注疏不終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潛心研索,終身不知有聖賢諸儒經傳之學矣。至於注疏諸義,亦有是非。我朝經學最盛,諸儒論之甚詳,是又在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尋覽之也。”[47]張之洞《書目答問·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之“經學家”前曰:“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後總結説:“右漢學專門經學家。諸家皆篤守漢人家法,實事求是,義據通深者。”《書目答問》“經濟家”曰:“經濟之道,不必盡由學問,然士人致力,舍書無由,此舉其博通確實者。士人博極群書,而無用於世,讀書何爲?故以此一家終焉。” [48]“經濟家”所列者有黃宗羲、顧炎武、顧祖禹、秦蕙田、方苞、魏源等人,皆經世致用者。阮元、張之洞之言,說明經學是一切學問的根基。《十三經注疏》是經學核心文獻,宋元明清,代有校刻,時至今日,也是讀書人案頭必備之書。
由於時代的變遷,學術風氣的轉變,阮刻本及其以前的《十三經注疏》,今日之大多數讀書人難以卒讀,亟待重新整理,以適應學術發展的要求。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李學勤先生主編的《十三經注疏》標點本,此後又出版“繁體豎排”本。李學勤先生《序》説:“這裡提供給讀者的《十三經注疏》整理本,仍以阮本爲基礎,而在注記中博採眾説,擇善而從,在校勘上突過前人。同時施加現代標點,改用橫排,這樣做雖有若干障礙困難,卻使這部十分重要的典籍更易爲各方面讀者接受。”該書《整理説明》曰:“全面吸收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和孫詒讓《十三經注疏校記》的校勘成果,對阮元《校勘記》中已有明確是非判斷者,據之對底本進行改正;對其無明確是非判斷者,出校記兩存。”[49]這套書最大的優點是施加標點,簡體橫排,方便閱讀,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經學研究。缺陷是校勘有限,對阮元《校勘記》多有刪改,日本學者野間文史、呂友仁先生曾撰文批評該書的缺陷[50]。
二〇〇一年六月,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本,總計二十册,這套書依據南昌府學刊阮刻本整理,分段標點,未加校勘,完整保留阮刻本內容。
一九九二年,西北大學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於共同發起成立了“新版《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編纂委員會”,整理《十三經注疏》,主編是張豈之、周天游二位先生,其《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序》説:“各經均追本溯源,詳加考校,或采用宋八行本爲底本,或以宋早期單注、單疏本重新拼接,或取晚出佳本爲底本,在盡量恢復宋本原貌的基礎上,整理出一套新的整理本,來彌補阮刻本的不足,以期對經學研究、對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能起到推動作用,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51]已出版《尚書正義》《毛詩注疏》《周禮注疏》《儀禮注疏》《禮記正義》《春秋公羊傳注疏》《孝經注疏》《爾雅注疏》等,質量參差不齊。其中呂友仁先生整理的《禮記注疏》在標點、校勘等方面,均優於前者[52],然於八行本疏文無起訖語[53]者,自擬補入,實不可取;將八行本和潘宗周影刻本等同爲一,屬於失察。呂友仁先生整理的北大《儒藏》本《禮記正義》[54]以八行本爲底本,用足利本、阮刻本和撫州本、余仁仲本通校,改正上古本失誤,不附錄釋文,實爲八行本最佳之整理本。其他各經注疏,問題不一,學界多有討論,不再贅述。
北大《儒藏》和浙大《中華禮藏》整理出版了部分經書注疏合刻本[55],不是成套的《十三經注疏》。
近日,中華書局推出了南京師範大學方向東教授點校的《十三經注疏》一套,精裝二十五冊(下簡稱“方校本”)[56]。此書以道光六年(1826)朱華臨重校本爲底本,用阮元校刻南昌府本、江西書局本、脈望仙館本、點石齋本、錦章書局本、世界書局本對勘,參校武英殿本及各經傳世經注本、單疏本,《禮記注》《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參校撫州本、余仁仲本,《尚書正義》《周禮疏》《禮記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參校八行本,《毛詩注疏》參校日本藏宋十行本,《儀禮注疏》《論語注疏解經》《孝經注疏》依據通志堂本《經典釋文》,補入釋文,人名、地名、國名和朝代名加專名線,施加新式標點,全書簡體橫排,極便閱讀。方校本有如下優點:
一是底本優良。阮刻本《十三經注疏》自清嘉慶年間刊刻以來,多次翻刻,有道光本、江西書局本、脈望仙館本、點石齋本、錦章書局本、世界書局本等。方教授曾經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華書局影印阮刻本《十三經注疏》彙校勘正”,通過彙校,釐清了阮刻本系統諸版本之關係,南昌府本經過重校重修,其中道光重修本保存原版,修改錯訛,質量較好,故選道光本爲底本整理,保證了文本品質。
二是整理規範。阮刻本附有經盧宣旬等人摘錄的校勘記,校勘記與經注疏文,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此次整理,制定凡例,保留阮校,且將校勘記移至每段之下,别以“【阮校】”,較之原附於卷尾者,方便閱讀。又,各書參校宋元以來八行本、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殿本以及余仁仲本等經注本,校改底本錯誤,凡有改正,新出校記於本頁下端,約近萬條,校勘有據,魯魚亥豕,多已修正,形成一部阮刻本《十三經注疏》的升級版。
三是標點準確。已出版的《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對於經注疏文和釋文的處理,各有不同,由此而導致對於經注疏文和釋文的標點斷句,有前後失照者。方校本在斷句標點時,立足經文,會通注疏,前後照應,點校句讀。所以,該書既是一部普及傳統文化的優良讀本,也是匯聚諸家之長和眾本之善的注疏本,是文史哲研究者案頭必備的經典文獻。
方教授長期從事經學文獻的整理校勘,成就斐然!阮刻本《十三經注疏》是集大成式的古籍善本,他歷時十多年,焚膏繼晷,孜孜矻矻,完成“爲往聖繼絕學”之重任,值得肯定,令人敬佩!
由於整理《十三經注疏》工程浩大,頭緒繁多,方校本仍然存在一些破句、失校、漏標專名線和誤排等問題。此舉一例,《禮記注疏》卷十四:“《律曆志》又云’地數三十’者,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故三十也。”[57]“者”上脫“所以三十”,元十行本同,閩本補,八行本有“所以三十”四字可證[58],方校本漏校。
自南宋以來,經書注疏開始合刻,此後匯集爲一套經學文獻專科叢書《十三經注疏》,有元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殿本、《四庫》本和阮刻本,當今出版的《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大多立足於阮刻本進行點校,說明阮刻本至今無法替代。
如果要整理出超越阮刻本的《十三經注疏》,必須做好以下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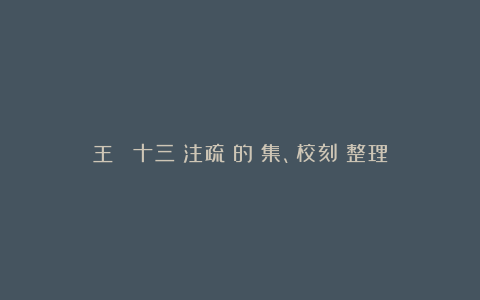
第一,彙校諸經版本,梳理版本源流。經書版本主要有白文本、經注本、單疏本和注疏本,各經應該立足某本,彙校眾本,在彙校的基礎上,梳理版本源流,然後選擇底本,確定對校本和參校本,吸收前人校勘成果,方可整理出一部超越阮刻本的《十三經注疏》新版本。山東大學杜澤遜教授的“《十三經注疏》彙校”、北京大學顧永新教授“《周易》彙校”、南京師範大學楊新勛教授“《論語注疏》彙校”、陝西師範大學瞿林江副教授“《爾雅注疏》彙校”皆可模仿。
第二,撰寫整理凡例,規範校勘記撰寫。閩本至阮刻本《十三經注疏》,尤其是殿本、阮刻本,在經書文獻整理方面,積累了很多成功的經驗,諸如句讀全書、撰寫考證或校勘記,如何對校,如何參校,如何吸收前賢校勘成果,校勘記寫成簡明的“定本式”還是繁雜豐富的“彙校式”,等等,前人校刻《十三經注疏》的經驗,多可借鑒參考,只有搞清前人做了什麼,成績和缺陷何在,方能推陳出新,超越前賢。
第三,明確經注疏和釋文的關係,在遵守底本的同時,照顧閱讀的便利。經書注疏本是經文、注文和疏文的彙編,自宋代以來,或以經注本爲主,將疏文插入相應的經注之下;或以疏文爲主,將經注分配於疏文之前;注疏本卷數,或據經注本,或以單疏本,或依據經書內容分卷,諸書不一。爲了照顧閱讀,又附錄陸氏釋文,釋文的附入,經歷附於全書末尾、段落之後、分散插於經注之下等形式[59],考慮疏文和《經典釋文》的版本優劣,釋文如何插入,使用什麼版本的《經典釋文》,還是依據南宋如余仁仲本已附釋文者,類似問題,在重新搭配經文、注文、疏文和釋文時,必須仔細推敲,方能相輔相成,互相爲用。
經學、經學文獻研究是專門之學。整理《十三經注疏》,抑或重編“十三經注疏”,一定要熟讀經書,梳理前賢工作。若率意爲之,追求名利,則有百害而無一益!
結語:《十三經注疏》是儒家的核心文獻,是研究經學和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石。自南宋初年以來,爲了讀書的便利,首先在越州(今浙江紹興市)出現了半頁八行的注疏合刻本,此後在福建建陽地區雕版附有陸德明釋文的“附釋音注疏本”,附釋音本較之八行本,經注文音義,一覽即知,十分便利。元代泰定年間,翻刻宋十行本,出現元十行本,板片一直保存於福州路府學經史庫,遞經修補,刷印流傳,故有元刻明修十行本,學術界稱之爲“十行本”“正德本”。因元刻明修十行本板片壞缺,印刷本缺字太多,影響閱讀,明嘉靖年間,李元陽重刻《十三經注疏》,即閩本,又稱嘉靖本、李元陽本,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十三經注疏》。此後監本、毛本、殿本、《四庫》本先後翻刻傳抄,每次翻刻,都依據他本進行校勘,然因條件所限,善本難尋,未能從整體上改變元刻明修十行本的缺陷。清嘉慶年間,阮元立足所謂“宋本”,即元刻明修十行本,替換《儀禮注疏》《爾雅注疏》,彙校眾本,撰寫詳盡的校勘記,於南昌府學刊刻《十三經注疏》,即阮刻本。阮刻本自刊刻以來,兩百多年,風靡學界,多次翻刻,近二十多年,《十三經注疏》數次整理,不無遺憾。二〇二一年底,中華書局出版方向東教授點校的《十三經注疏》,以阮刻本爲底本,參校眾本,糾謬是正,值得一讀。然欲整理出超越或代替阮刻本的《十三經注疏》,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學術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1]清惠棟《禮記正義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70,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中華再造善本》影印。
[2]清段玉裁撰,鍾敬華校點,《經韻樓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
[3] 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18頁。關於經書注疏合刻問題,汪紹楹、張麗娟、顧永新等先生皆有討論,據以梳理,略有補充。
[4] 汪紹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考》,《文史》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25-60頁。
[5] 清錢大昕撰《十駕齋養新錄》卷13,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冊第340頁。
[6] 清錢大昕撰《十駕齋養新錄》卷2,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7冊第52頁。
[7] 清黃丕烈撰《百宋一廛賦注》,清顧廣圻著,王欣夫輯,《顧千里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4頁。
[8] 清顧廣圻著,王欣夫輯,《顧千里集》,第30-31頁。
[9] 清惠棟《禮記正義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70。
[10] 王鍔《三禮研究論著提要》(增訂本),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頁。
[11] 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第334頁。
[12] 顧永新《元貞本〈論語注疏解經〉綴合及相關問題研究》,《版本目錄學研究》第2輯,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209頁。顧永新《金元平水注疏合刻本研究——兼論注疏合刻的時間問題》,《文史》2011年第3期,第189-216頁。
[13] 張麗娟《記新發現的宋十行本〈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零葉——兼記重慶圖書館藏元刻元印十行本〈公羊〉》,《中國典籍與文化》2020年第4期,第9-16頁。
[14] 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第361頁。
[15] 元岳浚《九經三傳沿革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83冊561頁下欄。
[16] 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第393-400頁。杜澤遜主編《尚書注疏彙校》,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1冊19頁。
[17] 宋周密《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85頁。
[18] 王鍔《〈四庫全書總目〉“周禮注疏”提要辨證》,《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23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21年版,第126-141頁。李學辰《八行本〈禮記正義〉與和珅刻本〈禮記注疏〉體例比較研究》,《歷史文獻研究》第42 輯,揚州:廣陵書社2019 年版,第64-75頁。
[19] 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第376頁。
[20] 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第385頁。
[21] 張麗娟:《元十行本〈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印本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7年第1期,第4-8頁。
[22] 張麗娟《〈十三經注疏〉版本研究》,未刊書稿,此乃北京大學張麗娟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十三經注疏》版本研究”(14BTQ020)之結項書稿,張教授惠贈電子版。杜以恆先生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元十行本《儀禮圖》一部。杜以恆《楊復〈儀禮圖〉元刊本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22年第1期,第67-79頁。
[23] 井超《上圖藏〈附釋音禮記注疏〉卷二十五殘葉跋》,未刊稿,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井超惠贈電子版,又見“学礼堂”微信公众平台,https://mp.weixin.qq.com/s/3kGkcsnNLPBJn50R3Z73tA。
[24]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賈貴榮輯《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第9冊第142頁。
[25] 張麗娟《元十行本注疏今存印本略説》,未刊稿,北京大學張麗娟教授惠贈電子版。
[26] 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第354-385頁。
[27] 王鍔《明清〈禮記〉刊刻研究》,未刊書稿,是筆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明清時期《禮記》校勘整理與主要刻本研究”(17AZW008)之結項書稿。
[28] 王鍔《元十行本〈附釋音禮記注疏〉的缺陷》,《文獻》2018年第5期,第59-73頁;王鍔《禮記版本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387-423頁。
[29] 郭立暄《元刻〈孝經注疏〉及其翻刻本》,《版本目錄學研究》第2輯,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版,第307-313頁。程蘇東《“元刊明修本”〈十三經注疏〉修補彙印地點考辨》,《文獻》2013年第2期,第22-36頁。
[30] 楊新勛《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明修叢考——以〈論語注疏解經〉爲中心》,《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第171-181頁。張學謙《元明時代的福州與十行本注疏之刊修》,《歷史文獻研究》第45輯,揚州:廣陵書社2020年版,第34-41頁。
[31] 瞿林江《爾雅注疏彙校》,未刊書稿,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瞿林江副教授惠贈電子稿。
[32] 明代永樂年間,刊刻過幾部注疏合刻本?請教杜澤遜教授,他回復説:“王鍔兄,承詢永樂刻注疏本存世情況。據弟瞭解已知存世者有三種:一、《周易兼義》,藏臺灣故宮博物院,原北平圖書館善本甲庫書,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著錄,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甲庫善本》收入。另一部在日本靜嘉堂文庫,陸心源舊藏,《皕宋樓藏書志》著錄爲明覆宋八行本。據弟校勘,實爲重刻元十行本。二、《尚書注疏》,臺灣’中央’圖書館藏,張均衡舊藏,張又得之天一閣,均定爲宋刻本,張氏影刻收入《擇是居叢書》,繆荃孫爲作校勘記附後。’中央’圖書館改定爲明初刻本。又一部藏日本靜嘉堂文庫,亦陸心源舊藏,版本著錄同《周易兼義》,實亦永樂重刻元十行本。盧址抱經樓另藏一部,傅增湘《經眼錄》著錄,有永樂刻書題識,不知下落。三,《毛詩注疏》,重慶圖書館藏,海甯許焞舊藏,黃丕烈見過,定爲元刊本,有跋。弟夫婦帶領學生到重慶通校兩遍,字體風格與永樂《周易》《尚書》如出一轍,遂定爲明永樂刻本,其底本亦元十行本。三種校勘均不精,偶有可稱道者,當是坊本。唯元十行本初印罕見,存世多明正德嘉靖修版重印,訛誤增多,永樂本尚存元十行本舊貌之八九,亦未可輕視之也。專此奉覆,即頌撰安。弟澤遜頓首。2021年12月28日。”
[33] 清顧炎武撰,嚴文儒、戴揚本校點《日知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07頁。
[34] 清張爾岐撰,《〈儀禮監本正誤〉序》,張翰勛整理《蒿庵集捃逸》,濟南:齊魯書社1991年版,第213頁。
[35] 清盧文弨著,王文錦點校《抱經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87頁。
[36] 清惠棟《禮記正義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卷70。
[37] 清張敦仁《撫本禮記鄭注考異》(顧廣圻代撰),顧校叢刊《禮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下册第1134頁。
[38] 杜澤遜《“秦火未亡,亡於監刻”辨——評顧炎武批評北監本〈十三經注疏〉的兩點意見》,《微湖山堂叢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上冊第48—54頁。王鍔《禮記版本研究》,第457頁。
[39] 杜澤遜《影印乾隆武英殿本〈十三經注疏〉序》,《武英殿〈十三經注疏〉》第1冊卷首,濟南:齊魯書社2019年版。楊新勛《武英殿本〈論語注疏〉考論》,《中國典籍與文化》2021年第2期,第50-58頁。
[40] 殿本卷十九《考證》頁2A行3-4。
[41] 侯婕《經學文獻文化史視域下的清代學術與〈禮記〉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0年。
[42] 清彭元瑞《知聖道齋讀書跋尾》卷1,《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0輯第22冊第766頁。
[43] 清彭元瑞《知聖道齋讀書跋尾》卷1,《四庫未收書輯刊》,第10輯第22冊第766頁。
[44]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上册第1-2頁。
[45] 范希曾編,瞿鳳起校點《書目答問補正》,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頁。
[46] 阮刻本《儀禮注疏》50卷,實據張敦仁本《儀禮注疏》翻刻,顧廣圻、喬秀岩等已言之。韓松岐《張敦仁本〈儀禮注疏〉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2年。
[47] 清阮元《重刻宋板注疏總目録》,阮刻本《十三經注疏》,上冊第2頁。
[48] 范希曾編,瞿鳳起校點《書目答問補正》,第344頁、第347頁、第360頁。
[49]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龔抗雲整理,王文錦審定,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50] 野間文史《讀李學勤主編之〈標點本十三經注疏〉》,《經學今詮三編》——《中國哲學》第24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81—725頁;呂友仁《〈十三經注疏·禮記注疏〉整理本平議》,《中國經學》第1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131頁。
[51]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唐陸德明釋文,呂友仁整理,《禮記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下簡稱“上古本”),上冊第5-6頁。
[52] 王鍔《三種〈禮記正義〉整理本平議——兼論古籍整理之規範》,《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4期,第363-391頁。
[53] 呂友仁先生稱“起訖語”爲“孔疏導語”。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唐陸德明釋文,呂友仁整理,《禮記正義》,上古本上冊第12頁。
[54]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呂友仁校點,《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北大《儒藏》”是指“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主持整理的“《儒藏》精華編”。
[55]“浙大《中華禮藏》”由浙江大學“《中華禮藏》編纂委員會”主持整理,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已經出版賈海生點校《儀禮注疏》50卷、郜同麟點校《禮記正義》70卷等。
[56] 清阮元校刻,方向東點校,《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版。
[57] 清阮元校刻,方向東點校,《十三經注疏》,第13冊第792頁。
[58]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日本喬秀岩、葉純芳編輯《影印南宋越八行本〈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上冊第470頁。
[59] 王鍔《再論撫州本鄭玄〈禮記注〉》,《中國經學》第27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