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碑玉器图像与巴蜀地域文化
金正林
巴蜀地区汉代碑刻的一大特色是使用玉器图像装饰。夏鼐就曾以此讨论汉代的玉器,也被别的学者使用以讨论战国秦汉时期及唐宋的瑞玉、琮瓶等。同时,因为不少碑刻见于传世的金石学著作《隶续》中的摹刻,清代就有人怀疑这些碑刻的真实性,直至今日,仍有学者持此观点。实际上,考古出土的王孝渊碑即可佐证这些玉器图像的真实性,学界却少有关注。这些图像集中出现在巴蜀地区的汉碑上,既有整个时代的大传统和大背景,也有巴蜀地区的区域传统和地域背景,反映出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基于此,笔者不揣谫漏,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巴蜀地区汉碑上的玉器图像,进而探讨其文化内涵和社会背景。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巴蜀汉碑中的玉器图像
迄今所见的装饰玉器图像的汉碑,数量并不多,依次分述如下:
(一)王孝渊碑
1966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郫县犀浦二门桥附近的蜀汉砖券墓中。据碑文“永建三年六月始旬丁未,造此石碑,羊吉万岁,子孙自贵”,可知石碑建造于东汉顺帝永建三年(公元128年),原应立于王孝渊墓前,后被二次利用,作为蜀汉墓护壁。石碑高255厘米,呈上窄下宽的梯形。石碑正面分为上下两栏,上栏浮雕朱雀、男女像及跪女像各一,下部刻隶书碑文十三行。碑两侧还分别浮雕龙、虎衔璧图像。其背面亦分为上下两栏,上栏浮雕头举日月,尾部交缠的伏羲、女娲。伏羲、女娲之间为跳舞的蟾蜍。下栏上部浮雕麒麟与凤凰,最下方浮雕龟蛇缠绕的玄武。背面中部浮雕玉器与牛首(图一)。该碑有可能是迄今所见最早用玉器图像装饰的汉碑。作为考古发掘品,其真实性当无疑问。对比王孝渊碑碑阴的玉器图像,可以知道《隶续》中摹刻的玉器图像虽然有失准确,但真实可信,绝非向壁虚构。
碑阴装饰的玉器图像可分为三列。左列上部图像残存部分呈长条状,上端作三角形,下端为矩形。等腰三角形的浮雕尖端表明该图像是圭。其下图像呈圆形,中间有方孔,即璧。中列上部浮雕仅残存下部边缘,呈多角形,其残痕中部似有圆孔。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玉部》“琮”说:“瑞玉。大八寸,似车釭。”徐锴《系传》:“谓其状外八角而中圆也。”明确当时人认为琮呈外缘八角,内部圆孔形状,类似多角圆孔的轴承用具车釭。林巳奈夫曾据此考证洛阳西郊4号墓出土的一件八角形石片就是战国中期的琮。再结合《隶续》中摹刻其他碑刻上的多角形来看,这些图像应当也是呈多角圆孔形的琮。
琮之下的区域残损较严重,仅存类似“︼”形的图像。在《隶续》摹刻的汉碑材料中,益州太守碑、柳敏碑和双排六玉碑上均有一个类似“︻”的图像。《说文解字·玉部》“瑁”说:“诸侯执圭朝天子,天子执玉以冒之,似犂冠”。《说文》解释“瑁”似“犂冠”,“ 犂冠”即犁铧头。因此这类图像当为瑁。右列上部的图像,与左列上部浮雕的圭相似,仅是残存的尖端为直角三角形,下部还留有矩形的残痕,因此这个图像当是璋。下部浮雕图像保存较好,整体呈半圆形,中部有方形的孔。《白虎通·瑞贽》:“方中圆外曰璧。半璧曰璜”,该图像正是“璜”。
图一:王孝渊碑背面下栏
(二)益州太守碑
除了出土实物,金石学文献中也有关于汉碑中玉器图像的记载,集中在南宋洪适编纂的《隶释·隶续》中。《隶续》卷五《益州太守碑阴》可见其碑刻形制与装饰图像:碑整体为上窄下宽的梯形,玉器图像分为两列。左列自上而下依次是璋,璧。右列自上而下依次是瑁、圭、琮。碑阴的其他图像可分为两组,上部位于玉器之间的是九尾狐、麒麟和回首向上的兽。最下方是牛首与碑阴题名(图二,1)。同卷还摹刻了益州太守碑的正面,上朱雀,下玄武,龙虎衔璧位于两侧(图二,2)。《隶释》卷十七《益州太守碑》:“永寿元年三月十有九日,益州太守□君卒……吏民□□立石纪迹”。该碑虽未载刻碑树立的年代,当应距离碑主去世的东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不远。益州太守碑应由其门生故吏们立在蜀地,也是一座墓碑。
图二 《隶续》摹刻的益州太守碑
1.碑阴 2.碑阳(1、2.分别采自《隶释·隶续》,第322、321页)
(三)柳敏碑
据文献记载,柳敏碑位于南宋夔州府黔州,即今重庆黔江地区。柳敏碑整体呈圭形,碑面可分为上中下三部分。背面中部装饰的玉器图像分为三列,左列自上而下依次是琮、璋、璜,中列图像呈圆形,中部孔较大,应为环,右列自上而下依次是瑁、圭、璧。牛首居中,为玉器所环绕。上部为三角形,内装饰一禽鸟,可能为凤凰,下部是带翼麒麟(图三,1)。正面碑刻也分为三部分,上部三角形装饰朱雀,中部为碑文,下部装饰玄武(图三,2)。柳敏碑是第三通纪年明确的装饰六玉图像的碑刻。《隶释》卷八《柳敏碑》:“建宁元年,县长同歳楗为属国赵台公愤然念素帛之义,其二年十月甲子为君立碑”。柳敏在东汉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被蜀郡太守察举后不久即去世,直到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才立碑。
图三 《隶续》摹刻的柳敏碑
1.碑阴 2.碑阳(1、2.分别采自《隶释·隶续》,第320、319页)
(四)双排六玉碑
据文献记载,南宋时该碑位于渠县冯绲神道中。双排六玉碑整体呈圭形,碑背面分为上下两部分,玉器图像位于下部,分为三列,左列是瑁和圭,中列是琮和璜,右列是璋和璧。上部呈三角形,内为九尾狐与三足乌相向。玉器图像之下是麒麟(?)与仙人骑鹿,最下为牛首。同时,碑的正面分为两栏,上栏三角形内为朱雀,下为玄武。但中部未刻字(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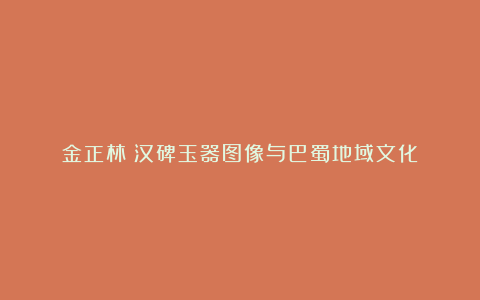
图四:《隶续》摹刻的双排六玉碑
1.碑阴 2.碑阳(1、2.分别采自《隶释·隶续》,第323、324页)
(五)单排六玉碑
据文献记载,单排六玉碑也位于达州渠县,应在冯绲神道附近。该碑整体呈圭形,碑面装饰玉器图像位于中部,分为三列,左列是圭、璜,中列偏下是璧、琮,右列是璋、璜。最上和最下分别是朱雀与龟蛇缠绕的玄武(图五)。
图五 《隶续》摹刻的单排六玉碑
(采自《隶释·隶续》,第325页)
表一:汉碑玉器图像及其组合的统计
这五通装饰玉器图像的碑刻年代都集中在东汉中晚期,尤其是桓灵时期;地域上则是集中于巴蜀地区,主要都是墓碑。如表一所示,装饰玉器图像的碑的形制主要是梯形和圭形。各碑装饰的玉器图像位置并不固定,种类如表一所示。除了璋、璧、琮较为固定,图像组合也较为随意,未见如经书中“五瑞:珪、璧、琮、璜、璋”的固定排列顺序。总的来说,只要将玉器图像置于同一碑面即可。其他牛首、四神和仙禽瑞兽等图像的种类、数量、组合、位置等均未见固定模式。
二、汉碑玉器图像的功能及其属性
(一)汉碑玉器图像的功能
《国语·楚语下》记载楚昭王问观射父祭祀之事,观射父言:“夫神以精明临民者也,故求备物,不求丰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纯、二精、三牲……玉帛为二精”。《集解》引韦昭注“备物,体具而精洁者”。可见在时人眼中,玉器的特色是“精洁”,与祭祀活动关系密切,即以玉器与牺牲来祭祀祈祷,以通其神。考古遗存的发现,则有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祭祀坑、陕西凤翔马家庄秦国宗庙遗址以及山东成山发现的战国时期祭祀用玉。这些祭祀遗存的用玉情况也表明,这一时期的祭玉以圭、璧为主,兼有玦、环以及碎玉片等多种形制,祭祀对象也较为多样。战国时期楚地出土的卜筮祭祷简中,明确提到以玉器来祭祀包括墓主祖先在内的不同神灵,如包山楚墓随葬的卜筮祭祷简中便有使用环、少环、玦等不同玉器祭祀不同对象的记载。近来新发现的若干秦至西汉时期的国家祭祀遗址表明,祭祀用具的主体仍是玉器。从祭祀用玉组合的角度看,《白虎通》所载五瑞中的“圭、璧、琮、璜、璋”,均已存在,尤其是早期的玉人伴随西汉王朝的礼制建设,逐渐淡出。这种现象正与东汉碑刻上的玉器图像,主体是圭、璧、琮、璜、璋、瑁相统一。
目前虽未发现很典型的东汉时期官方祭祀用玉遗存,但以玉祭祀的实践及用玉礼神的观念一直在延续。《后汉书》载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故荐嘉玉洁牲,以礼河神”,李贤注引《礼记》:“凡祭玉曰嘉玉”。这是汉朝中央朝廷举行的国家祭祀,上行下效,各地方举行的祭祀活动也仍以玉器作为祭品。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三公山神碑》:“荐圭璧牺牲四时祠”,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封龙山颂碑》:“宜蒙圭璧七牲法食”,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1年)《无极山碑》:“七牲出用王家钱,小费蒙大福,尊神以圭璧为信……为民来福以祠祀为本,请少府给圭璧,本巿祠具”。可见作为地方祭祀贡品的“圭璧牺牲”的功用也是“为民来福”,对理解汉碑上玉器图像的功能具有重要价值。虽然目前所见主要是巴蜀地区的中下层士人使用玉器图案装饰碑刻,其身份等级、使用场域和祭祀对象均与前述官方组织的国家祭祀活动有别。但是不论祭祀对象为天神、地祇或人鬼,玉器作为时人眼中的“精洁”之物,正是较好的祭祀贡品。这种视玉器为“精洁”之物,适宜祭祀求神的观念,应当是东汉时期社会上的一种普遍观念,尤其流行于当时的士人阶层中。不论是生活在东汉早期的中低层士人王充撰写的《论衡·明雩》:“礼之心悃愊……悃愊以玉帛效福”,还是东汉末年的高官荀悦撰著的《申鉴·俗嫌》:“祈请者诚以接神,自然应也。故精以底之,牺牲玉帛,以昭祈请,吉朔以通之”,均表明这种观念贯穿整个东汉时期的士人阶层。作为国家祭祀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士人阶层亦普遍掌握使用玉器祭祀求福的知识,参与日常祭祀活动。或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玉器图案在东汉中晚期的巴蜀地区被当地的中低层士人群体装饰到祭祀先人的碑刻上,将之作为祭品以供祀碑主,起到通神祈福的功能,达到《王孝渊碑》《柳敏碑》等碑文中:“造此石碑,羊吉万岁、子孙官贵”、“建竖斯碑,传于万世,子孙繁昌,永不漫灭”的目的。
巴蜀汉碑上的装饰,并非仅有玉器图像。同一碑面的其他图像大致可分为三组,一组便是朱雀、玄武与两侧的龙、虎图像构成的四神组合,另外一组是麒麟、凤凰、九尾狐、伏羲、女娲等瑞兽与仙人图像,最后一组便是多位于碑面下方,或为玉器环绕的牛首图像。牛是古代祭祀活动的重要用牲,按照战国秦汉时期礼学家构建的祭牲序列,牛是诸牲之首。《礼记·曲礼》:“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玉曰嘉玉”。《礼记·王制》更明言:“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陕西凤翔马家庄秦国宗庙遗址发现了牛骨坑86个,可分为三种祭祀形式,全牛、牛身祭祀和头蹄祭祀。因此碑面上被玉器换绕的牛首,应该象征着各类祭祀用牲。故而牛首与玉器的组合就是“圭璧牺牲”,自然可以昭所祈请,福佑通吉,起到祭祀来福的作用。
(二)汉碑玉器图像的属性
正如夏鼐先生所言:“这些图(引者按:指玉器图像)是汉人依据《三礼》经书和汉儒的注释而加以想象绘成的。”因此,玉器图像不是简单的装饰图像,而是经战国秦汉时期的经学家系统化、理想化之后的礼器系统之一,承载着经学意义的瑞玉与祭玉。《尚书·尧典》篇:“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提到了“五瑞”“班瑞”,并未确指“五瑞”为何物。至相传为西汉伏生所做的《尚书大传》就解释为:“舜修五礼、五玉、三帛”,并从诸侯朝觐天子之礼仪用具来阐发圭、瑁之寓意。到了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由班固将章帝亲自主持、裁决的经学辩论成果整理为今文经学代表作《白虎通义》。其《瑞贽》篇已经明确将五瑞解释成:“何谓五瑞?谓珪、璧、琮、璜、璋也”,并且融合阴阳五行学说,立足关联式宇宙论,阐发五瑞、五方、五色、五德等联系与意义,谓之“五玉所施非一,不可胜条,略举大者也”。同篇在讲朝觐之仪时,讲“瑁”的作用,“合符信者,谓天子执瑁以朝诸侯,诸侯执圭以觐天子。瑁之为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可见这时已经延续《尚书大传》的传统,将瑁和五瑞共同相配成六玉,而没有琥。
不同于《尚书大传》等今文经系统中将瑁与五瑞相配。属于古文经系统的《周礼》则是将五瑞与“琥”相配,如《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又见《秋官·小行人》:“合六币:圭以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锦,琥以绣,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诸侯之好故。”只有被后人补入其中,并非古文经系统的《考工记》中提到了“瑁”,《考工记·玉人》:“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郑玄注:“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盖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为贵”。
如表一所示,目前所见的巴蜀汉碑装饰的玉器图像,均无琥;四通碑有瑁。从玉器种类的情况来看,表明《白虎通义》等今文经学传统的影响更大。同时这五通碑刻集中分布在巴蜀地区。巴蜀地区不同于东汉中晚期中原地区流行的古文经学,正是今文经学大盛之地。集中体现在当地士人熟习的经典派别中,像巴郡阆中人杨仁“诣师学习《韩诗》,数年归,静居教授”;广汉郡梓潼人景鸾“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 作《易说》及《诗解》……又作《月令章句》”;广汉新都杨统“代修儒学,以《夏侯尚书》相传”;蜀郡繁人任末“少习《齐诗》,游京师,教授十余年”;犍为郡武阳人杜抚“少有高才。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后归乡里教授……弟子千余人”;蜀郡郫人何随“治《韩诗》《欧阳尚书》,研精文纬,通星历。”。正因为东汉时期巴蜀地区今文经学氛围浓厚,与中原地区古文经学日益兴盛形成了鲜明对比。东汉末年的梓潼郡涪县人尹默才以“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由此可见,东汉中晚期以来巴蜀地区浓厚的今文经学与图谶传统,正是上述玉器图像孕育而生的知识与观念背景。
三、玉器图像与巴蜀碑刻的地域传统
玉器图像是汉碑中一种较特殊的图像,且集中分布在巴蜀地区。因此这些碑刻不论整体形制,抑或装饰图案,均显示出浓厚的巴蜀地域传统,尤其表现在“碑”与“阙”的含混性。
先来看碑刻的整体形制,汉代巴蜀地区的碑、阙之别并不明显。王孝渊碑和益州太守碑整体呈梯形。但是现存的王孝渊碑实物表明,碑身上端有榫口。此碑“上端正中有一长17、宽12、高9厘米的榫头;下端有一长26、宽16厘米凹进去的浅窝”。因此此碑当上有拼装的顶部构件,下端有基座。2010年四川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的蜀郡太守李君碑和蜀郡太守裴君碑(图六),均提供了较好的例证。根据碑文,李君碑,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立,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重立;裴君碑,顺帝汉安三年(公元144年)立,桓帝元嘉二年(公元152年)重立。王孝渊碑立于顺帝永建三年(公元128年),与李君碑初立年代不过5年。益州太守碑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立,距离裴碑重立年代不过3年,距离初立年代也仅11年。四通碑地域相近,时代相仿,碑身形制均为上窄下宽的梯形,实际上是对汉代石阙的模仿。李君碑、裴君碑的碑首是“迭落式四阿顶”,这种碑首与汉阙的阙顶极为相似,应该是吸收其相关因素。王孝渊碑与益州太守碑也应拼装类似的顶部构件。此类阙形碑,目前仅见于巴蜀地区。
图六 成都天府广场出土裴君碑、李君碑
1.裴君碑 2.李君碑
(1、2.分别采自《成都天府广场东御街汉代石碑发掘简报》第3、6页)
其次是装饰图像。正如前文所述,除了“牛首与玉器”的图像组合具有祭祀功能,巴蜀地区汉代碑刻中还多装饰一组象征方位的四神图像和一组营造神仙氛围的瑞兽图像。三组图像均多见于汉代巴蜀地区其他的石刻艺术中。综合来看,汉代巴蜀地区碑、阙之别并不鲜明,较为含混。不论碑或阙,均与其他石刻艺术共享一套装饰图像组合,凸显出这一区域重装饰,杂糅多种功能于一身的地域传统。
纵观装饰玉器图像的石碑,不论见于金石学材料而不存实物,抑或新近出土的考古遗存。从装饰图像到整体形制都呈现出相似的风貌与特征,可以证明这些遗存均带有浓厚的汉代风格,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同时,这些石刻也展现了汉代巴蜀地区石刻艺术,重装饰、兼具礼仪功能与神仙氛围的地域特色,庶几近之左思《蜀都赋》:“一经神怪,一纬人理”。
附记:本文的写作是在四川大学霍巍教授和王煜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焦阳老师和顾大志同学也给予了许多帮助,谨致谢忱!另本文受到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双高计划”项目支持。
本文原载《考古》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