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国学堂2025-03-09 11:52广东
#春季图文激励计划#
以古为师,悉心交流!敬请关注收藏“大成国学堂”!
(续上)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秾芳诗》,此为绢本,朱丝阑瘦金体书,其独特之处在于,宋徽宗的瘦金书多为寸方小字,唯独《秾芳诗》为大字,凡 20 行,每行仅书 2 字,用笔酣畅淋漓,锋芒尽显,傲气十足,有断金割玉之气势。诗是这般写的:
秾芳依翠萼,
焕烂一庭中。
零露沾如醉,
残霞照似融。
丹青难下笔,
造化独留功。
舞蝶迷香径,
翩翩逐晚风。
舞蝶、迷香、残霞、晚风,自然的美轮美奂,似乎尽在赵佶的掌控之中,不费丝毫力气,便自他的笔端流淌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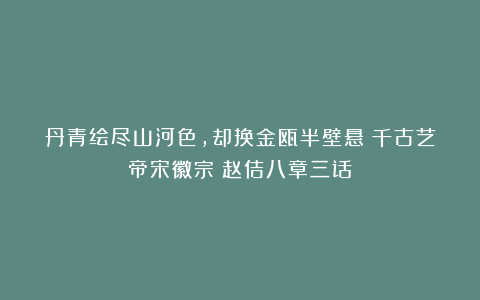
园林乃书写的绝佳场所。宫殿并不适宜书写,宫殿适合朗诵,将皇帝的意志高声朗诵出来,通告天下,因而宫殿高大宏伟,尽可能地敞开,而四周的配殿和宫墙,则恰到好处地增添了它的音响效果。舒适的后宫适合书写,诸多皇帝都有于后宫办公的习惯,譬如紫禁城养心殿,自雍正至溥仪,清朝共有 8 位皇帝将此处当作寝宫,但即便在后宫,书写的内容也大抵与朝政相关,清朝因不设宰相,皇帝事必躬亲,所以在此,皇帝每日要面对堆积如山的奏折,完成他的 “家庭作业”。
唯有苑囿,才适合书写些诗意文字。倘若说宫殿建筑尚有某种公共性,为朝廷政治服务,那么皇家园林则仅为皇帝一人服务,连大臣进入,都需经过特别许可,这个空间内所讲述的,已非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官方关系,而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因而更为私密、更具个人化,更契合宋徽宗式的游戏人生,而书法本身,并非全然以实用为目的,而更似一种艺术上的游戏。
像艮岳这般的皇家园林,必定会长出瘦金体这般的文字植物,反过来说,瘦金体只能在艮岳这样的土壤中生长,只能由艮岳的甘泉浇灌,因为一种书法风格的形成,与环境紧密相连,甚至于,一种风格,便是对一个世界的精准表达。儒家讲 “格物”,通过 “格物” 来 “致知”,物质世界与人的内心世界具有某种同构性,人们需要从物质世界中去深究 “物理”。
那么,作为艺术的书法亦是如此。赵佶的书法,不单是书法,亦是音乐,是建筑,是花卉,是美食与美器,是上述一切事物的混合体、综合物。它们皆是赵佶的一部分,相互酝酿,相互生成,无法拆分。
瘦金体乃典型的帝王书法,它与帝王的极端主义美学品位相联。它是皇帝的专属,甚至于,连皇帝也极难写出 —— 中国历史上 83 个王朝 559 个皇帝,也唯有宋徽宗一人写出这样的字。没有一人能如宋徽宗那般,拥有如此强大、丰饶、富丽的气场,也没有一人像赵佶那样善于从这庞大的气场上提炼出书法的金丹。瘦金体,近乎成为中国艺术中的孤品,空前绝后,独领风骚。在宫殿、苑囿、印玺之上,它成为无可比拟的皇权徽章,甚至,它远比君权还要不朽。
许多人言,赵佶是入错了行,他应当只做艺术家,不做皇帝,若不做皇帝,就不会有后来凄惨的结局。但于我而言,若无帝王、尤其是宋代帝王极端绮丽的生活品质,他亦难以创作出这种极端主义的字体。这是他的悖论,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悲剧。上帝乃大戏剧家,早已为每个人安排好了角色,他无从躲避。
人生不忍细述,还是看他的字吧。面对《秾芳诗》,我不止一次于心中复原他写字时的模样。他写字之时,其神态应当是专注的,聚精会神。在他身旁,龙涎的香气缭绕着,于空气中漫漶成繁复的花纹。对于这种若有若无的奇香,后人有如此描述:“焚之则翠烟浮空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烟缕,所以然者入蜃气楼台之余烈也。” 龙涎香的烟缕,竟有形可依,可以用剪刀剪开,丝丝缕缕,如赵佶的笔在笔洗里漫漶出的墨痕。
我想象着,在龙涎的芳香中,赵佶的脸上浮现出迷醉的神情,有点似太白醉酒后的那种沉醉感,又像做爱时的兴奋,只不过并非与女人做爱,而是与纸做爱。冰肌雪骨的纸,柔韧地铺展着,等待他的耕耘。赵佶的笔,就这样将龙涎香的烟纹一层层地推开,落于纸上。他以行书笔调来运笔,使他的一切动作皆富有节奏韵律的美感,故而不仅他的字美,他写字的过程亦定然是美的。瘦金体的字迹,仿若自身体深处涌起的一种电击般的兴奋,一层层地荡漾开来。
他所用是一种细长的狼毫,极难掌控,但它提供了一种塑性的抵抗力,赋予笔画一种锋利之力,能于细微的差异中传达出书写者鲜明的个性。将近 900 年后,末代皇帝溥仪也在自己的宫殿里试图复制这种笔,他偏爱赵佶的书法,紫禁城里更是搜集了许多真迹,其中便有《赵佶秾芳诗帖》、《宋徽宗赵佶恭事方丘敕绢本》、《赵佶蔡行敕》。他一遍遍地模仿,揣摩赵佶的心境,每当此时,他便感觉 “中国书法的巨人在引导着他的手,授权给了他每一笔、每一画、每一个字中存在的书法秘诀”;
他写坏了许多支笔,于是为这些笔制造了一个笔冢,为每一支笔都修了一个小小的棺木,立了碑,还写了碑文,包括制笔者的姓名、开笔和封笔的日期等等,不过这些皆为据说。唯一能够确认的,是溥仪如同赵佶一样,从这些笔墨出发,走向了囚徒的营地。
皇权助了他的艺术,他的艺术却挖了皇权的墙角。
04
血红的宫墙划分出了天堂与地狱的界限。依循物质的守恒定律,当帝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汇聚至少数人身旁,在更广阔的国土之上,则必然出现物质匮乏、饥馑乃至死亡。
当宋徽宗的宫殿每夜皆要消耗数百只名贵的龙涎香,当蔡京的府中做一碗羹需杀掉数百只鹌鹑,这个帝国早已是 “两河岸边,死丁相枕,冤苦之声,号呼于野”。其实,早在公元 1100 年,赵佶登基之初,便有一位名叫钟世美的大臣上奏:“财用匮乏,京师累月冰雪,河朔连年灾荒,西贼长驱寇边,如入无人之境。” 但庭院幽深,门禁森严,宋徽宗沉浸于他的艺术天地里,永远听不到宫墙之外的呻吟与呼喊。在如此浩大的宫苑中,所有不合时宜的声音皆会中途夭折。宋徽宗置身人间仙境,觉着生活美好,生命欢愉,他不明白方腊、宋江缘何要揭竿而起,不明白为何总有人与这个朝廷过不去。
他喜爱炫富,不炫富便浑身不自在。倘若向他人炫富倒也罢了,可他偏偏要向金国的使者炫富。但饱汉不知饿汉饥,宋徽宗不计后果的炫富,对于物资匮乏的金国而言构成了极大的刺激。据古气象学家的研究,唐末至北宋初期(公元 800—1000 年)乃是气候温暖、冬温少雪的 “中世纪温暖期”(Mediaeval Warm Period),而自宋徽宗时代起始,一直到南宋中叶(公元 1110—1200 年)则气温低寒,雪灾频繁,冬季漫长,是典型的 “小冰期”(Little Ice Age),亦是中国历史近 3000 年来的第三个寒冷期(Cold Period)。来自中亚细亚内陆沙漠的冬季干燥季风掠过中原,致使北宋出现大面积沙漠化。宋徽宗政和元年(公元 1111 年),淮南旱;政和三年,江东旱;政和四年又旱,皇帝下诏,“赈德州流民”。
与中原农耕民族相较,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对气候的依赖更为显著。公元 1110 年,辽国(当时金国尚未建立)大饥,“粒食不阙,路不鸣桴”。北宋政和四年、公元 1114 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率领 2500 人,在来流水起兵反辽,一年后创立大金国,十年后灭掉大辽国,而后挥刀直指北宋。
在物质丰饶之时,享乐或许是个人之权利;但在民不聊生之岁月,奢侈便是罪孽,不仅需承担道德上的责任,甚至应当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宋徽宗享乐的直接后果是:公元 1120 年,方腊率众于歙县七贤村起义。起事时,方腊之妻浓妆艳抹,前胸缀嵌一大铜镜,对着太阳行走,远远望去,光芒耀眼,在无数百姓眼中成为毋庸置疑的祥瑞之兆,于是纷纷入伙。方腊之乱,惨死者逾 200 万人。
(鸣谢祝勇先生才情之作!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