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辑
中国中古的河西走廊
西北所出汉代簿籍册书简的排列与复原[1]
——从东汉永元兵物簿说起
百余年来,汉代张掖、敦煌两郡范围内出土大量与屯戍有关的简牍,内容丰富多样,其中很多是各种类型的簿籍。对此,自王国维开始就不断有学者加以研究,成果斐然。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同类簿籍的集成与同一册书的复原,在这方面,森鹿三、陈公柔、徐苹芳、鲁惟一(Michael Loewe)、永田英正、大庭脩、谢桂华与李天虹等均做出过重要贡献[2]。关于汉简册书复原的方法也不断有学者加以总结与反思[3];对于簿籍的性质与关系,亦有学者反复深入探讨[4]。不过,这类簿籍的研究上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
仔细分辨,学者对于簿籍的构成,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些实际默认“簿籍”单独构成一类文书,因此在归纳“簿籍”时只收入相关标题简与内容简,并未包含相关的上呈文书之类的内容,账簿加上呈文则称为“会计报告”[5],而有关文书则被认为是正文,簿籍属于附件[6]。另有学者在讨论簿籍时则一并包含呈文(或称送り状〔呈送状、送状〕、呈报,以下统称为“呈文”)[7]。但对于以簿籍为主体的文书是如何排列的,却少有明确讨论[8]。涉及到呈文在簿籍册书中的位置时,针对不同的册书,意见仍有分歧,自然得出的这些簿籍诸简的排列也就不同。
具体而言,关于“橐他莫当燧守御器簿”中的“始建国二年五月丙寅,橐他守候义敢言之:谨移莫当燧守御器簿一编,敢言之”简(73EJF16:1537),除去1978年发表的《简报》认为置于册书之首外,其余学者(包括简报作者后来的论述)多认为应置于册书的末尾[9];而关于甲渠候官出土的“始建国天凤亖年当食者案”(EPT68:194-207),则几乎都认为呈文位于册书之首[10],以至有学者认为簿籍的“呈文”或位于一册文书的最前(如EPT68的“当食者案”)或最后(如 “永元兵物簿”)[11]。究竟是否如此,可惜至今未见学者进一步讨论。这枚(有时会是两枚,甚至三枚)小小的呈文位于册书何处,牵涉到如何复原西北汉简中数量最为庞大的簿籍类文书。另外,有不少文书虽非簿籍,但亦包含类似的呈文,如起诉官吏的“劾状”,呈文在此类文书中的位置亦是见解不一[12],这些都表明此问题不可不辨。本文将围绕此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由出土编绳尚存的簿籍简册论一般簿籍的排列
要确认呈文的位置,最稳妥的办法是参考出土时原有编绳尚存的同类册书。为此,我们先从现存最长、最完整的东汉永元兵物簿说起。
东汉永元兵物簿(128.1)出土于A27(查科尔帖),遗址在汉代究竟属于哪个机构尚无定论[13]。此簿是由77枚简组成的一册,编绳完好,全册由编绳分四次连缀在一起,内容涉及不同年份的五份簿书,具体分为月言簿(简1-16、17-32、33-48)与四时簿(简49-77,两份)两种。时间是从永元五年六月、七月、永元六年七月、永元七年正月至三月、四月至六月,跨三年,从笔迹看前两份月言簿出自一个书手之手,后一份月言簿与两份四时簿由另一书手抄写,整个簿册被认为是文书的副本[14]。各个簿书的时间不同,但格式基本一致,茲引录格式最为齐整的第二份簿书如下:
其余四份簿书内容不同,但格式基本相同。这种兵物簿的格式可概括如下:
构成此册书的五个簿书的核心或为“月言簿”,或为“四时簿”,均为按月、按时定期编制的簿书,“呈文”所记的日期可视为簿書完成的下限。五个簿书编成的日期下限见下表:
|
名称 |
永元五年六月官兵釜磑月言簿 |
永元五年七月見官兵釜磑月言簿 |
永元六年七月見官兵釜磑月言簿 |
永元七年正月尽三月見官兵釜磑四时簿 |
永元七年四月尽六月見官兵釜磑四时簿 |
|
日期 |
五年六月壬辰朔一日壬辰 |
五年七月壬戌朔二日癸亥 |
六年七月丙辰朔二日丁巳 |
七年三月壬午朔一日壬午 |
七年六月辛亥朔二日壬子 |
五个簿书先后跨了三个年份,但编成的下限均在月或三、六、九、十二月的一、二日,可见这种簿书的编制有其一定之规,下属的部则是照例执行。当然这种由部制作的簿书都是要上呈候官,乃至更高级别的机构,所以会附有“呈文”。这种按照一定时间间隔编制的簿书属于“定期簿书”,加上“呈文”构成“定期文书”[15]。这种“定期簿书”的特点之一就是有固定的名称,且反复按一定时限编制,不需要上级下达命令,下级机构就会按期制作,所以我们可以找到不少相应的标题、内容与呈文,而找不到有关的下行文书。“兵物簿”就是一例,鲁惟一、永田英正与李天虹均搜集到不少关于兵物、守御器之类的简[16]。
值得注意的是,与簿书相连的“呈文”是置于簿书的最后,簿书最前面则往往是带有“●”的标题简。这在类似的簿书简的排列中是否为孤例呢?是否仅是东汉的制度呢?不是。敦煌悬泉出土的西汉簿书亦采用了相同的排列方式。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简Ⅰ90DXT0208②:1-10发现时两道编绳尚存,上道完整,下道前半部分残损,简则多有残断。按简上的称呼名为“传车亶轝簿”。先依原简格式移录释文如下:
观察图版,此册为相当工整的隶书,各简笔迹相同,应为一位书手一次书写而成,先写后编,从右侧开始编,两道编绳的绳結均系在最左侧简旁。前面9枚均为单行的札,最後一枚为两行。此册为上行文书,收件人应是效谷县,却发现于发件人处,有些奇怪。且此册日期、官吏名字完备,一次写成且字迹相当规整,应该不是草稿,或属于待发的正本,也许是存档的底本[19],此点犹需研究。
册书上呈的时间是西汉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闰三月壬申朔癸未,为十二日,非月初月末,似为不定期编制的簿书,不过,悬泉传舍为悬泉置中机构之一,任务就是接待往来的官吏、使者,传车是必不可少的装备[20],定期清点传车的完损情况,事关传舍能否正常运转,应属重要工作。悬泉简中尚有关于传车的资料,如:
“十二月餘”显属某种月度或四时簿书统计上的用语[22],表明存在某种连续定期编制反映“传車”状况的簿书。与传車密切相连的“传馬”名籍有多种,此外,还有标题简“·縣泉置元康三年九月官牛簿”(Ⅱ90DXT0111④:1)、“·縣泉置初元年十月官牛车簿”(Ⅴ92DXT1311③:134)[23],上引“傳車亶轝薄”当属某种定期编制的传车簿书,月言簿或四时簿均有可能,与居延地区烽燧上编制“兵物簿”类似。只是目前悬泉简仅公布很少一部分,相信其中包含大量相关内容。正因为是定期簿书,没有下行的命令,并有固定的标题。
此册书关涉本文之处在于十简的排列,尤其是“呈文”的位置。有论者认为前三简应是“第一傳車一乘”、“第二傳車一乘”、“第三傳車一乘”[24],很有可能。只是第一枚简残存两字为“敦煌”,其下空白,或许第一传车当时不在置中,被调往敦煌。传车在各置之间接力迎送官吏、使者,很是常见[25]。若此说成立,则此册书没有标题简,只有最后的“呈文”。
这是两件基于定期簿书构成的定期文书,呈文均置于簿书的末尾,即整个文书的最后。再来看看“不定期簿书”与“不定期文书”。所谓“不定期簿书”是指临时根据上级的命令而编制的簿书,基于这种簿书的文书不仅包含呈文,还有上级下达的命令(来文),整个文书的构成更为复杂。我们也要先从保留有编绳的册书入手。
悬泉置遗址中出土一件由6枚简组成,两道编绳完好如初的册书“建昭三年付懸泉廄穬麥簿”,茲依格式转引录文如下:
本册书前5枚简为“札”,最后一枚为中间起脊的“两行”,账目使用“札”,呈文则用“两行”。具体内容是渊泉县移送悬泉置的文书,告知该县派遣吏与御带领传马送迎使者时已经提供了多少廩粮,要求计入悬泉相应的廩粮出入簿书。这实际是将临时发生的事务纳入到定期簿书中,此册书本身记录的是一件临时发生的迎送接待事务(“遣吏、御持傳馬送迎使者諸國客”)中涉及的粮食出入。河西四郡地处中西交通孔道,往来的人员很多,且事务出现时间不固定,迎来送往的随机性事务很多,除去定期上呈的簿书外,还有大量的按照每件事务来编制、移送的不定期文书,“不定期簿书”往往没有确定的名称,围绕它的编制会形成往来的文书。
此册书只是悬泉置接到的一件附带移文的“不定期簿书”,接到之后,当如何处理,未见资料,据同一探方出土的同类册书,“建昭元年懸泉置穬麥受簿上報書”,可以了解后续工作。先移此简册录文如下:
谛观图版,此四枚简中的第一枚与后三枚原先应分属两个册书,后被套在一起,当是事后,或按一定时限整理文书时被系联起来,如上引东汉永元兵物簿。此册书首简为中间起脊的两行,从编绳保存情况与内容看,其前面原先应还有简,出土时已脱去。后三枚为一般的札,形状并不齐整,单行书写。文字均潦草,应是某种留底性质的底本。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四枚简记录的是一件事,还是两件同类而不同的事?我现在的看法是同一件事。第一枚简开始的时间表示方式为“十月己巳”,未写年号、月朔,应是接在前文后面向下转达文书时的写法,观大庭脩复原的“元康五年诏书”册,便是如此[28]。因此,此简中的“寫移書到”的“移書”应指效谷县所接到其他同级机构的来文,并非效谷县自己下达的命令,最有可能的就是附近的某个县。而第二至四枚简涉及的时间与此衔接,同时有“廷移淵泉書曰”云云,显然命令是来自效谷县转來的渊泉县的文书,与第一枚简书写格式所反映的文书性质是一致的,两者间对下级的要求以及下级的回复之间亦相对应,加上日期相联,编绳又套在一起,视为同类同时出现的不相关的两件事,恐怕机率有点低。
为何会分别编为两个册书,恐怕册书一相当于上面所引的“建昭三年付懸泉廄穬麥簿”,是外部机构的移文与簿书,册书二是悬泉置的答复。两者同属一事务,故编联在一起。
这些穬麦出入记录如何纳入悬泉置的簿书,目前已刊的资料尚无直接的资料,但有些线索可循。我们看到有这样的标题简:
恐怕也应该有“縣泉置建昭三年七月穬麥出入薄”与“縣泉置建昭元年十月穬麥出入薄”之类的簿书。具体如何记载,“元康四年鷄出入薄”可供参考。其中的入鸡部分:
鸡属于比较贵重的食材,且为副食,只是用来招待级别较高的使者或官吏,获取与消费并不频繁,三个月编制一份簿书尚可。穬麦属于主食,消费频繁,簿书当是按月编制,但其形式应与“鷄出入簿”出入不大。据此,这种临时发生的物资出入最终会被纳入定期簿书中。可以说那些不定期的簿书只是文书作业中的一环,定期簿书与定期文书乃是其常态化的归宿。
定期簿书与不定期簿书之间的关系大体如上。而后者的构成亦是簿书在前,文书附在后面,尽管我们见到的是平行机构間的移文,下级的回复在事后则编在文书的最后。这样一种构成,实际与上引定期文书是一致的。
从上述出土时编绳尚存的册书看,无论是定期文书与不定期文书,均是先列簿书,最后是文书。其他数量庞大的散乱定期文书与不定期文书是否也是如此排列呢?有无线索可循?答案是有,那就是文书上起草与抄写者——书吏的署名。
关于文书上书吏的署名,陈梦家以来有很多学者做过研究,不过,多关注的是署名者的官职,以及与文书撰写间的关系[31]。这里讨论的是书吏的署名与册书排列之间的关系。学者曾指出,起草人的署名“通常位于正文之后或简背。凡正文与起草人书于同一面者,二者之间以界隔符’/’或空格隔开”[32]。观上引“建昭三年付懸泉廄穬麥簿”,“掾延年、啬夫竟”写在末简背面;“建昭元年懸泉置穬麥受簿上報書”则是签在文书末行的尾部,并用“/”与正文分隔,正与学者的归纳相同。需要补充的是,所谓“简背”应是指末简的简背,而非首简或其他简的背面。“元康五年诏书”,以及笔者复原的关于肩水候通知行塞而委任代理者的文书均不出这两种方式[33]。像元康五年诏书之类需要逐级抄写下发的文书,各级机构中的书吏的署名均在其所抄写的文书的末简,到达肩水候官时,其“行下之辞”便积累了多行末简。文书起草或抄完之后,书吏在末简左下角或其背后署名,亦符合抄写文书的流程,既顺手亦方便,是当时通行的做法。学者认为此点乃是汉代官府往来文书中较为固定的结构程式的一部分[34],是有道理的。
依据李天虹对居延簿籍简的整理,在“呈送”类简(即本文所说的“呈文”)中有一些就带有书吏的署名。先将此类简胪列如下,分类则依据李天虹:
|
类别 |
簿籍名称 |
简文 |
出处 |
|
俸禄 |
吏奉赋名籍 |
居攝二年二月甲寅朔辛酉甲渠鄣候放敢言之謹移正月盡三月吏奉賦名籍一編敢言之 A 令史羕 B |
EPT8:1 |
|
现钱 |
赋钱出入簿 |
陽朔三年九月癸亥朔壬午甲渠鄣守候塞尉順敢言之府書移賦錢出入簿與計偕謹移應書一編敢言之 A 尉史昌 B |
35.8 |
|
赋钱簿 |
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謹移四月盡六月賦錢簿一編敢言之 A 掾譚 B |
EPF22:54 |
|
|
奉秩別用钱度簿 |
甘露二年四月庚申朔辛巳甲渠鄣候漢彊敢言之謹移四月行塞臨賦吏三月奉秩別用錢簿一編敢言之 書即日餔時起候官 A 令史齊 B |
EPT56:6 |
|
|
谷物 |
谷出入簿 |
謹移穀出入簿一 A 亭長最B |
11.27,地湾出土 |
|
兵物 |
完兵出入簿 |
漢元始廿六年十一月庚申朔甲戌甲渠鄣候獲敢言之謹移十月盡十二月完兵出入簿一編敢言之 A 掾譚B |
EPF22:460 |
|
守御器簿 |
始建国二年五月丙寅朔丙寅橐他守候義敢言之謹移莫當燧守御器簿一編敢言之 A 令史恭B |
74EJT37:1537,金关出土 |
|
|
日常工作 |
日迹簿 |
五鳳元年二月丁酉朔乙丑甲渠候長福敢言之謹移日迹簿一編敢言之 A /候史定B |
267.15 |
|
日迹簿 |
元康元年五月乙□朔丁丑候長安世敢言之謹□四月日迹簿一編敢 A 候史□ B |
EPT57:87 |
|
|
贳卖 |
贳卖衣财物爰书名籍 |
元康四年六月丁巳朔庚申左前候長禹敢言之謹移戍卒貰賣衣財物爰書名藉一編敢言之 A 印曰藺禹 六月壬戌金關卒延壽以來 候史充國 B |
10.34,地湾出土。 “印曰”与“六月… …以來”为收文记录 |
|
牛车马 |
传驿马名籍 |
河平四年十月庚辰朔丁酉肩水候丹敢言之謹移傳驛馬名籍□□敢言之 A 令史臨尉史音 B |
284.2,地湾出土 |
|
其他 |
财物簿 |
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候放□謹移正月盡六月財物簿一編敢言之 A 掾譚 B |
EPF22:55 |
此外,敦煌汉简中同类简,见下表:
|
类别 |
簿籍名称 |
简文 |
出处 |
|
兵物 |
部铁器簿 |
永光元年二月戊戌朔辛酉敦煌玉门都尉平丞得□敢言之謹移部鐵器簿一編敢言之 A 掾子長屬通 B |
敦煌馬圈湾1064(T12:107) |
|
铁器簿 |
元康三年九月辛卯朔癸巳縣泉置啬夫弘敢言之 移鐵器簿一編敢言之 A □□長富 B |
敦煌悬泉采集1295(DQC;6) |
|
|
谷物 |
谷簿 |
神爵五年二月庚寅朔□□縣泉置啬夫弘敢言之謹移穀簿一編敢言之 佐禹∨廣德 |
敦煌悬泉Ⅱ90DXT0213③:71[35] |
|
粟簿 |
甘露四年十一月甲辰朔辛未縣泉置丞祿敢言之謹移十月盡十二月粟簿一編敢言之 掾廣意、佐世 |
敦煌悬泉Ⅱ90DXT0115④:33[36] |
肩水金关简中同类简,见下表:
|
类别 |
簿籍名称 |
简文 |
出处 |
|
不明 |
就人载谷名□ |
朔四年十一月丁巳朔庚辰肩水候宗移橐佗就人載穀名□A 守令史音 B |
73EJT21:109 |
这些简的时间是从元康元年(前65)到东汉建武四年(28),前后近百年;地点以甲渠候官为多,亦包含少量肩水候官(地湾)及其下属的金关,以上均属于张掖郡,还有敦煌郡玉门都尉与属于民政系统的悬泉置。涉及的簿籍类别可以说五花八门,涵盖了李天虹区分的十类中的七类。
概言之,无论是簿是籍,不论具体涉及的对象是人、錢还是物,编制是按月或四时,书写格式高度一致,说明是遵照一定之规进行的。学者曾经指出西北边塞的文书书写存在“范本”——式,并从殘简中找到一些[37],遗憾的是虽然发现一些簿书的范本,却尚未发现与此类文书有关的,不过,我们相信一定存在过此类的范本,且通行很久,不然无法解释近百年間不同地点出土此类格式相同的文书。
以上诸简背面均有书吏的署名[38],按照上引学者的看法,均应位于文书的末尾。而简文的内容均属于不同簿籍的呈文。再参照前文引述的带有编绳的簿籍文书,可以肯定,这些呈文简应置于簿籍的最后。
此外,西北出土的汉简中还有很多格式相同的简,均属于与簿籍相联的呈文,只是简的左下角或背面没有相关书吏的署名。永田英正与李天虹先后搜集了居延汉简中的此类简。茲将此后新公布的汉简以及两人没有论及的敦煌汉简中的同类简,列于次[39]:
|
类别 |
簿籍名称 |
简文 |
出处 |
|
日常工作 |
卒不任候望名籍 |
始建國三年三月癸亥朔壬戌第十隧長育敢言之謹移卒不任候望名籍一編敢言之 |
额济纳汉简2000ES9SF3:2A |
|
兵物 |
守御器簿 |
守御器簿一編敢言之 |
敦煌汉简释文: 752: 釋MC.665 |
|
兵物吏卒 |
兵守御器戍卒名籍 |
元始三年四月丙午闐胡燧長鳳敢言之謹移兵守御器戍卒名籍一編敢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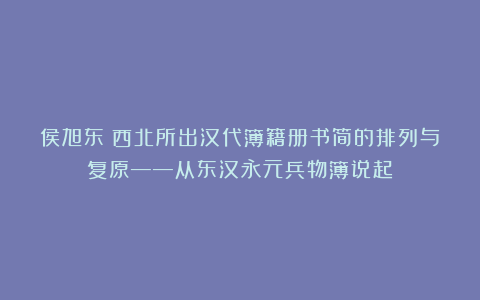 |
敦煌汉简释文: 920: 釋MC.793 |
|
兵物吏卒 |
兵守御器吏卒名籍 |
謹移兵守御器吏卒名籍一編敢 |
敦煌汉简释文: 921: 釋MC.794 |
|
吏卒 |
候官隧和吏妻子私从者三月名籍 |
五鳳三年三月丁丑朔癸卯士吏帶敢言之候官隧和吏妻子私從者三月稟名籍一編敢言之 |
敦煌汉简释文: 1161: 釋MC.998 |
|
谷物 |
耫糒薄 |
元康三年正月乙丑朔庚戍效穀丞 敢言之 謁耫糒薄一編敢言之 |
敦煌汉简释文: 1505: 釋HC.1292 |
|
谷物 |
谷出入簿 |
元鳳五年十二月乙巳朔癸亥通道廄佐敢言之謹移穀出入簿一編敢言之 |
肩水金关73EJT10:200 |
|
谷物 |
谷出入簿 |
元鳳五年十二月乙巳朔癸卯□□□□□乘敢言 謹移穀出入簿一編敢言之 A 財□賦…… B |
73EJT10:203 |
|
谷物 |
谷出入簿 |
元鳳六年正月乙亥朔癸卯通道廄佐敢言之謹移穀出入簿一編敢言之 |
73EJT10:209 |
|
吏卒 |
吏卒廩名籍 |
元始元年八月丙戌朔壬子西部候史武敢言之謹移吏卒廩名籍一編敢言之 |
73EJT21:108 |
|
功劳 |
功劳 |
庚申朔庚申肩水士吏漢成敢言之謹移元康三年功勞一編謁上
|
73EJT21:127 |
|
不明 |
□□簿 |
神爵二年正月丁未朔癸酉執適隧長拓敢言之謹移□□簿一編敢言之 |
73EJT22:25 |
|
牛马车 |
驿马名籍 |
居攝三年正月己卯朔 驛馬名籍一編敢言之 |
73EJT23:350 |
|
不明 |
建昭五年三月丙午朔甲寅西部守候長 一編敢言之 |
73EJT23:352 |
|
|
亡人火出入界相付日時 |
元始四年五月庚午朔乙未東部候長放敢言之謹移亡人火出入界相付日時一編敢言之 A 牟放印 令史發 五月乙未以來 君 前 B |
73EJT23:855 |
|
|
俸禄 |
受奉名籍 |
元始三年四月丙午朔□丑□□□□裦敢言之謹移受奉名籍一編敢言之 |
73EJT24:31A(背面习字) |
|
吏卒 |
廩城官名籍 |
永始四年七月壬寅朔 廩城官名籍一編敢 |
73EJT24:133 |
|
吏卒 |
卒名籍 |
…… 卒名籍一編敢言之 A 百八人丙午 甘露 B |
73EJT24:159 |
|
牛马车 |
传馬出入簿 |
永光五年八月壬申朔辛卯縣泉廄啬夫遂成敢言之,謹移傳馬出入簿一編敢言之 |
以下敦煌悬泉ⅡT014②:548 |
|
牛马車 |
传馬出入簿 |
建昭元年十月丙寅 傳馬出入簿一編敢 |
ⅤT1511②:1 |
|
牛马車 |
传馬出入簿 |
建昭五年十一月壬申朔 縣泉廄啬夫霸敢言之謹移傳馬出入簿一編敢言之 |
ⅤT1611③:305[40] |
这些简的行文格式与前引带有书吏署名的简完全一致,之所以不见书吏的署名,有些是因为残断,有些则是因为发文者是隧长或候史,一隧之中,能完成文书工作的应该只有隧长一人,其手下只有戍卒二至四人,大多为三人[41],再无书吏。担任隧长需要“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42],其所上的文书原则上均应为隧长自己起草书写。候史平日亦负责文书工作,其发文的文书无须再署名。士吏或许也是如此。其他简为何没有署名,还需要研究。个别简,如73EJT21:127、73EJT23:855为何会在金关出土,颇费思量。两简字迹均较工整,不似底本,后一简的背面更是带有别笔书写的收文记录,且云“令史发君前”,难道是候外出或行塞时,关啬夫代行候事时处理的文书?
因为这些简与上引带有书吏署名的简行文格式一致,应该是按照同样的“式”来起草抄写,它们也应该放在簿籍最后,而不是前面。
此外,簿籍类册书的编缀与收卷方式,据现存带有编绳的册书,均是从首简向末简穿系,绳结置于册书的末尾,并有多余的编绳,可以连缀更多的简。墓葬出土的一些带有标题的律令类简亦是置于末简的背面,如睡虎地秦简中的“封诊式”、张家山汉简中的“二年律令”与“奏谳书”,这些均说明其收卷是从首简有文字一面开始向左侧卷入,使得册书的末简出现在整卷册书的最上边[43],将呈文放在簿籍册书的最末,不必展开全册就可知晓其内容,正便于接受文书的一方迅速了解文书的内容与性质。
若此说无误,对于“始建国天凤亖年当食者案”(EPT68:194-207)册书诸简的排列,需要重新考虑。因为未能考虑簿籍册书简的排列方式,或在复原或引用这两个册书时均将本应置于最后的简(EPT68:194)放在了首位,颠倒了诸简的次序,不免造成讹误。此册书原先的排列次序应如下:
以带有“·”的标题简置于册书之首,应该是当时通行的做法,即便没有呈文也是如此。金关出土的编绳尚存的册书“勞邊使者過界中費”(73EJT21:2-10)就是一例。“居延都尉府奉例”冊的排列亦应是以文书结尾。
至于是否汉代所有簿籍类册书均是如此排列?目前还没有看到反例,但已知总是有限的,未来不能排除出土将呈文列于册书之首的简牍。
二、簿籍简册排列的渊源与影响
西汉中后期见于西北边地的簿籍文书的排列方式,并非西汉一朝自创的制度,而是袭自秦代。湖南龙山县里耶镇出土的秦代洞庭郡迁陵县保存的行政文书简牍中就不难找到类似的先例。茲引数例如下:
此木牍是由三枚碎牍缀合而成。经检视图版,缀合无误。三牍缀合后长度为46.3厘米,合秦代两尺。此文书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五月由库(守或啬夫?[45])武向县呈报的“作徒簿”,这种簿恐怕是一种按月呈报的簿书,有固定的称呼:作徒簿,亦很常见,简8-1559 有“上五月作徒薄”之说,可能是月度性的簿书。簿书在列举了作徒的来源后,便按类分三行列出(疏书)十五人当时从事的工作,背面则是呈文。之所以断定呈文是在背面,一是里耶的行政文书末尾通常会有书手的署名:“×手”,这件木牍的“橫手”便写在呈文的下面,此面应是文书结尾处。二是此面还有递送与拆启文书的记录,这通常亦是出现在文书的末尾,因此,笔者认为校释者缀合后确认的木牍正背面的顺序是正确的[46]。
此例的排列便是时间、负责人与标题“作徒簿”在前,随后是簿书具体内容,最后是呈文。类似的文书还有:
又如:
又如:
还有:
此外,还有一木牍,性质相同,不过,残存的记录的分为上下五栏,内容颇多,为节省篇幅,仅引存有文字的第二栏与最后一栏,以及背面文字:
以上根据呈文的内容、“×手”的位置,以及收文记录(××以來, ×發)的位置,可以肯定这几枚木牍亦是簿书在前,呈文在后。
不过,里耶秦简中也有一些将呈文写在前面,簿书放在后面的文书,如:
此木牍由两枚牍缀合而成,检图版,无误。此文书说“疏书廿八年以尽卅三年见戶数牘北”,校释者认为“北”通“背”,表示将六年的现户数抄录在木牍背面。若此,此文书则是呈文在前,具体内容在后,与上面的簿书不同。又如:
类似的文书还有简8-1517、8-1566。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将具体内容写在木牍背后,则要在呈文中明确说明,表明此做法异乎寻常,这亦反证簿书在前,呈文在后乃是常态。
即便出土的里耶秦简中迁陵县保存的文书,或是收到的来文的抄件,或发文的底本,转录或抄写时一般不会改动文书正本的格式,也许会改变使用的简牍形制。如学者研究所揭示的,至少里耶秦简中,帐簿与呈文是书写在木牍这类被称为“单独简”之上来递送的[50],若此,帐簿居前,呈文在后应是此类文书构成的常态。
尽管里耶与张掖居延、敦煌相距数千里,时间上也前后相隔150年左右,在簿书与劾的排列上却呈现相当的一致性,当然不是说两地之间存在什么相互影响,两地均是在秦、汉律令与式的规范下进行文书行政。这种一致性是源于汉代文书制度相当程度上继承了秦制,所以才会穿越了时空,在百余年后的异地他乡,见到相似的文书排列方式。
实际上,不仅是在汉代,甚至到了早已是纸制文书时代的唐代,为编制计帐与户籍,由編户所上的手实之类的文书还是先逐项罗列各户的人口、年龄与各段土地的四至细目,最后为各户的呈上牒文,如吐鲁番出土的武周载初元年(690年)一月西州高昌县宁和才等户手实(64TMD35:59-75)[51]。这种书式甚至影响到日本,十世纪完成的《延喜式》中的大帐书式也沿用了这种形式,逐项细目在前,最后为呈文“以前某年大帳依例勘造,具状如前,仍錄事状,差官位姓名申上,謹解”[52],尽管此时呈文的用语与汉代已颇为不同;《延喜式》“主税寮下”所录“正税帐”、“租帐”、“青苗帐”的构成亦均是如此[53]。
此外,这种簿书的排列不仅通行于世间,亦影响到阴间,汉代以后的衣物疏亦模仿官府的簿书+呈文的形式。较早的一例见于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墓出土的西汉景帝前元四年(前153)木牍“衣物疏”,其书写次序便是如此。释文如下:
此件木牍应是始于“竹笥二”,排列顺序是第一栏由右向左橫读,然后自上而下依次第二、三、四栏,“黑杯五”为正面结尾,转入背面,最后是文书[55]。此种书写方式在战国时期楚地墓葬的遣册中尚未发现[56],乃是帝国建立后模仿官府行政文书而形成的。墓主人张偃身为西乡的佐或啬夫,平日要编制相当多的簿籍,并向县廷移送副本,死后的随葬品中就有不少此类簿籍的抄件,他自己及其家人对此类文书的格式应该不陌生,在时人的死后世界观中,地下世界乃是人间的翻版,模仿人间的官文书来安顿死者亦不意外。
这种排列方式甚至到十六国北朝乃至唐初的墓葬中的“随葬衣物疏”还是如此。目前所见的很多都是先列随葬品清单,后附移文[57]。
三、结论
本文借助编绳犹存的简册,如居延出土的东汉永元兵物簿与敦煌悬泉出土的传车亶轝簿,以及悬泉发现的两件不定期簿书,指出无论是基于定期簿书还是不定期簿书形成的定期文书或不定期文书,在具体内容的排列上,均是内容在前,呈文在最后。通过对呈文书写特点的归纳,推断一般簿籍类册书的排列均是如此。因此,学界通常对“始建国天凤亖年当食者案”简册的复原是有问题的,应该将呈文置于简册的最后。
这种排列结构并非西汉首创,而是承袭自秦代。里耶秦简中就已出现如此排列的木牍簿籍,而这一文书书写的结构安排,甚至唐代的文书中还保留,并东传影响到日本。同时,不只是行用于世间的官府,从西汉到唐代,针对地下世界的“衣物疏”中很多也仿自此种簿籍的书写格式。
本文修改过程中先后得到邢义田、凌文超先生的赐教,2013年8月22日到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查看简牍实物,得到张德芳、韩华先生的多方帮助,11月3日曾就此问题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做过报告,得到陈伟、刘国胜与刘安志先生的指教,学棣王振华复纠谬正误,谨此一并致谢。
注释
[1]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秦汉六朝国家日常统治机制研究”(11YJA770015)的前期成果。
[2] 森鹿三《居延漢简の集成—とくに第二亭食簿について—》,《東方学報》29(1959.3),第139-154页;《居延出土の卒家属廩名簿について》,《立命館文学》80(橋本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学論叢)(1960.6),第342-353页,陈公柔、徐苹芳《大湾出土的西汉田卒簿籍》,《考古》1963年第3期,第156-161页;鲁惟一(Michael Loewe)《汉代行政记录》上册,于振波、车今花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28页以及下册;陈公柔、徐苹芳《瓦因托尼出土廪食简的整理与研究》,《文史》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5-60页;永田英正《居延汉简研究》第一部“居延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张学锋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323页;大庭脩《汉简研究》第一篇“册书研究”第四章“地湾出土的骑士简册”,徐世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0-90页;谢桂华《新旧居延汉简册书复原举隅》,《秦汉史论丛》第5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年,第264-277页;《新旧居延汉简册书复原举隅(续)》,《简帛研究》第一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年,第145-167页;《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和册书复原》,《简帛研究》第二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238-264页;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此外,薛英群、李均明亦对籍簿做过全面的概括,分见《居延汉简通论》,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47-464页;《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47-414页。
[3] 如大庭脩《汉简研究》第一篇“册书研究”序章第四、五节专门讨论册书复原的原则,第10-20页;张俊民《居延汉简册书复原研究缘起》,《简牍学研究》第4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5-79页;徐苹芳《汉简的发现与研究》,原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6期,后收入所著《中国历史考古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03-312页;《再谈出土简帛文书的整理和出版》,原刊《古籍整理出版丛谈》,后收入上书,第410-416页;沈刚《居延汉简册书复原方法述论》,张德芳主编《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3-174页。
[4] 胡平生《新出汉简户口簿籍研究》,收入所著《胡平生简牍文物论稿》,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343-348页。
[5] 如李均明说“簿籍等专用文种不具备通行性,当它们需要上送或下传时,须附着于通行文种,作为通行文种的附件运行”,见《古代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中的“簿籍类”,第247-414页。如所录“橐他莫当燧守御器簿”就略去了简EJT37:1537,第305-306页。另外,作者区分出一种有关钱粮及其他物质的调拨的“调书”,见第404页。东汉永元兵物簿则认为属于“会计报告”,并指出“账簿与呈文的结合构成完整的会计报告。……从广义而言,定期上报之各种账簿(含呈文),皆可称为会计报告。而狭义的会计报告当经过累计与综合归纳”,第408页。其实,墓葬中的确出土过不少木牍,上面的名称确有“×簿”,如尹湾汉墓出土的“集簿”、天长汉墓出土的“户口簿”、“算簿”、荆州松柏汉墓出土的更丰富,有“户口簿”、“免老簿”、“新傅簿”、“罢癃簿”、“归义簿”等。
[6] 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5、159-160页。
[7] 如永田英正《居延汉简研究》上册,第42-323页,特别是第266-267、267-275页;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冨谷至《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刘恒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8页。
[8] 偶有学者论及,如角谷常子在分析居延旧简10.34,指出,参照永元兵物簿,应置于册书的最后,见《木简背书考略》,收入《简帛研究译丛》第1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217页。
[9] 甘肃居延考古队所做的照片说明将“守御器簿”中的简1537置于册书之首,见《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第24-25页。初师宾后来对此簿的复原则改为置于册书末尾,见所著《汉边塞守御器备考略》,《汉简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4-146、147-149页;永田英正的看法则颇显矛盾。时而认为是置于册书之首,时而又认为在尾部,见《居延汉简研究》上册,第267页及第266页注释①。他还指出簿籍是附上簿籍递送文书后装入口袋,然后再系上封检以后发送的,第275页。按照此说,递送文书恐怕是置于簿籍的末尾吧。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第109-110页;冨谷至《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第48页。
不过,籾山明还是将此简置于册书之首,见所著《漢帝国と辺境社会:長城の風景》,东京:中央公论社:1999年,第149-150页。
[10] 如鵜飼昌男《「始建国天凤亖年當食者案」冊書の考察:漢代の「案」の語義を中心に》,《东洋史研究》56.3(1997),第38-39页;中译本见《简帛研究2001》,第696页;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第81页;冨谷至《文書行政の漢帝国:木簡竹簡の時代》,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年,第369-373页;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第159、400页;及李均明《古代简牍》,第167页、《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第416页。胡之主编《中国简牍书法系列·内蒙古居延汉简(二)》,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20页的照片亦是如此排列。
[11] 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前言,第viii页。
[12] 如徐世虹《汉劾制管窥》,《简帛研究》第2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312-323页;鷹取祐司《居延漢簡劾狀關係冊書の復原》,《史林》79.5(1996),第94-98页;佐原康夫《居延漢簡に見える官吏の處罰》,《东洋史研究》56.3(1997),第441-455页;高恒《汉简牍中所见举、劾、案验文书辑释》,收入所著《秦汉简牍中法制文书輯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02-312页;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第70-79页;《居延汉简诉讼文书两种》,1990年初刊,后收入所著《简牍法制论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0-88页;宫宅潔《中国古代刑制史の研究》第六章“’劾’をめぐって—中国古代訴訟制度の展開”,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11年,第289-295页。
[13] 参邢义田《汉代简牍公文书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签署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2本4分(2011),第644页注82。
[14] 参邢义田《汉代简牍公文书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签署问题》,第643-647页。
[15] “定期文书”与“不定期文书”的概念是永田英正提出的,不过,后来他又有所订正,称之为“簿籍类”与“文书类”,见《居延汉简研究》上册,第48-49页。根据悬泉出土的简牍,的确存在按照上级的命令,不定期编制的簿书,加上呈文,构成不定期的文书(下详),我想,永田原先提出的分类概念更具有涵盖性。
[16] 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下册中的MD18、MD19,第275-277、278-292页;永田英正《居延汉简研究》上册,Ⅲ器物,第54、88-97、100-103、162、172-178、200、205、213、225-233、247-248页;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第90-120页。
[17] 核图版,“車”字脱,各家释文仅胡之主编《中国简牍书法系列·甘肃敦煌汉简(一)》(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1页)注意到。
[18]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例10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5-86页。图版见该书前彩色插页。又见《文物》2000年第5期,第42页图七;马建华主编《河西简牍》,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年,第35页;胡之主编《甘肃敦煌汉简(一)》,第1页;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书前彩色图版,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图版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六图稍有不同。主要是第7枚简上半部分“亶轝一”摆放的位置不同。
[19] 参邢义田《汉代简牍公文书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签署问题》,第627-630页。
[20] 参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第33-36页。
[21]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引简90,第33-34页。
[22] 参李均明《汉简“会计”考》(上),《出土文献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27-128页;《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第402-403页。
[23]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引简106、109,第35页。
[24]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86页注释的按语。
[25] 类似的例子见简Ⅱ90DXT0114③:461:“五鳳四年九月己巳朔戊子,淵泉丞賀敢言之:大司農卒史張卿所乘傳車一乘,皁〔留〕黄蓋杆衣各一,皁繒並塗一具,駕一被具,張卿乘,西付冥安,皆完,今張卿還至”,见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例103,第87页。
[26]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第263-264页,照片为笔者2013年8月22日在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库房所拍摄。
[27] 据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引此册书,标题做“建昭三年”,当是笔误,第264页。左侧图版见胡之主编《甘肃敦煌汉简(一)》,第17-19页,右侧为笔者2013年8月22日在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库房所拍摄。
[28] 参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第70页;李均明指出“转发行下文或转呈上行文通常不署年号及年序”,见《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第130页,又见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第146-147页。
[29]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例92,第76页。
[30] 同上,例95,第78页。
[31] 陈梦家《汉简所见太守、都尉二府属吏》三“汉简文书签署”,收入《汉简缀述》,第104-109页;大庭脩《汉简研究》,第205-221页、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第71-73页;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第160-163页;冨谷至《文書行政の漢帝国:木简竹简の時代》,第205-214页;邢义田《汉代简牍公文书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签署问题》,第604-612页;《汉至三国公文书中的签署》,《文史》2012年第2辑(总100辑),第163-198页。
[32] 见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第160页;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第134页。汪桂海的看法基本相同,见《汉代官文书制度》,第73页。例外的是编绳尚存的57.1,由三枚简组成,“令史充”三字写在首简的背面,而非末简。或许因为是留底副本的缘故。
[33] 参侯旭东《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简牍学研究》第5辑,待刊。
[34] 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第73页。
[35] 引自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简2,第45页。
[36] 引自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简30,第25页。
[37] 邢义田《从简牍看汉代的行政文书范本——“式”》,收入所著《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50-472页;高恒《汉简牍中所见的“式”》,收入所著《秦汉简牍中法制文书辑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16-238页;张俊民《悬泉汉简所见文书格式简》,《简帛研究200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0-141页。还有一些簿书的习字简,如敦煌马圈湾出土的简187。
[38] 至于简上署名的书吏在文书形成中的作用,亦各有不同。有些秩级较高的如“掾”,应该是负责文书起草,而“佐”则是具体负责抄写。署名的规则,还待进一步的研究。文书的性质,有些是存档的底本,有些是副本,为免文繁,茲不一一详论。
[39] 文字过残者,如仅剩“一編敢言之”之类的简,未收入。
[40] 以上三例据张俊民《对汉代悬泉置马匹数量与来源的检讨》,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长春:2007年,第9页。
[41] 李均明《汉代甲渠候官规模考(下)》,《文史》35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83页。
[42] 具体见居延汉简13.7、37.57、89.24、179.4以及新简EPT50:10、EPT52:36和EPT59:104。亦有个别例外,如甲渠候官第十二隧长张宣(129.22+190.30),分析见邢义田《汉代边塞吏卒的军中教育》,收入《治国安邦》,第585-594页。关于“隧长”是否一定识文断字并能起草文书,学界尚有分歧,赞成者见高村武幸《汉代地方少吏的任用与文字知识》,傅江译,收入《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年刊(2006年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9-102页;反对者如冨谷至《文书行政の漢帝国》,第112-116页。
此外,即便某隧的隧长文字能力有限,难以处理文书,亦可得到“助吏”的帮助,助吏常常是其他隧的隧长,详见刘增贵《〈居延汉简补编〉的一些问题》“(三)助吏—兼论其他以“助”为名的小吏”,收入简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补编》附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98年,第37-41页。此点承邢义田先生提示,谨谢。
有学者认为边塞中“部”为制作文书的最低一级机构,而“隧”并不制作文书,如冨谷至《文書行政の漢帝国:木簡竹簡の時代》,第117-121页。从上表所引数例以及其他简看,情况并非如此。之所以看到“隧”编制的文书不多,应与发掘的遗址多为候官遗址以及汉代文书逐级上报的制度有关,候官遗址中残存的多为其直接下属的“部”的来文,如果发掘更多的汉代的某个“部”所在的隧或一般的隧,应会发现更多隧制作的文书。
[43] 具体讨论见冨谷至《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第46-48页。此点承邢义田先生提示,谨谢。当然亦存在从册书尾部起卷的情况,如《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肆》中“揭剥图21”所描绘的册书,如此收卷,册书的标题就收在了最外面,标题亦体现了文书的内容,实际亦无妨收到册书者了解其内容。此点承凌文超兄提示,谨谢。
[44]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2-273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43、175、194页。简號排列次序据实际位置有调整。
[45] 《里耶秦简》(壹)中同是卅一年三月的出禀记录,有的作“倉武”,见8-760,有的则作“倉守武”,见简8-606、8-763。
[46] 角谷常子指出这乃是里耶秦简记录文书的通例。她还仔细比对了此类文书正、背面的文字,指出两面的文字字迹一致,并认为可能是接受文书的迁陵县重新抄录所致,见《里耶秦简における単独简について》,《奈良史学》30(2013年1月),第111、115页;关于迁陵县保存的阳陵县送交文书为迁陵县制作的存档抄件的看法,见邢义田《湖南龙山里耶J1(8)157和J1(9)1-12号秦牍的文书构成、笔迹和原档存放形式》,收入所著《治国安邦》,第494页。
[47] 以上释文均据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417、111、421、196-197、84页。
[48] 据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166页。
[49] 据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203页,第三栏“廿廿年上之”,校释者指出“此五字字体较大,或与正文无关”,当是。释文的正、背面则据内容做了调换。
[50] 见角谷常子《里耶秦简における単独简について》,第111-112页。
[51]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三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98-516页,相关分析见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译本:中华书局,2007年,第90-93页。
[52] 黑板勝美编《延喜式》卷二五“主计寮下”,新订增补国史大系26,东京:吉川弘文馆,1965年,第642页。
[53] 黑板勝美编《延喜式》卷二七“主税寮下”,第671-694页,特别是第685、690、694页。
[54] 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89-91页。
[55] 见胡平生、李天虹《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33页。
[56] 参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18-121、287-290、338-339、382-384、469-471页。
[57] 见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附录二《吐鲁番晋——唐古墓出土随葬衣物疏》,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697-721页。亦有少量衣物疏只有随葬品清单,如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年)缺名随葬衣物疏(59TAM305:8),《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一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3页;或在移文中列举随葬品清单,如高昌建昌四年(558年)张孝章随葬衣物疏(72TAM169:32),《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三册,第207页。
原载于《史学集刊》2014年01期。感谢侯旭东先生授权发布。引用请查阅原文。
“中国中古的河西走廊”专辑组稿:贾小军 戴卫红
编辑:韩玄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