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被车裂了,但他制定的那套法治机器没被拆。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先把那场处刑交代清楚。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嬴驷继位,史称秦惠文王。旧贵族趁机反扑,把商鞅扣上谋反的帽子,结果商鞅被车裂,家人也遭株连,血淋淋地结束了他的生命。可别以为死人了事,惠文王把私人恩怨放到一边,没有把商鞅的法令全盘否定,反而继续沿用。政治里有件事很常见:恨一个人不代表要否定他留下来的制度和规则。国家的需要,有时候比个人情感更重。
回过头看商鞅的来路。大约三十多年以前,他从魏国到秦,带来李悝的《法经》这套主张,得到秦孝公重用。那会儿的秦在中原还算外人:领土有丢失、内部被旧贵族把持,国家既怕被轻视又怕内部瓦解。孝公下了求贤令,商鞅应召而来,动起了翻天覆地的手脚。公元前356年,他先推行第一波变法:什伍连坐、以军功分田、禁止私人报复、强调重农抑商;到前350年,又废井田、实行郡县制,还统一度量衡。法律、户籍、军功、土地这几环同时动了,像一次性把国家机器的齿轮重新咬合。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效果很快露出来。十年左右,社会秩序好转,盗贼减少,普通百姓生活稳定些,军队对外作战的意愿上来了,内耗少了。公元前340年,商鞅亲率秦军夺回河西失地,这类胜利都记在正史里。不过变法也踩到不少人的铁脚板。比如“太子犯法,师代受刑”的原则让太子的老师、公子虔都遭了刑——被割鼻留作羞辱。这事记在心里,未来的惠文王也不会忘,政治往往就是这样,个人旧怨和国家利益经常发生冲突。
把视角再拉宽一点,才看得清为什么法家能当道。西周之后,传统礼制慢慢崩松,原本依赖宗法体系的“士”开始另找出路,有的开私塾教书,有的四处游说当说客。这样一来,社会流动性增加,思想市场活跃,私学兴起,意见多了,竞争也就多了。正是在这种语境下,纵横家——专门干外交说服活儿的那类人——才有了用武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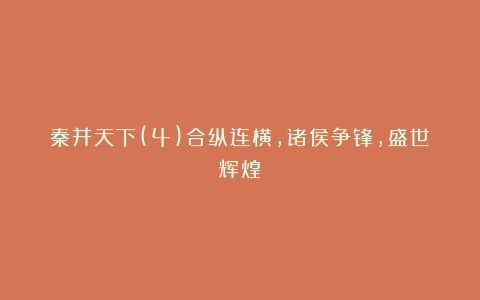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苏秦和张仪就是那一批人。苏秦早年漂泊,靠合纵之策把六国拉在一起对付秦,短时间里让秦也不好随便动手。合纵的短处也明显:利益各异、地理分散、协调难,顶多是一张临时的网。张仪出现后走的是另一套:连横。把列国一个个拉到秦的利益盘里,拆散合纵的脊梁。俩人同师出于鬼谷子,但命运迥异。张仪会算人心,他对楚怀王下的那一盘棋很经典:许诺给楚地、送美女、结盟甜头,靠利益诱惑把楚拉到秦一边。等到事成,张仪还上演一出“假摔假伤”的戏,三个月不朝,回头一句话把好处缩小化,让对手恼羞成怒,结果楚王出兵吃亏,最后又得向秦妥协。这套把利害算清的手段,在战国的外交里行得通。
在更大的历史脉络里,这一切并不是偶然。春秋向战国过渡时,君权的绝对性在削弱,伦理话语不再自然决定国事。过去靠“孝”和礼仪维系的那套,面对战争和土地、农业、税收这些现实问题显得力不从心。于是,讲规则、看得见奖惩的法家理路变得有市场。商鞅提出的是一种可操作的、偏向理性的国家治理方案,能提高动员力和战斗力。问题是,太过强调规则也会死板、忽视人情。秦在统一六国后用了极端有效的集中与法令,短时间内完成了大一统,但这套“刚性治理”也埋下了摇摇欲坠的隐患,秦朝最终只撑了十几年。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说到具体细节,别忘了那件小事儿——徙木立信。公元前359年,秦都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官府下告示,谁能把它搬到北门就赏十金。都有人看热闹,但没人动。赏金涨到五十金时,一个年轻小伙儿上前把木头扛过去,拿了赏钱。围观的人一下子信了国家说话。就是这么一件看似小儿科的事,实际是把国家信用往实处一敲:国家说了算,有规矩有奖罚。这一招对当时老百姓心理的震撼,等于把一整套法律和行政威信扎了根。
从一根木头到完整法令体系,从几条新法到打回来的一块地,历史的脉络一直连着。那些看起来冷冰冰的条文背后,其实是具体的人、利益和算计,是一次次胜败和一桩桩日常的实践。事情就像齿轮咬合,个体受伤了,制度还在转;人死了,规则可能活下来,国家也就会跟着走样或走正路。最后那根被扛起来的木头,在当时的意义就是:从今往后,国家要按规矩来办事。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