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成建制地从大兴路小学转到了大董家巷小学。
大董家巷
在大董家巷小学的时候,班上多了三个同学,其中一对双胞胎姐弟,弟弟叫恒子。姐姐叫什么忘了,就叫恒姐吧,整天很少有笑容,不过她那一举一动,倒像个姐姐。姐弟俩衣服破旧,补丁摞补丁;尤其是恒子,一双又破又脏的布鞋,除了进校门扯上脚跟,通常是趿着,有时疯逗打闹把鞋子弄掉了,就抬起一只腿蹦几步,把那鞋捞在脚上。恒姐衣服虽破旧,不过给人的感觉很整洁,一根独辫总是梳得光溜溜的,像前清的落魄秀才。
恒子不读书。上课经常睡觉。即使不睡,眼睛也不看讲台,更不会看书,但他却很忙。比如,从作业本撕一页纸,在黑板槽刮一团粉笔灰,包得平平展展的,上课的时候就用根针在上面戳一个个小眼。下了课就把那包纸放在手掌心,“友好”地拍一下人家的后背,于是在人家的后背就印上了“王八”的字样,或者乌龟的图案。
我们的班主任特别喜好揪耳朵,恒子自然是被老师逮去揪耳朵的常客。恒姐由于“管教不严”也被叫去挨呵斥。她也奈恒子无何,充其量皱皱眉头瞪一眼,或者朝弟弟身上一巴掌,那巴掌绝对不重,因为连声音都没有。
不过,他们俩也有风光的时候。那是上手工劳动课。一张印着花花绿绿图案的硬纸,按要求剪成一片片再粘好,拉动下面的纸条机关,武松就举拳打虎,或者白雪公主舞起来。
发的浆糊要么粘不牢要么难干透,但姐弟俩带来的浆糊又白又香干得又快,所以大家都用他们的浆糊,他们也不小气,任大家用。有同学说,他们家是糊洋火盒子的,所以浆糊好。
那时候下午放学很早,我们通常要在学校玩很久。很奇怪姐弟俩一放学就不见了人影。说到这里,还得提及另一个新同学:
这哥们长得很肥,一对缝眼老眯着。姓马名翀。就连老师也不认识“翀”字,我们认为能取这个名字的人一定有学问,马翀洋洋得意地点头默许了。但是,我们一直管他叫“马震”,因为:
那年头大概吃了各种各样的杂粮缘故,课堂上经常有些因生理现象产生的杂音,本习以为常,但这家伙却会随时震一个,所以诨名“马震”,就连老师也喜欢拿他开心:“震一个。”他缝眼一瞪,腮帮子一鼓,卟 —— 音效就出来了。于是,老师们笑得人仰马翻。
有老师的欣赏在先,这小子胆子也逐渐大了,时常在课堂上创作一个,老师喜欢他,装着没有听见。不过,他也有过冤案,那天上课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抑扬顿挫的一长声,同学们笑翻了天;老师可能心情不好,把教鞭一拍,只听马震申辩:“这个 —— 不是我的啊。”老师吼叫:“不是你是鬼!滚到外头站着!”
其实,我们都知道马震委屈,因为他的爆发力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艺术境界。
马震读书很认真,也喜欢玩,只是玩法与恒子不一样。他喜欢粘知了,两根细竹竿用松紧带捆绑,成了伸缩竿,在竹竿的顶端抹上洋㞎㞎和松香,朝那知了轻轻一点,一粘一个准。后来才知道,他粘的知了是用来卖钱的。进江汉公园要门票,知了也少,无法量产,他不知怎么发现了一处风水宝地,即现在的月湖桥一带。当时那里是土堤,沿堤长满了大树,满树的知了叫个此起彼伏。
落成不久的江汉桥
他带我去粘过几次。从四官殿坐7路公汽沿江、沿河大道后,右拐顺着江汉桥引桥旁马路,再左拐上中山大道到硚口。记得在江汉桥引桥边的长江食品厂附近,两旁分别有一个半圆形花坛,人们叫作“磨盘”。那里有一站“汉水桥”。
这天放学,就去硚口粘知了。车上马震突然要撒尿,肥脸憋得像猪头。只得在汉水桥站下车去马路对面的公厕,下车的时候他与售票员纠缠了一阵,因为到硚口买的8分钱车票,而到汉水桥只要5分,马震逼着售票员退了3分钱,也不怕憋得难受。正要过马路,他一声惊乍:“恒姐!”
果然,恒姐身上斜挎一个已经不见绿色的军用水壶,弓着身子在推一辆板车。我们想看个究竟,就退回到马路对面远远跟随,到了桥中央,板车停下,才发现是恒子用绳子拉这辆板车。车老板给了恒子一张钞票就翘起板车扶手,一跳一颠地下桥了。恒子把钞票给了恒姐(马震断定:一角钱),手上挽一根麻绳,麻绳上套着一根铁钩;恒姐递过水壶,恒子摇摇头,顺手将绳钩搭在肩上,模样老道成熟,用现在的话说,有点酷。然后姐弟俩一后一前地回头往桥下走去。
我和马震没有惊扰他们,干脆笔直走向汉阳。到汉阳引桥,马震才惊叫着蹿下土坡,对着一堵围墙轻松了。一路上马震反复说“划不来”,起初我以为他是说恒子姐弟为挣钱耽搁了学习划不来,马震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你晓得个屁!”
马震告诉我,他爸爸是炸爆米花的,有几多人撑饱了有米去炸爆米花?下雨下雪还不能炸。妈妈白天上班,晚上帮人织毛衣,五六个晚上才能织一件,一件两块来钱;姐姐用钩子针给棉线手套的指尖收针,晚上钩着钩着打瞌睡,就扎了手。“你猜钩一打多少钱?”马震问,我怕他又骂我“晓得个屁”便摇摇头。“12个,4分钱!”马震恨恨地说。
我去过住在二圣巷马震的家,他爸爸虽然炸爆米花,但像干部的样子。“你爸爸不是有学问吗?”“有学问管屁用……”马震说,“我也想赚钱,但是恒子他们划不来,等于拉一趟5分钱。”
我说回头再坐车去硚口,马震担心被恒姐看见了让他们难为情,干脆过长江大桥坐轮渡回去。在黄鹤楼影院处下引桥,马震眯着眼,在一个租小人书的地摊旁站着看了许久。我好不容易把他拉走,边走边告诉他,我的小人书很多,你想看我借你。
我真佩服马震的聪明,他已经看出门道了:“刚才我数了的,有七个人在看,几多钱?”“七分钱。”“笨猪,厚的两分!比恒子拉板车划得来吧?哎 — 刚才你说你有好多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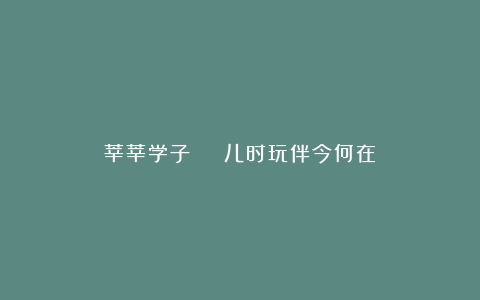
我的确有好多小人书,像《水浒》《杨家将》还是成套的。妈妈有一个皮箱,大小与现在装手提电脑的包差不多,但厚多了,也硬多了,就是给我装小人书的。“敢不敢拿出来?我们摆摊租书。”够刺激的,我便大义凛然地答应了。
第二天就把皮箱提到了学校,马震把恒子姐弟俩叫到一起,商量了一会,姐弟俩很高兴。现在想起来,马震果真是做总裁的料子,他吩咐恒子“反正你是不读书的,撕一张作业纸,裁成小纸片,上面一律写2分,免得到时候浪费时间”。恒子想先拿一本上课看,被马震踢了一脚:“老师发现了,通通没收,不误了事?”惹得恒姐也拍了恒子一巴掌。
江汉剧场电影票。朱汉昌收藏
怕被同学们发现,下午放学,我们过江去武昌。在渡轮上打开书箱,凡是有点厚的书都贴上“2分”的标签。上岸后在江汉电影院门口铺下几张报纸,摆上小人书,开始做生意了。那时候看电影的人比现在多,又没有手表掌握时间,便早早来到电影院门口等候散场,无聊了就蹲在地上看小人书打发时间。
书摊一摆开,头两名顾客竟然是姐弟俩,他们拿起书一本接一本,头都没有抬。我负责照看摊子,马震负责收钱。这小子够“奸”的,突然发明了“标价2分是看一套,如果看一本3分”的新规定,然后装作一副做赔本买卖的样子,搭一本《少年英雄吕锡三》之类塞给人家。估计人家见我们是孩子,也不计较。电影开演,书摊立即移至武昌电影院门口。
武昌电影院电影票。朱汉昌收藏
我们好像是下午赶6:20的轮渡回汉口的,在船上清点钱的时候,刨掉来往的船票钱每人大概分了一角多钱。马震开始向大家吹“比拉板车划得来吧”,接着又大叫“划不来”,因为来往的船票和耽搁的时间“是钱啊”。
第二天,心一横,出校门,去江边,就在长航候船室摆摊了。果然,收入大大增加,每人大概分了七八角钱。真刺激。有了钱,恒子上课似乎乖一点了,偶尔还抬头看看黑板。
摆摊租书的事老师们都知道,也没有干涉,只是我被班主任叫去问明了原委后,她点着我的脑门说了句:“人叫不走,鬼叫飞跑。”一个学年结束后,我们原班人马又回到了大兴路小学,与这三位同学就断了联系。
大兴路小学的条件比大董家巷小学好得多,不过从此感觉课余生活比较单调。记得当年统一街有个半日制的民办小学,学生必须拿自家凳子坐在课堂,在大兴路小学最大的快乐就是趴在窗户口,高声羞辱提着凳子路过的同学:
民办小学huái(差的意思,下同)又huái,棺材板子当黑牌,huái货老师来教书,教的学生都是猪。
后来才知道,那时读公办民办全看出生的时间段,下半年(注:9月1号之前)出生、户口又在生源饱满的街区,就不算“适龄”儿童,如果不愿因此耽误一年,只好屈从民办了。在大董家巷小学虽然仅一个学年,但懵懂中隐隐约约体会到了世情和人情。
六十多年了,儿时玩伴今何在,梦里常忆校园外。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汉口解放电影院
转载请注明出处,勿侵犯知识产权!
扫描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