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过云楼 顾氏家族 《沪吴日记》 中日艺术交流 近代书画流通
Keywords Guoyun Pavilion; Gu family; Kōgo Diary; Sino-Japanese artistic exchange; modern circulation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苏州收藏家顾文彬(1811—1889,图1)创立的过云楼,所藏书画、碑帖及善本古籍自清末民初以来便在江南文化圈中享有盛誉,坊间更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半壁江山过云楼”的说法。近年来,随着过云楼旧藏陆续亮相苏州、南京、北京等地的展览与拍卖会,其艺术价值与文化地位越发引起学界与公众的关注。例如,苏州博物馆于2016年12月起举办“烟云四合: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展览,为“清代苏州藏家”系列学术展的首个展览。〔1〕随后,南京图书馆与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其前身为江苏古籍出版社)合作,于2023年策划了“霞晖映世 源远流长:百年’过云楼’古籍书画精品合璧展”。〔2〕两大展览首次系统呈现了顾氏三代所收珍稀善本与历代书画碑帖名迹,其中包括被董其昌誉为“法书天下第一”的《北宋拓定武兰亭序》(苏州博物馆藏,图2) ,以及敦煌藏经洞发现前即已广为传世的唐代写经《续华严经疏》卷(私人藏,图3)等重器,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反响。
图1 过云楼第一代主人顾文彬(1811—1889) 引自苏州博物馆(陈瑞近)《烟云四合: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图录,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
图2《北宋拓定武兰亭序》册(五字未损本) 苏州博物馆藏 引自苏州博物馆(陈瑞近)《烟云四合: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图录
图3 过云楼旧藏《唐人写经续华严经疏》卷 引自苏州博物馆(陈瑞近)《烟云四合: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图录
早在太平天国战乱之后,关于过云楼收藏的消息便经由避乱东渡的清人书画家(日语为“来舶清人画人”)在长崎一带广为传播。加之江户末期以来中国书画及刻帖的大量输入,以及清中晚期江浙文人画家与日本文人画家的深度互动,使得日本南画(文人画)界对吴门画派、四王吴恽等清代主流画风早有认知。〔3〕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之下,顾氏旧藏中的精品如石溪《达摩面壁图》(泉屋博古馆京都馆藏,图4)与八大山人《安晚册》(同馆藏,图5-1至图5-4)辗转东渡,最终流入日本。
图4 [清] 石溪 达摩面壁图 纸本淡彩 21.3×74.3厘米 1665 日本泉屋博古馆京都馆藏
图5-1 [清] 八大山人 安晚册(引首) 纸本水墨 31.5×27.5厘米 日本泉屋博古馆京都馆藏
图5-2《安晩册》之二《鹌鹑图瓶花》 日本泉屋博古馆京都馆藏
图5-3《安晚册》箱盖上桑名铁城的题签 日本泉屋博古馆京都馆藏
图5-4 明治初期书画家江上琼山撰写的跋文 日本泉屋博古馆京都馆提供
然而,关于过云楼收藏的形成机制与文化特征以及上述绘画作品究竟于何时、由何人、通过何种方式进入日本,目前仍缺乏系统的历史考证。已有的研究虽有若干推测,然诸如《安晚册》由日本篆刻家桑名铁城(名箕,字星精,号铁城、大雄山民等,1864—1938)于清末购得之说,尚无法确认它与顾氏之间的具体关联。〔4〕
本文作为关于《达摩面壁图》与《安晚册》东传日本的前期研究,拟以近年来苏州档案局与过云楼文化研究会整理出版的《过云楼书画记》(2011)、《过云楼日记》(2015)、《过云楼家书》(2016)与顾麟士(字鹤逸,号西津渔夫、和鹤庐主人,1865—1930)所著《过云楼·续书画记》(1927年初版、1999年再版)等史料为基础,结合近年出版的展览图录与拍卖目录,以及日本儒医兼书画家冈田篁所(1821—1903)所遗《沪吴日记》[上、下,明治二十三年(1890)] 、《修竹楼坐右日记》,并参考《琼浦笔谈》等赴日清人书画家与日本书画家和僧侣学者的笔谈资料,考察顾文彬父子与日本书画收藏界之间的交流脉络,探寻这些顶级收藏品流入日本的可能路径。通过钩沉这段跨文化交流史,笔者希望为近现代中国书画及珍稀古籍流通机制的重构提供一个以“过云楼”为核心个案的分析视角,同时也为日后更为系统的清中期中日书画交流史研究提供史料基础与方法尝试。
一、过云楼收藏的形成及特征
过云楼的首任主人顾文彬,字蔚如,号子山,又号紫珊,晚号艮庵,系清代元和(今江苏苏州)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历任湖北汉阳府知府、武昌盐法道、浙江宁绍台道员等要职。顾氏家族涉足书画收藏,肇始于其父顾大澜,于道光八年(1828)已有相关活动;至顾文彬,则自同治八年(1869)起展开个人的搜求。不过,其收藏活动真正步入轨道,是在同治十年(1871)丁忧之后复出仕途、出任浙江宁绍台道员之际,此时他得以凭借厚禄广筹资金,积极搜访购藏,收藏渐成规模。
此前,顾氏之收藏尚无显著之处,亦未跻身江南显赫藏家之列。盖因苏州自明清以来,素为文人荟萃之地,书画流通与收藏尤为活跃,聚集如吴云(字少甫,号平斋,晚号退楼主人,1811—1883)、潘曾玮(字宝臣、季玉,1818—1886,潘世恩第四子)、潘遵祁(字觉夫、顺之,号西圃,1808—1892,潘世恩堂侄)、何绍基(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蝯叟,1799—1873)、沈秉成(字仲复,号听蕉,藕园主人,1823—1895)、李鸿裔(字眉生,别号香严,晚号苏邻,1830—1885)、李嘉福(字麓苹,号笙渔,1829—1894/1839—1904)等一代书画名家与收藏重镇,藏品流转其间,目力所及皆为精品。顾氏初涉其间,自属“后起之秀”,其名未为时人广知。自同治十年(1871)任浙江宁绍台道员后,顾文彬遂得以资力为凭,广布耳目,凡书画之珍品无不力求收入囊中。光绪元年(1875),顾氏辞官归隐,返里苏州,优游林下,又通过购藏前辈旧藏或与之互易,藏品之质日益精良。此后顾氏收藏虽趋于平缓,但其一生所收之精华,尤为后世称为过云楼之“镇楼之宝”者,业已收入掌中。借此顾文彬跻身江南一流藏家之列,过云楼成为区域内负盛名之藏书宝阁。〔5〕
(一)收藏形成的三要素
依笔者之见,过云楼收藏体系之得以肇建,盖赖“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之合。其中“天时”尤为关键,故当首先论及。
探讨过云楼收藏初成之际,有两个时段不容忽视:其一为太平天国之乱前后,其二则为顾文彬任浙江宁绍台道员之在官时期。太平天国之役所带来的动乱,几近摧毁江南原有经济秩序,苏州及其周边的名门望族世守之书画收藏皆因兵燹离散外流,为顾氏家族提供了难得的购藏契机。同治九年(1870)三月,顾文彬丁忧起复,为谋再仕之机而赴京,旋于闰十月被擢为浙江宁绍台道员,并于次年正月赴宁波履任。顾氏一到任,即于公事之暇,专志搜访名迹,所得碑帖书画,数量可观。是情是状,于其自著《过云楼书画记》中有明载:“余素嗜书画,自唐宋元明迄于国朝,诸名迹力所能致者,靡不搜罗,旁及金石,如钟鼎古钱古印之类,亦皆精究。”〔6〕其藏癖之深、搜罗之广,可见一斑。其孙顾麟士于《过云楼·续书画记》自叙中,对其祖父之收藏盛况有所追述:“溯道光戊子,迄今丁卯,百年于兹。唐宋元明真迹入吾过云楼者,如千里马之集于燕市。”〔7〕由此可知顾氏后人对于前辈之收藏盛业,颇以为荣,亦间接印证过云楼收藏于斯时已臻高峰。
“地利之便”亦为过云楼收藏体系得以构建之关键因素。顾文彬籍贯苏州,仕途所之宁波乃至早年求取功名之地北京,三地皆为自南宋以降迄于明清,文人画创作、流通与鉴藏之枢纽重镇。同治九年间,顾文彬曾于京师琉璃厂古玩肆购得少量书画珍品;任职宁绍台道员期间征集到其主要藏品;辞官归里后广泛结交苏州当地收藏大家,通过购藏或交换等方式,进一步充实了过云楼藏品之规模提高其品位。〔8〕
近年苏州博物馆主办的“清代苏州藏家”系列学术展亦印证了这一文化现象。其间,出身浙江、寓居于此且有同样收藏癖好者有吴云、沈秉成、李嘉福,湖南之何绍基,以及四川人李鸿裔等,皆与顾文彬交往甚密。
图6 [清] 胡芑孙、任熏 吴郡真率会图(局部) 纸本设色 42.5×1003.5厘米 引自苏州博物馆(陈瑞近)《烟云四合: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图录
顾文彬与上述诸公,或因婚姻结好,或通过园林雅集、诗酒酬酢之文会结为忘年之契。顾文彬还与吴云、沈秉成、李鸿裔、潘遵祁、潘曾玮等人共组“吴中真率会”,其《过云楼日记》中屡屡记载与这些友人游赏聚会、品评书画之胜情逸事(图6)。〔9〕如其光绪五年(1879)与十年(1884)日记中所载(括号内文字为引文者所加,以下同):
午刻,赴网师园,坐客少仲、退楼(吴云)、仲复(沈秉成)、养闲(潘曾玮)。见香严(李鴻裔)新押之《醴泉铭》,张小华旧藏,帖之边纸,翁覃溪(翁方纲)精楷题满,固是宋拓佳本,尤以翁题增重。此外尚有宋拓《王圣教序》、王石谷(王翚)《趋古》册,石涛《山水对题》册,张得天(张照)、陈香泉(陈奕禧)两字册,共押千金,已是足价,未必取赎矣。《醴泉铭》数年前曾许过五百元,未成交,今为香严所得。信乎,有前定因缘,不可强也。
光绪五年(1879)二月十八日〔10〕
举七老真率会,移樽于潘西圃(潘遵祁)之三松堂,与会者蒋心香(蒋德馨) 、彭钝舫(彭慰高) 、吴引之(吴艾生) 、吴语樵(吴嘉椿) 、潘养闲(潘曾玮) ,期而未至任筱园。庭前安罗花盛开,西圃手剪数枝分赠座客,首唱七律两章,余与诸公各有和章,并乞顾若波绘《西圃看花图》,请会中人各书和诗于后。
光绪十年(1884)四月十二日〔11〕
上述日记所载诸人,皆为顾文彬交游之旧谊。其所称“香严”者,即网师园主人李鸿裔;“仲复”乃藕园主人沈秉成;“潘养闲”与“潘西圃”则分别为苏州潘氏望族之潘曾玮与潘遵祁。顾氏与诸人或因雅好相投,或有姻亲之故,交谊颇深。实则,顾文彬诸多藏品正是经由这些苏中藏家挚友,或借清末赴日书画家之中介,得以自北京、宁波、粤地乃至东瀛搜集而归。由此可见,于顾文彬之收藏体系而言,涵盖地域之广与来源之繁,皆赖其密切而广泛之人际网络。是所谓“人和”之利,不可忽视者也。
既知顾文彬所藏精品,多购自其任浙江宁绍台道员期间[即自同治十年(1871)旧历正月至光绪元年(1875)辞官归里],则有必要据其当时所书与三子顾承(字承之,号骏叔、乐泉,1833—1882,图7)之家书、日记及书画著录诸材料,进一步考察顾氏一门之收藏趣味及过云楼藏品之主要特征。
图7 吴昌硕绘过云楼第二代主人顾承小像 引自苏州博物馆(陈瑞近)《烟云四合: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图录
(二)顾氏家族的收藏趣味及藏品特征
《过云楼书画记》与《过云楼·续书画记》,乃顾氏三代,即顾文彬、其子顾承、其孙顾麟士于过眼书画碑帖逾千件中精心遴选尤为精妙者加以著录之成果,为过云楼收藏面貌之一斑,不足以尽窥其全貌。根据两书所载,可知过云楼所藏法书名迹,包括智永、范仲淹、苏轼、赵孟𫖯、董其昌等历代名家书作;而其绘画收藏,则涵盖自唐代吴道子以下,至宋代巨然、李公麟、米友仁、刘松年、夏珪、扬无咎,及元代四大家、明四家、清初四僧、四王吴恽、金陵八家等诸大家之杰作,代有名迹,为后人称道。其谓“镇楼之宝”者,则有北宋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卷、元代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元代赵孟𫖯的《吴兴清远图合》卷、元代张渥的《九歌图》卷、明代徐渭的《墨花》卷等,皆为艺术与文献价值并臻其极者。
关于过云楼藏品之特征,陶大珉曾据前述两部著录与相关史料,编制了3张表格,并收录于其2011年发表的论文《过云楼到怡园:顾氏书画鉴藏及其艺文交往》附录(见该论文第432—434页)中。其中包括附录二所列之“顾氏藏画总数表”表①(据《过云楼书画记》),表②(据《过云楼·续书画记》),以及附录三所列之表③“《过云楼》收藏历代绘画群体作品表”(依据两书中所载画家加以分类整理)〔12〕,为研究顾氏收藏体系之结构与美学趣向,提供了系统而有价值之量化依据。
依据陶大珉所整理之顾氏藏画总数表①与表②,可见顾氏三代在《过云楼书画记》及《过云楼·续书画记》中所著录之书画作品共计359件,其中由顾文彬与其子顾承父子所收者113件,顾麟士所藏者则达246件,显示其承前启后、扩充家藏之不懈努力。其次,从藏品种类分析,绘画远多于书法;就装潢形式而言,顾文彬与顾承父子之收藏重心多在画类之手卷与立轴,尤以手卷为重;而其孙顾麟士则似对手卷式绘画兴趣稍减,收藏中以其他形式为主。至于书迹部分,顾文彬父子以手卷为主,次为册页,所藏颇丰;顾麟士在此方面亦多有收藏,手卷与册页两类数量几与前人相埒。陶氏指出了顾氏三代几无立轴式书迹之收藏,然其论文中并未就此现象给出明确解释。〔13〕
依笔者浅见,此现象或可从清中期以降之书法生态及收藏习尚加以探讨:其一,清代中后期金石学风行,碑学兴起,书风逐渐转向精谨严整之笔法,擅作大幅行草者日渐稀少;与此同时,“馆阁体”之盛行亦使书法审美趋于规范,立轴大字之形式不复为时尚所趋。其二,从受众层面观之,手卷与册页便于陈列案头,适合文人日常赏鉴与递相观玩,具有更强的亲近感与实用性;从流通与收藏的角度观之,立轴不仅不易携带与贮存,且因体量较大,装裱成本亦高,再加之江南地区如苏州一带多雨潮湿,悬挂墙上的立轴极易受潮损坏,故难为藏家所偏爱。由此可见,至清中叶之后,书画收藏市场日益分化,文人阶层与鉴藏家出于赏玩与实用之需,渐多偏好便于流通、易于保存之手卷与册页,立轴则因其体制之不便而渐趋式微。〔14〕
此外,参照陶大珉于其论文附录三所编《过云楼收藏历代绘画群体作品表》(表③),可观察到在顾氏三代的收藏体系中,明清两代画家以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及清初四王吴恽(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之作品数量最为突出,成为过云楼藏品中熠熠生辉的重要组成。此种收藏倾向,笔者以为不仅与顾氏家族本身之在地性——世居苏州,深植吴门文脉——息息相关,亦与清代以来正统文人画派之审美趋向及画学评价体系密切相连。
清代在官方及文人群体中,对以董其昌为代表所建构之文人画正统谱系多有推崇,明四家与四王、吴恽皆被奉为画道正宗,顾氏之收藏视野与价值取向显然受到这一主流话语的影响。顾文彬收藏心态亦可由其致子书信中窥见一斑。同治十年(1871)四月,顾文彬为求得王蒙(号黄鹤山樵)与王翚之佳作,特地致函其子顾承,再三叮嘱,语气之迫切,足见其对正统画派名迹之珍视程度,亦反映出当时文人士大夫以收藏“正脉”画为荣耀的时代风尚:
玉溪之物,山樵、石谷两册,世间稀有,切勿交臂失之,更恐为捷足者得去,如肯脱手,亟须取归。
同治十年(1871)四月二十七日第12号〔15〕
翌日复信,字里行间流露对所得二册之渴望:
昨夜悬想山樵、石谷两册,几不成寐。(中略)两册总以购成为度,且能于数日内成交最妙。
同治十年四月二十八日第13号〔16〕
至六月初九日所致儿子的信中,更详述其中抉择与考量,明言于二者之间取舍之故:
玉溪乃江湖老友,藏此瑰宝,求之者又众,岂肯轻售? 二者不可得兼,舍黄鹤而取石谷。(中略)石谷册不为稀有,然如此大册,实所罕见,况我家若聚四王巨册,缺此不可,故莫惜重价也。
同治十年六月初九日第17号〔17〕
信中可见,顾氏父子为购此册,周旋于藏家之间,殚精竭虑,终得石谷大册,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如六月十五日的信中写道:
石谷册如愿而得,可谓快心之事。抄录各题并各幅结构,虽未目击亦可神游。
同治十年六月十五日第19号〔18〕
顾文彬笃志搜求明清正统派诸家书画,其用心之深,于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十三日所记日记中可见一斑:
张子蕃前日自上海来,携到书画各件,买得其文衡山(文徵明)轴廿八元、文衡山轴廿四元、王麓台(王原祁)大轴卅二元、吴渔山(吴历)小轴廿元、柴桢册六十元、石涛册六十元、莲池大师卷廿六元(下略)。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十三日〔19〕
同时期所致顾承家书中,他亦称“价虽稍昂,所选皆精”〔20〕,足见其对此次交易之满意。正因为如此,即便顾文彬在以下《过云楼家书》与《过云楼书画记》中,对八大山人的《安晩册》与石溪的《达摩面壁图》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然顾氏父子为冀求更高品质之明四家或四王吴恽之作,竟于清末某一时期将此两件藏品转售他人,遂致其远流日本。
茅古董携示石涛、石溪两卷,石涛卷赝作无疑,石溪画达摩面壁图,引首题跋皆有石溪书,石溪画境与石涛相近,而书法似更胜。后跋十家,程青溪、龚半千、释大嵩、行澈,皆有名者也。此卷昔年在上海,记得于黄受益铺中见过,不知何以不买,大约嫌贵。石溪之画甚少,此卷似不可失。
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二十六日第111号〔21〕
改革之际,贤士君子相率飞遁,往往皈心竺乾,寄迹芯刍,以遂其志节。间或粗笔淡沈,写其伊郁悲凉之况,不得以寻常绳尺拘之也。山人此册合题跋二十二帧,作山水者二,余皆为写花果鱼鸟。水墨设色,信笔点染,意到而已。然神气溢出,姿态横生,可谓奇而法,醇而肆矣。〔22〕
那么,《安晩册》《达摩面壁图》两件顾氏旧藏,究竟何时、由谁携入东瀛? 流入日本者是否仅止此两件? 为解此疑,笔者拟以清中期来往中日之间的书画家与僧侣笔谈文献《琼浦笔谈》,以及明治初年来华的日本书画家兼儒医冈田篁所遗《沪吴日记》为线索,先就顾氏父子与日本学者及书画家的结缘始末,作一探究。
二、赴日清人书画家、日本汉学家和书画家与过云楼
依据笔者目前之调查,最早将过云楼收藏信息传入日本者,极可能为与顾家因书画碑帖之交易和鉴藏而建立深厚关系的苏州书画家金邠(字子则、邠卿、嘉穗,号芷山、病鹤等,1834—?)。从以下日记和笔谈资料来看,金氏可谓联结过云楼与明治初期日本书画收藏界的关键人物。
据鹤田武良(1937—2009)及町泉寿郎之研究,金邠于同治九年[明治三年(1870)]三月,为避战乱,将妻留于苏州,独自一人赴上海避难。其后随日人赤松氏转赴长崎,旅居期间以书画营生。翌年同治十年[明治四年(1871)]一月下旬,受名古屋藩主延聘至藩校明伦堂,担任“教习”之职,讲授儒家经典、汉文及书法。其门下弟子中,有后成为明治政坛与文坛重镇的汉诗人森槐南(名公泰,字大来,别号秋波禅侣、菊如澹人,1863—1911)及书画家永坂石埭(名周,字希壮,号石埭,1845—1924)等人。然明伦堂于明治政府推行“脱亚入欧”政策之际,废弃传统汉学教育,转而推广西学与西语课程,金邠遂于同治十一年[明治五年(1872)]三月被解聘,旋即束装归国。〔23〕
然而,在同治九年金邠旅居长崎期间,其活动远不止于单纯避乱与谋生。据考,他不仅与被誉为江户末期“长崎南画三笔”之一的文人画家、长崎华岳山春德寺第十四代住持铁翁祖门(俗姓日高,讳祖门,道号铁翁,别号莲舟人等,1791—1872)及其弟子冈田篁所建立起亲密关系,更在铁翁引介之下,于该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结识了来长崎讲学的净土宗高僧、京都千年古刹知恩院第七十五代住持养鸬彻定(1814—1891)。
在与彻定进行的多达六次的笔谈(《琼浦笔谈》)中,彻定曾展示其私人收藏的《菩萨处胎经》《大楼炭经》等西魏和唐代写经,还请金邠题写跋文。作为酬谢,彻定以《唐写续华严经疏》卷与《福田经》赠之作润笔。金邠归国后,即将《唐写续华严经疏》卷售予顾文彬(相关内容后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两人第二次笔谈[同治十年/明治四年(1871)一月三日]中,金邠首次向彻定披露顾文彬父子于宋元名迹方面之精鉴力(图8);而至第四次笔谈(同年一月十三日),金邠又提及冈田篁所为其拟定在长崎挥毫润例,可见其与冈田之间交谊匪浅,此情节亦可在以下冈田日记中得以佐证。〔24〕综合前后脉络,不难推知:冈田极可能是在初步掌握过云楼收藏信息之后,遂决意踏上访华(苏州)之旅。不过,与《琼浦笔谈》相比,更为详尽记录顾氏父子及其书画收藏状况者,当数明治初年来华的冈田篁所所著《沪吴日记》(图9-1)。
图8《琼浦笔谈》(右)提及顾文彬父子 同治十年正月三日(明治四年,1871)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室藏
图9-1 冈田篁所《沪吴日记》(上)封面 明治二十三年(1890)日本长崎私家版
(一)冈田篁所与《沪吴日记》
冈田篁所(图10),生于文政四年(1821),为肥前藩长崎(今长崎市)人,名穆,字清风,号篁所、修竹吾庐、小绿天、大可山人等,医号为恒庵。其门下弟子中,尤以北方心泉(名蒙,号心泉,1850—1905)、江山琼山(名景逸,字希古,号琼山,1862—1924)等最为知名,均为活跃于明治至大正时期书坛的书画名家。
图10 江户末期长崎出身的汉学家、书画家兼儒医冈田篁所 日本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藏
明治五年[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十三日,冈田偕同擅长书画的友人、长崎古董商松浦永寿(生卒年不详),以及当时暂居长崎的苏州人汤韵梅,自长崎港启程赴华。三人于二月十五日抵达上海,随后游历了上海、苏州及其周边地区,于四月十三日返回长崎。冈田所撰《沪吴日记》即为其此次从长崎出发,经上海、苏州游历,再返回长崎途中之纪行实录。该日记详细记述了旅途见闻,亦具体记录了旅途中与沪苏两地中日书画家、收藏家、外交官员及医者之间的交流往还,内容不仅具史料价值,更反映了明治初期中日文化互动之实貌。
关于《沪吴日记》的先行研究,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最早提及该日记者为鹤田武良,其所发表的系列关于“来舶画人”研究,尤其是《关于金邠:来舶画人研究(一)》《关于王寅:来舶画人研究(二)》《陈逸舟和陈子逸:来舶画人研究(四)》《王克三与徐雨亭:来舶画人研究(六)》这4篇论文,均对过云楼收藏及其主人顾文彬有所论及。〔25〕其次是陈捷在2000年、2003年与2009年间所发表的论文与专著,其中特别对《沪吴日记》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并具体提及顾文彬及其子顾承,以及过云楼相关情况。〔26〕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09年为止,顾氏家族与过云楼相关的核心史料(如《过云楼家书》《过云楼日记》等)尚未在中国正式出版。因此,鹤田与陈捷的研究视角主要立足于日本,聚焦于日本汉学家、书画家及滞留日本的清人书画家等人物之活动。由于这一研究立场的限制,他们对于以下三组交流关系——清人书画家与顾氏家族,赴日清人书画家与日本汉学家、书画收藏家及佛教学者,以及顾氏家族与明治初期来华的日本书画家及古董商之间的密切且错综复杂的互动,尚未给予充分关注与深入分析。〔27〕
此外,近年来中国学界亦有学者尝试依据新近整理与出版的过云楼相关史料,从中医学史的角度重新定位《沪吴日记》的史料价值。这类研究虽拓展了《沪吴日记》的使用路径,但遗憾的是,尚未有效整合日本所藏的其他史料,亦缺乏对中日史料之间的交叉印证。因而,对于笔者前述顾氏父子与来华日本书画家、顾氏父子与长期滞留于长崎的清人书画家,以及清人书画家与日本汉学家及书画家之间这三重错综的交流关系,尚未展开系统且深入的考察。〔28〕
尽管如此,笔者自上述先行研究中获得重要启示,进而在本文中尝试转换视角,以过云楼主人为中心,聚焦《过云楼日记》《过云楼家书》《过云楼书画记》等史料,并将其与《沪吴日记》及相关笔谈记录对照阅读,从中国(即过云楼)出发,重新评估《沪吴日记》在中日书画交流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
(二)拜访过云楼之前的种种偶遇
冈田一行于同治十一年[明治五年(1872)]二月十五日抵达上海后,最初拜访了此时旅居沪上的日本南画家安田老山(名养,字老山,别号万里翁,1830—1883)夫妇,随后开始游览上海市区。在《沪吴日记》中,过云楼第二代主人顾承之名首次出现是二月二十四日。〔29〕然此前的二月十九日日记中,“金邠”之名已然出现。如前所述,金邠当时尚滞留于名古屋,担任明伦堂教习;而顾文彬则因正在宁波任所,顾承受父亲之托,全面负责苏州过云楼事务,包括怡园(其中包含过云楼与坡仙琴室等)的增建、书画的购藏与交换、家族义庄与当铺的营运以及子孙的教育等事宜。
同日(二月十九日),冈田一行在游览上海市区后归途中,偶见书法家翁东谿的招牌,遂造访其寓所,与之进行笔谈。席间,冈田得知翁亦系苏州府吴江县人,便顺势询问其是否识得金邠,并称金邠“聘于尾州也,弟聊与有力”(标点符号为引者所加,以下同)。
(篁)吴江人,姓金名邠,字嘉穗,又号䆃(通禾)菴。去年航海来长崎,与余交善,先生知此人否?
(翁)此人素相知,尚在长崎否?
(篁)金邠应尾州侯之聘,闻近况顺吉。其聘于尾州也,弟聊与有力,今尚在尾州。
一八七二年二月十九日〔30〕
以上笔谈虽尚未提及顾氏父子,但冈田已明确表露其与金邠的深厚交情,并借与翁东谿的交谈再次确认金邠的活动动向与人际网络。
次日(二月二十三日),翁东谿回访冈田,因冈田外出未能相见,仅留下一纸字条。翌日(二月二十四日),冈田登门回访,两人进一步笔谈。在此次对话中,“顾骏叔”这一关键人物首次出现在冈田的日记中(图9-2):
图9-2 冈田篁所《沪吴日记》(上),1872年2月24日日记中第一次出现顾承名字 明治二十三年(1890)日本长崎私家版
(篁)客春贵友金嘉穗笔话中,有桶脱和尚及顾骏叔,皆苏州人,先生知此人否?
(翁)顾骏叔,其父号子山,位居二品,现在宁波道任内。骏叔仍在苏州,其收藏碑版书画甚富,弟固相识。桶脱和尚想是别号,未知其姓氏,却不熟识。
(篁)闻之金嘉穗曰:“桶脱和尚避长毛贼乱,夫妇入道,深隐山中。”余曾见其所作诗书画,酷慕其人。弟近日将游苏州,希带阁下手书通谒顾先生,幸许否?
(翁)可以俟。弟书就后,送至贵庽(通“寓”)耳。
二月二十四日〔31〕
通过上述笔谈内容,可清晰看出冈田对顾承(字骏叔)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已通过金邠等人掌握了其人及其家族书画收藏的重要情报。翁氏所提供的背景信息也进一步印证了顾文彬时任宁波道员的官职与顾承常驻苏州、主理家事的现实,说明冈田之行已有明确目标,即拜访顾氏家族,并借此深入接触江南上层士绅的收藏网络。值得注意的是,冈田此处所言“近日将游苏州,希带阁下手书通谒顾先生”,不仅表明其访顾之志切切,也可视为他此次访华旅程进入实质性阶段的标志。在得到翁东谿的书信允诺之后,冈田正式将“谒顾”列为其苏州之行的重要任务。
接下来的行程安排亦与此笔谈相呼应。冈田一行于三月七日启程离沪,途经溇泾、徐家汇、青州、昆山、长洲等地,并于三月十一日抵达苏州。沿途,冈田不断探询顾骏叔的消息,显示其访顾之行并非例行游历,而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准备性。令人意外的是,就在船抵苏州阊门之日,一位名叫王正帆的苏州人主动登船拜访冈田,进一步向其透露了关于顾氏父子、金邠及其他赴日书画家的诸多细节信息。这一意外会面,可视为冈田即将进入过云楼核心圈层的又一契机。
(王)小弟于同治二年、三年之间,曾至贵邦三次,惜各处未曾游到,不胜怅恨。(中略)请问二公来此,有何贵干否?
(篁)二人来此欲谒文墨之士,览佳山水;又问收藏家,观古贤之遗墨耳,此外无一干事。闻苏州顾骏叔先生,颇富收藏,弟在敝邑时,苏人金嘉穗名邠,为余所话也。
(王)顾骏叔之父,现任宁绍台道,二品官。他家收藏书画极多,住城内铁瓶巷。金嘉穗,号芷山,画兰并好金石。二人小弟俱认识。嘉穗右足不良,身子甚弱,闻在尾州,尾州距长崎远近如何?
(篁)尾州东距长崎二百余里,即贵邦里程当二千余里。火轮船四、五日即达。邠兄夫人尚在苏州否? 弟欲明日去报其平安。
(王)邠兄之夫人物故多年,未曾续娶。有叔祖在上海,即金保三先生,行医住二马路。
(篁)在上海时却不得闻之,今于先生闻之,多谢!王克三,乍浦人,擅书画,曾来长崎,与弟相善。闻现游苏州,先生亦认识此人否?
(王)骏叔要去访否? 如欲去访,须先嘱韵梅兄问明,或请骏叔来舟会晤亦可。克三先生问之骏叔即知。
三月十一日〔32〕
从笔谈内容来看,王正帆与金、顾两家均有交往,并熟悉苏州当地士绅和收藏家网络,其在同治二年(1863)至同治三年(1864)之间三度赴日之经历亦使其成为了解清日文化交流背景的重要人物之一。尤其是在冈田明确表达“欲谒文墨之士”“观古贤之遗墨”之旅行目的后,王氏便迅速提供有关顾氏家族居所(城内铁瓶巷)、收藏状况(书画极富)及金邠家族等信息,显示出其对苏州文人圈之熟稔。此外,笔谈中还涉及诸多值得注意的情报线索:如金邠“右足不良,身子甚弱”,以及其大伯金德鉴(又名宝鉴,字保三,1810—1887?)在上海行医的消息,皆为冈田日后深入了解金氏家族背景提供了具体参考。除此之外,冈田在笔谈中,还提及另一赴日清人书画家王克三(名峻明,字克三,1822—?),反映出冈田在长崎相识的清人书画家不止金邠一人,而王正帆提供的信息,使得冈田在苏州的文化交游网日渐清晰,也逐步展开。更为重要的是,王正帆在笔谈中主动提出“须先嘱韵梅兄问明,或请骏叔来舟会晤亦可”,无疑为冈田与顾承之间的正式接触打开了路径。此举标志着冈田此次苏州之行已从初期的探访与打听,转向直接进入顾氏家族核心圈层的实质阶段,因此,王氏不仅是信息提供者,更实际成为冈田与顾氏建立联系的中介角色。
(三)连接过云楼和日本书画收藏界的关键人物金邠
三月十二日,冈田致信顾承,告知将于翌日前来拜访。信件送出当日,冈田即与松浦、汤韵梅一道,冒着蒙蒙细雨前往顾氏宅邸怡园。此次访问在怡园中的坡仙琴馆进行。冈田与顾承虽为首次会面,然两人迅即建立起深厚的共鸣,言谈之间有“相见恨晚”之感。宾主甫一寒暄,话题便自然转入他们共同的朋友金邠(图9-3—图9-6):
(篁)遂访顾骏叔,书曰:“昨通贱名,蒙见许拜谒,今来候。”
(顾)金邠现寓贵邦,何日还里,其近况祈赐示!
(篁)邠兄来我邦也,与弟最善。其聘于尾州也,弟聊助其力,闻近况顺吉,如锦归,当在明年桂花之时。
(顾)请先生用茶了,到我书室里一坐。
三月十二日〔33〕
图9-3 冈田篁所《沪吴日记》(下),1872年3月12日日记中与顾承初次见面笔谈之一
图9-4 冈田篁所《沪吴日记》(下),1872年3月12日日记中与顾承初次见面笔谈之二
图9-5 冈田篁所《沪吴日记》(下),1872年3月12日日记中与顾承初次见面笔谈之三
图9-6 冈田篁所《沪吴日记》(下),1872年3月12日日记中与顾承初次见面笔谈之四
从这段笔谈内容可见,顾承对于远在东瀛的金邠近况颇为关心,特别询问其回国日期及身体状况。这种关切并非偶然,而是基于金邠及其家族与顾氏之间长年累积的深厚私交与合作关系。金邠不仅通过其书画鉴藏与交流活动与顾家保持密切往来,其大伯金保三更因擅长书画收购、鉴定及经营之道,与顾文彬父子建立了稳定的收藏与流通管道。金邠本人更积极参与顾氏书画收藏的编目与出版事务,成为过云楼文化实践的重要协力者,这点亦可从顾文彬所撰日记、家书及著录中得到印证。
在《过云楼日记》与《过云楼家书》中,金邠的大伯父金保三之名频繁出现,是顾文彬书画收藏网络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如家书所示:
昨晤金保三、张子祥、徐顺之、张子凡,各有所见。保三处有倪文贞字卷《赠范景文》律诗六首,子凡处有文贞札两通,若买来裱在文贞画后,皆妙,惜皆价昂,不能得也。
同治九年(1870)三月十三日第4号〔34〕
保三仍将赵卷寄来,其价落至五十元,我仍以四十元寄去,大约必成。
同治十年(1871)五月二日第4号〔35〕
顾文彬赴宁波任职的同治十年(1871)期间,其致顾承的第6号、第7号、第10号、第15号、第21号及第31号至第34号家书中,频繁提及与金保三之间的书画交易。〔36〕然而,或因金保三屡次未按约履行与顾文彬的书画交易,其名字在顾氏家书中一度沉寂,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四月五日顾文彬致顾承的第11号家书中才再度出现。〔37〕耐人寻味的是,尽管金保三在与冈田笔谈中强调其与顾文彬父子为“世交”关系(“乐泉父子,弟之世交也”)〔38〕,但从顾文彬所撰日记与信札的语气来判断,相较于他与金保三的合作态度,顾文彬对其侄子金邠的书画才艺、学识修养及品行风范更多褒赞,给予极高评价。如在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顾文彬赠归国的金邠诗联两首,并各附上长注,其间洋溢着对金邠的钦佩与称赞。赠金邠卿一联云:
抱三尺琴,游三山岛,水仙操,移我情矣;
载万卷书,破万里浪,郁林石,渺乎小哉。
……
邠卿先生学问湛深,襟怀豪放,前年遨游日本,东诸侯拥彗郊迎,待以上宾之礼。经年小住,酒醴笙簧,殆无虚日。迨其行也,赏赠如雪,却之不受,挟万卷书而归。先生精于琴学,亦为东人国所钦慕云。
西土求佛书,东土求儒书,三藏而还,艺林定补东游记;
下士珍货物,上士珍文物,重洋以外,异域争延上国宾。
邠卿往游日本,诸侯延为上宾,日本重中国文字,载籍极博,皆中国商人携往贸易者。中国自粤逆扰后,各省书籍尽付劫灰,邠卿忽发奇想购之异域,尽出囊中金,载书万卷而归,其余未及载者,尚有数十箧,拟雇轮舟,续往载回,豪举卓识,度越恒流矣。
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二十一日〔39〕
值得注意的是,顾文彬在日记中极少用大段文字对人褒贬,除非该人给予其深刻印象或具有非凡行谊。从以上两联诗及诗注内容来看,不仅篇幅之长在《过云楼日记》中罕见,其措辞亦充满敬意与感慨,足见顾文彬对金邠的器重与赞赏。顾文彬在日记中评价金邠“学问湛深,襟怀豪放”,并以“诸侯拥彗郊迎”“赏赠如雪,却之不受”形容其在日本的声望与气节;而诗联中的“三藏而还”“上士珍文物”等修辞,则进一步将金邠比拟为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儒书三藏”,以肯定其“载万卷书而归”之文化义举与远见卓识。金邠之所以能获得顾文彬如此盛誉,一方面固然源自他与顾氏父子之间长期而密切的私交与合作;另一方面,则亦因其作为赴日清人书画家中的代表人物,其东游行为在顾文彬眼中不仅是个人的游历,而是携回东瀛遗珠的“文化复归”之举,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这种文化使命感亦反映出顾氏家族一以贯之的收藏价值观与“守文传薪”的文人理想。事实上,数日后,金邠即将其自日本带回的唐人写经两卷,专程自苏州赴宁波呈予顾文彬披览。对此,顾氏亦在日记中留下了详细的观感:
邠卿携示东洋古寺所藏残经两卷,日本僧彻定各有跋尾,皆断为唐人所写。余审其笔意,有一卷似张即之者,不过宋人笔。其一卷系小行书,不能定为何代也。(眉批:或此卷写经在先,而张即之师其笔法,亦未可定,未敢执一己之私见也。)
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九日〔40〕
日记中所记“东洋古寺所藏残经两卷”,笔者推测是前述彻定作为润笔赠予金邠的《唐写续华严经疏》卷与《福田经》。顾文彬从书风角度出发,对其真伪年代提出细致观察与判断,一卷“似张即之者”,但定为“宋人笔”,另一卷则“不能定为何代”或“张即之师其笔法”,显示出其审慎态度。在此后的顾氏父子来往信札中,可进一步窥见金邠试图将写经售予顾家,并引发双方就价格与友情之间微妙平衡的讨论:
过云楼收藏精益求精,中下之驷则必须推陈出新,以资贴补。(中略)邠卿残经究是古物,稍加亦可,且系故友,不必与之丁丁较量也。
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初二日第20号〔41〕
信中顾文彬一方面强调过云楼藏品须“推陈出新”,通过售出中下质藏品以资购入更优者,表现出其一贯奉行的“藏品更新”之策;另一方面,出于对金邠所持写经之“古物”价值以及与其多年交谊的考量,顾亦特意叮嘱儿子顾承“稍加亦可”,“不必与之丁丁较量”。此种态度,不仅体现出顾氏对金邠之人品与物品兼而重之,也映照出清代文人藏家在情义与功利之间的平衡策略。不久之后,顾家便购入了这两卷写经。在五月初九日第22号家书中,顾文彬写道:“所得邠卿东洋写经两卷,寄来一阅。”〔42〕可见顾承已将写经寄至顾文彬任职之地宁波。顾在五月十八日信中则对其笔墨极为赞赏:
两经笔墨俱非唐以后人所能到,一洗痴肥之习,故足宝贵。此等物是真古董,然只可自怡悦,难与俗人言,亦不能刻入丛帖也。
同治十二年五月十八日第26号〔43〕
其所称“一洗痴肥之习”,当为对晚近书风佻浮冗肿之批评,对比之下更凸显写经笔墨之精古遒劲。然亦因其“真古董”之特质,不适宜纳入“丛帖”,亦即刻印流传者,说明其重“自怡悦”而非“传布显扬”的态度。直至晚年顾文彬撰《过云楼书画记》之际,仍不忘著录《唐写续华严经疏》卷之来历,写道:“余从同郡金君芷衫得之,金君游日本,从佛眼山僧彻定得之。”〔44〕此一记载不仅确证唐代珍稀经卷的传入路径,也再次肯定了金邠在顾氏收藏体系中的特殊角色。作为连接过云楼与日本佛寺写经的文化中介者,金邠在中日文物交流史上的地位亦由此浮出水面,成为顾家藏品外部来源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此外,金邠亦在顾文彬父子主持的目录编纂工作中担任了重要角色。迄今可见他参与的过云楼藏品目录主要包括:
①顾承编纂、出版,金邠题词《借碧簃集印》,同治元年(1862);
②顾承编纂、出版,金邠作跋与题款《过云楼古印谱》,同治八年(1869);
③顾承收藏,金邠考释《画余庵古泉谱》(四卷),同治十三年(1874);
④顾承收藏,金邠考释并作序《古泉略释》(六卷),光绪五年(1879)。
从上述编纂活动,可知金邠不仅与顾氏父子有同乡之谊,更以其书画素养、古文物识见以及在文献目录学上的精湛造诣,深度参与并助力了过云楼藏品体系的知识建构。他既是文物鉴定与购藏的合作者,也是目录编撰的合作者,其与顾家的关系,远超一般意义上的商业往来或文化交游。
考虑到这一特殊的交往背景,再结合金邠与长崎南画界重镇铁翁祖门及其门下弟子之间的交往关系,笔者认为,在已知文献与资料所能覆盖的范围内,金邠应该是最早将过云楼收藏资讯系统性传递至日本书画收藏界的关键人物。这一判断不仅可从其对顾氏藏品的直接参与与传播行为中得出,也将从下文所引金邠与尾州藩校主事(教务长),汉学家兼书画收藏家村濑美香(名为驹三郎、八郎右卫门,号长洲、不二三山人等,1829—1896)之间的笔谈,以及接下来冈田与顾承的笔谈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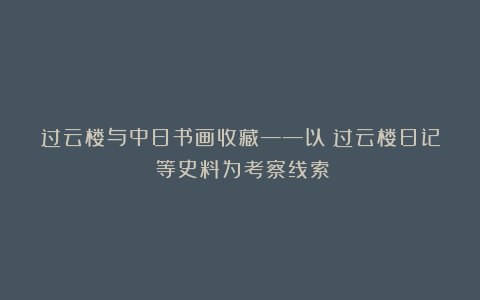
图11 金邠就过云楼所藏沈周画与村濑美香的笔谈资料 约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
金邠在明伦堂任教期间,村濑曾就其所藏沈周山水小幅的真伪问题与之进行笔谈[同治十一年/明治五年(1872)三月前后,图11],在谈话中金邠提及顾氏父子收藏,发表了就过云楼收藏的沈周作品之见解(参见画线部分):
(香)云:余久藏沈石田山水之小幅,生常爱观之,未辨真赝,愿鉴定之。
(金)云:是真迹。
(香)云:似带北气,如何?
(金)曰:此是石田晚年笔,学梅花道人。山头如(图形)此者,皆非北宗,山头如(图形)此者,乃北宗。石田下笔老劲,倍于他人,故若此气。有一敝友姓顾,现在宁波□王家。他家收藏唐宋以来书画,有千余幅,皆真迹。石田之长卷、册页、大小轴,有六十余幅,所见皆与此幅笔力相同,但有粗、细笔之不同。他家藏,甲苏州。己已(同治八年)之年,弟居他家一年,曾为之作书画谱一部,名《过云楼书画记》,如《江邨销夏录》(清高士奇的《江村销夏录》——引用者注)而加详,中亦有十余件即《江邨录》中所载者。〔45〕
从上述笔谈可知,金邠曾在同治八年(1869)前后寓居过云楼一年之久,对顾氏父子所藏历代书画,尤其是对明四家中沈周作品之数量、形制与笔墨特征了然于胸。其所言“(顾家所藏)沈石田之长卷、册页、大小轴,有六十余幅”,亦足证顾氏收藏在当时书画市场中的显赫地位。尤为重要的是,金邠提及其曾应顾家之邀,参与编纂《过云楼书画记》,称其详于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并指出该书所载作品中,有十数件与《江村销夏录》所载内容相重。此类记述显示出金邠对顾家藏品的熟谙,他极有可能通过其在日本书画界和汉学界的广泛人脉,将过云楼书画收藏的图录与观念引介至江户末期与明治初期的日本鉴藏文化圈。
事实上,在金邠归国后、与顾家完成《续华严经疏卷》等文物交易之后,他与其大伯父金宝三仍持续为顾文彬父子斡旋多宗书画交易。金氏叔侄在中日间的文物流通中所扮演的双重角色——既是文物采购与交易的执行者,又是收藏体系构建与传播的中介者——其关键地位,亦由此得以确立。〔46〕
(四)《沪吴日记》所记顾氏一族收藏与中日书画家
据《沪吴日记》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二日日记记载,当冈田篁所一行进入怡园坡仙琴馆,寒暄毕,冈田随即介绍随行者松浦永寿予顾承之后,两者重开笔谈:
(顾)前年贵国赤城米苏承顾舍,在琴馆中作画。旧岁瑞严和尚亦顾琴馆,往返者数次。今两位先生高名降舍,有无见教?
(篁)瑞严、赤城弟皆知道。瑞严是画禅铁翁之法弟。铁翁去年迁化。
(顾)篁所先生书法精妙,深为拜服,肯留墨琴馆乎?且问先生能丹青否?
(篁)謭(通“浅”)劣菲才,固无一能事,可愧!尊馆收藏之富,闻之邠卿,曰为“吴下第一”。自宗(“宋”字之误?)元以至近代名家,无一不收藏,切望拜观得益。二人留寓尚有日,于他日再来请观。
(顾)我家藏字画,俱是家传有年矣。今高躅(通“足”)远来,出以请教。如欲交易,亦可割爱。知两先生法眼甚高,得归清閟,可谓是明珠倍皎洁矣!
(篁)如割爱,余辈敢当之? 明日来请拜观。王克三、贺镜湖二位,现住在何处?
(顾)克三旧岁正月在舍榻琴馆六、七月,现在乍浦居住,贺镜湖未识其人。
三月十二日〔47〕
此段笔谈透露出数个关键信息:冈田一行并非首批访过云楼者。早在同治九年(1870),一名叫“赤城米苏”的日本人即曾造访坡仙琴馆,并曾在馆中作画;翌年(1871)正月,瑞严和尚亦数度来访。虽“赤城米苏”身份尚未详考,但“瑞严和尚”即为日本南画家长井云坪(字桂山,号瑞严,别署玉兰堂、兰华山人,1833—1899)等,其与冈田篁所均出自铁翁门下。
长井原出自越后沼垂(今新潟市沼垂町)的医学世家,嘉永元年(1848)前往长崎研习医学,其间师事铁翁与木下逸云(讳相宰,号逸云、如螺山人等,1800—1866),潜心南画。庆应三年(1867)渡清,深入研习书画,并与清末海上派名家徐雨亭(字溶,号观山樵者,生卒年不详,浙江平湖人,赴日清人书画家)、王道子(不详)、陆应祥(字静涛,嘉善人)等皆有往来。后归隐信州(今长野县),为当地南画界开山人物。
笔谈中,冈田亦提及其师铁翁已于“去年”(1871)“迁化”(去世),暗示其来华之旅中,亦肩负为先师收集书画遗墨与交流情报之使命。而顾承对其书法赞誉有加,除请其留墨琴馆外,更以“割爱”“明珠”之言,示意若二人有意交易,顾家愿出售珍品,足见其对二人来访的重视。尤值得注意的是冈田明确表示其对顾家收藏之闻见,源自“邠卿”之介绍:“尊馆收藏之富,闻之邠卿,曰为’吴下第一’。”此为金邠早期向日本书画界传播过云楼收藏信息之又一实据。冈田所言顾氏“自宗(宋)元以至近代名家,无一不收藏”,不仅可视作对过云楼藏品体系的总括评价,也反映出当时日本收藏家对中国书画收藏体系的极高关注与向往。
此外,在冈田与顾承的笔谈中,还问及王克三和贺镜湖。王克三是浙江乍浦人,也是赴日清人书画家之一,与徐雨亭、金邠等人往来密切。从顾承的言辞中,可知王在前年[同治十年(1871)]正月曾在琴馆小住数月,顾文彬的《过云楼日记》中也数次提及王克三“为画轴”或“送画稿”等记录,可见他与顾家关系匪浅,亦可谓连接过云楼与长崎书画界的重要人物之一。
此外,顾承对于“贺镜湖”则表示“未识其人”,但冈田提及的这一人物有可能是贺良辅(字镜湖),为清末活跃于江南与长崎的文人画家,不过尚无确证。另外,综观这段笔谈,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关注:
①铁翁系文人画家与顾氏家族的多重交集:顾承口中的“瑞严和尚”曾数度拜访琴馆,而“赤城米苏”也曾作画于此,可见早在冈田一行到访之前,铁翁系文人画家已与顾家有实质性交流,琴馆成了中日文人书画交流之地,此亦印证金邠(及其他赴日清人书画家)在日本传播顾家藏品信息后,吸引了日本南画家群体对过云楼的强烈兴趣。
②顾承对交易的开放态度“如欲交易,亦可割爱”,表达出顾家对书画的“可藏亦可售”的灵活态度,这也为日后日本人从顾家购买书画提供了可能性,故而《达摩面壁图》《安晚册》等佳作的出境,未必是战乱或遗散所致,抑或延续了顾氏“推陈出新、精益求精”的藏品流转机制所致。
③对过云楼的书画定位:冈田引金邠之语称过云楼为“吴下第一”,顾承亦自称“家传有年”,说明顾家自视甚高,但并非完全封闭,而是兼具文化传承与流通策略的“开放式藏家”。正如顾文彬曾言:“中下之驷,则必须推陈出新,以资贴补。”这种策略为近代中日文物交流提供了关键通道。
④铁翁系文人画家的主动拜访:无论是赤城米苏、瑞严和尚,还是冈田、松浦永寿,皆主动造访顾家,可见过云楼在当时东亚书画收藏圈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标”意义,而金邠和王克三等赴日清人书画家群体显然是促成这一网络形成的重要推手。
这一点在四天后的三月十六日在冈田在与顾承的族叔顾淇(号左泉)的笔谈中亦得到印证,是日笔谈除了王克三和徐雨亭以外,冈田还列举了其他数位与顾氏家族关系密切且熟悉过云楼收藏的赴日清人书画家的名字,而顾淇则提到了另外两位到访过苏州的日本南画家:
(篁)乍浦人王克三、徐雨亭,二人善书画。周彬如学士,三人曾避乱来长崎,流寓五、六,各得润笔一千元而归。其他钱子琴、蒋子宾,皆余之亲交也。去年金嘉穗亦来游。
(顾左泉)此数人有覿(通“见”)面者,亦是有未遇者,但若辈或腹有诗书,或手有丹青,均又在贵邦营生,不似我辈之一无擅长,我等蒲柳之质,安敢有此望耶?(中略)贵处有二先生前年来航,擅画,今忘其姓名。
(篁)闻安老三、石涧泉二人曾游苏州,二人或是。
三月十六日〔48〕
关于钱子琴和蒋子宾,冈田称其为“亲交”,亦即常来往之人,说明这批书画家与长崎铁翁系文人画圈的关系已非偶然或短期之事。至于金邠,冈田还特别提及“去年亦来游”,再度确认了金邠1871年赴日后的行迹,而顾左泉则在笔谈中提及“贵处有二先生前年来航,擅画,今忘其姓名”,冈田补充道“闻安老三、石涧泉二人曾游苏州”,可视为铁翁门下或其友人来华的更多实例,构成了一个交错的中日文人画交流网络。
此外,三月十二日,冈田还与顾家的门客兼西席许锷(字颖叔)〔49〕之间也交换了书作。顾承招待冈田和松浦午膳,并为之斡旋住宿。饭后重返坡仙琴馆,顾承自述病情,冈田则当场腹诊并开药方,这些皆显示顾承款待客人礼遇之高,以及冈田此行非仅是旁观者身份,而是积极参与与顾氏家族的互动,尤其是他以“汉学者+文人画家+医者”的多重身份,更形成一种跨文化交流中少见的人际医疗信任,这是身份互信与文化亲近达到相当程度后的产物。
从顾承与冈田一行的频繁接触中不难推测,他极有可能将冈田一行来访详情以及意欲购买书画等事宜悉数上禀其父顾文彬。而顾文彬以下的回信中明确写道:
东洋人苦于无钱,故不能买物,我家所藏绫本各件,与其托子蕃(张子祥)经手,何不与东洋人当面交易。
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第82号〔50〕
可见顾氏家族已察觉通过掮客(如张子祥)转售,不如直接对外销售来得高效、主动。紧接着在二月二十七日的信件中,顾文彬更明确表示:
接二十五日禀,具悉。日本篁所、永寿两君,与之盘桓接洽,所拣书画,将来成否虽不可知,留此一路,为交易地步,胜于托掮客多矣。我家收藏海外闻名,亦不负数十年搜罗勤苦矣。
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第83号〔51〕
由此可见,顾文彬对与日本书画收藏家和古董商直接交流,不仅抱持支持态度,甚至可说是在主动构建面向海外的收藏流通机制。他清醒地意识到过云楼之所以为外人所仰,正因数十年间对书画珍品的持续投入,今之销售,不但无损名声,反可彰显其收藏之精。
(五)从顾氏家族到顾氏家族的书画收集朋友圈
更值得注意的是,冈田一行的拜访在三月中旬已不再局限于顾承一人,而是迅速辐射至顾氏家族其他重要成员。三月十七日上午,前出顾承的族叔顾淇与其兄顾锡焘(号鉴亭)专程造访冈田,请其为家属诊病。下午,冈田便赴顾鉴亭宅邸施诊,并受到隆重款待:
午后造顾鉴亭馆,宾客咸集,供应至恳。笔话了,展观数幅书画。又各位出金扇数握,请余书。(中略)今日斋中所观:董思翁争座位卷(草字)、邱园水墨山水、刘石庵书幅、毛际可米法,余数幅不记,遂辞。
三月十七日〔52〕
从日记内容可知,此次拜访已从诊病延伸至书画赏鉴与墨迹交流,并留下若干扇面书法,尤其是董其昌的《争座位帖》、刘墉(石庵)的书幅等名品出现,表明顾鉴亭亦为书画藏家,其收藏水准不亚于顾文彬一房。此类交流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冈田与顾家之间的文化纽带,也揭示出医疗行为作为文化亲近与信任构建机制的一部分,在推动艺术品交易和收藏知识传播方面起到了隐性但关键的作用。
三月十八日,冈田拜访了曾在长崎结识的苏州文人蒋子宾,至其私邸中笔谈论艺,继而与其父子偕往“品仙园”品茗宴饮,畅叙情谊。当日,冈田还致书顾承,恳请再度出借十二日于过云楼赏画时未能详观之罗饭牛(即清乾隆时书画家罗牧,字饭牛)山水巨幅。顾承旋即复信,允其所请,使冈田得以细赏此作。〔53〕
三月十九日,冈田在苏州书画家徐耕园引荐并陪同下,偕松浦共赴李嘉福宅第拜访。李氏为清中期吴门画坛名宿,艺术影响深远。是日宾主展卷观画之余,复就清末书画名家事迹进行笔谈,谈及清人江大来(即江稼圃,名泰交,字大来,生卒年不详)、书法巨擘何绍基诸人,冈田尤推崇江氏在日绘事之成就,亦对何氏书艺深致赞赏。当日李氏亦出所藏书画展观,冈田在日记中赞叹为“神品”〔54〕,足证其对李氏收藏及鉴赏之评价甚高。是次会晤,不仅拓展了冈田在苏之交游范围,亦加深其对清代中后期文人画流变及其艺术传承谱系之理解。
三月二十日,冈田偕同松浦,造访江稼圃同族后裔江子山,并与之笔谈。江子山早岁亦曾寄寓过云楼,逾一年之久,于顾氏家中习书画、观藏品,亲炙顾文彬父子之鉴藏经验,亦为熟稔顾氏收藏体系者之一。〔55〕是日晚间,冈田再度与顾承相见,继十二日初会后时隔八日,顾氏身体方痊,仍觉羸弱,然两人相对倾谈,依旧言笑晤畅。笔谈之际,顾承特向冈田提及,希望松浦亦能如冈田一般,题墨留迹于坡仙琴馆,以为纪念。此举不仅显现顾氏对冈田、松浦两人艺业之赏识,亦透露其欲借海外名家墨迹,丰富馆藏之用心。
(顾)永寿先生大画未经拜读,请赐一观。去年赤城先生到吴门,过琴室,求他作画数幅,人々称赞。
(篁)永寿所画固无法度,现有所作之扇,请先生之公评。
(顾)永寿画法与大涤子(石涛)相近。篁老以为如何?
(篁)余曰:“已经先生之公评,永寿之画自今生颜色。”
三月二十日〔56〕
三月二十二日,冈田与松浦将启程离苏,临行之际,特往顾承寓所辞行。是日两人笔谈所及,颇多文化交流之语。顾承盛赞东瀛刻书技艺之精,冈田则详述日本人研读汉籍时所采取之音读、训读二法。此番对话,既表现彼此间学术修养之互通,亦映现中日间古籍受容方式之差异。顾承原欲于次日午后设宴饯行,然冈田告知,翌日早已约定与王正帆同游虎丘,顾氏遂提议改设于晚间。不料该晚二人已应蒋子宾之邀,另有聚会,二十二日之日程遂告排满。然而,念及顾承情谊殷勤,冈田终决意将启程之日推延一日,允准于二十三日晚应宴,以酬东道之谊。〔57〕当日午后,冈田再度赴怡园坡仙琴室,观赏过云楼所藏书画,所见珍品录于日记中如下:
坡仙琴室书画再所观:倪元璐水墨山水、文嘉万山叠翠图、傅山五律诗幅、沈石田山水(款曰:“弘治甲寅秋八月”,沈周临痴道人笔意)、杨文総(“骢”字之误?)山水(落款五言二句:吉州杨文總[骢])、杨烈荐书幅、刘藻书幅、颜峄山水,此外明清名家金笺一百面。
三月二十二日〔58〕
是次再观,可谓冈田苏州之行对顾氏收藏系统所作最详尽之记录,不仅展现其对书画之精审眼力,亦为后人研究过云楼藏品在近代中日书画交流中的具体形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冈田一行在苏行程中,除与顾氏家族密切往来外,亦得以与顾氏书画收藏圈友人广泛接触,其中苏州名门潘氏后裔潘祖荫(字东镛,号伯寅、东园等,1830—1890)亦参与其间。据冈田日记所载,潘氏或因从顾家耳闻其名,于三月二十四日遣人致书相邀,款词殷切。书中并随附其祖父潘世恩、父潘曾绶(1810—1883)、伯父潘曾沂(1792—1852,诗人、收藏家兼医学家)所编诗集、年谱与折扇若干,以表礼遇。
接信后冈田即赴潘宅谢谒,并回赠江户末期著名汉诗人赖山阳(名襄,字子成,号山阳、三十六峰外史,1781—1832)诗钞及做工精致的日本产美浓纸。宾主间亲切交谈,并于庭院设宴款待。酒酣之际,顾承遣人至潘府迎请冈田赴宴,众人遂告辞而往。当晚之宴设于过云楼,顾氏家族亲友与苏州文士咸集于此,席间诗酒唱酬,以文会友。众人纷纷挥毫题赠诗作,以资纪念(图9-7)。宴罢返旅馆,仍有苏州士人尾随送行,冈田亦当场挥毫答谢。是夜,冈田即与徐耕园同行,较松浦与汤韵梅先行离馆,搭乘轮船赴上海。〔59〕三月二十九日,冈田复抵上海,遂造访旧识书画家兼中医钱子琴,追叙长崎旧谊。钱氏特为冈田所撰《沪吴日记》作序,并及时交付,使之得以携归。〔60〕此后,钱子琴与另一位赴日清人书画家王冶梅(名寅,号冶梅,1831—1892)一起,于明治十年(1877)十月因东本愿寺赴沪传教而赴华的僧侣书法家北方心泉交好。其后钱氏又于明治十二年(1879)出任清廷驻长崎总领事,驻节多年,与冈田间之书画诗文往还未曾稍歇。〔61〕
图9-7 冈田篁所《沪吴日记》(上)中以顾承为首的苏州文人赠送给冈田篁所的汉诗
冈田篁所在华期间,游历了上海、苏州及其周边诸地,凡所至之处,皆借由笔谈与文人和书画收藏家、古董商及中医等展开交流,其在长崎所结交之江浙籍清人书画家诸友,不仅为其牵线引荐,亦成为其深化了解中国艺术文化之桥梁,其中尤以与顾文彬家族及潘世恩家族来往密切,更显其在苏州艺文圈中所获之重视与信任。一行人在饱览江南风物、尽享文会佳酿后,遂于明治五年(1872)四月十六日启程返归长崎。
结 语
综上所述,笔者推知顾氏父子一方面将藏品售予日本书画家,亦通过赴日书画家之手购藏日本古刹所藏唐代写经和珍稀善本,充实过云楼的庋藏。另一方面,他们与冈田等人之间在医疗及书画鉴藏和交易基础上建立了双向的文化交流关系,体现出晚清时期顾氏家族对海外艺术市场的高度关注与深度参与。
正如鹤田武良、大庭修、松浦章、马成芬等学者的研究所示,早在江户末期中国商人即已通过长崎这一“窗口”销售书画刻帖和善本书籍,与长崎汉学界和南画界形成了密切的人际网络,在江户末期的日本掀起了一波中国文人画收集和研究热。〔62〕这一跨国艺术交流格局为清末以降来自宫廷和民间的优质文物流入日本提供了深厚的社会文化受容背景,顾文彬父子与日本书画家和古董商之间的交往,正是在这一更广阔的历史脉络中展开。
图12 晚年的顾文彬与孙子顾麟士 引自苏州博物馆(陈瑞近)《烟云四合: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图录
图13 过云楼第三代主人顾麟士 引自苏州博物馆(陈瑞近)《烟云四合: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图录
图14 顾麟士的书法作品 引自苏州博物馆(陈瑞近)《烟云四合: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图录
图15 顾麟士的绘画作品 引自苏州博物馆(陈瑞近)《烟云四合: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图录
顾氏所累积的家族收藏传统与书画鉴藏眼光由顾麟士继承并发展(图12—图15),同时他也延续了与日本汉学家与书画家的亲密交流网络。清末民初,顾麟士常在怡园的坡仙琴馆主持“怡园画社”雅集,与吴昌硕(1844—1927)、郑孝胥(1860—1938)、罗振玉(1866—1940)、山本竟山(1863—1934)、长尾雨山(1864—1942)、岛田翰(1879—1915)等人展开交流,过云楼由此成为清末中日文人艺术交往之重镇(图16—图17)。
图16 参加1919年在苏州怡园坡仙琴馆举办的怡园琴会的成员,成员之一的周庆云(号梦坡)是上海的实业家,后移居苏州,在此地经常举办诗社活动,书画鉴藏家长尾雨山亦是诗社成员。引自苏州博物馆(陈瑞近)《烟云四合: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图录
图17 吴昌硕撰写的《怡园会琴记》 引自苏州博物馆(陈瑞近)《烟云四合: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图录
值得关注的是,顾麟士编纂的《过云楼·续书画记》中,画类已无《安晚册》与《达摩面壁图》记载,从该书出版在1927年这点来判断,二者流出时间应在清末民初,而非抗战时期。宫崎法子教授曾考证指出:《安晚册》由篆刻家桑名铁城在清末赴华游学时购得,后因经济原因转让给住友宽一(1896—1956)〔63〕,终成住友中国书画收藏之翘楚。然就目前所见史料,桑名与顾氏家族并无直接交集,其购藏渠道尚未明确。〔64〕至于石溪《达摩面壁图》则经由另一路径流入日本,相关传承过程仍存诸多未解之谜。从以上熟悉过云楼收藏的金邠和王克三等赴日清人书画家在日的活动踪迹,以及在冈田之前已有数位日本书画家到访过云楼等来看,笔者推测,流入日本的过云楼旧藏当不止上述两件。因此,如何厘清这些过云楼旧藏的流通路径及具体牵线人,仍为当下研究的重要课题。未来笔者将进一步结合中日两国的文献、书简、展览资料及藏品档案,开展跨国的系统考察,以期重构清末民初过云楼收藏跨境流动的全貌与机制。(鸣谢:本文曾于2024年11月29日,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由村上卫教授主持的共同研究班“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再定位”例会上作口头报告。蒙日本实践女子大学名誉教授宫崎法子先生与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吴孟晋先生不吝赐教;泉屋博古馆京都馆亦慨然提供所藏中国绘画图版以资参阅,谨于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注释:
〔2〕关于该展,详见以下文献及新闻报道:李军《顾氏过云楼藏书曾拟售让考——兼论过云楼藏书的流散问题》,《烟云四合: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第46—71页;南京图书馆《霞晖映世 源远流长——百年“过云楼”古籍书画精品合璧展》图录,凤凰出版社2023年版;刘静妍文,顾炜、王曦摄《过云楼旧藏古籍书画精品合璧展出,北宋拓<定武兰亭>首次公开亮相》,2023年8月25日,现代快报网(https://news.qq.com/rain/a/20230825A09LPZ00);王峰《深度挖掘:50件国宝见证江南文脉传承》,2023年8月26日,光明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5253210859867519&wfr=spider&for=pc);《霞晖映世 源远流长——百年“过云楼”古籍书画精品合璧展》,2023年8月29日,雅昌艺术网(https://news.artron.net/20230829/n1124523.html)。
〔3〕陈诗悦《吴门特展之后走进苏州博物馆再品“顾氏过云楼”》,2016年12月11日,澎湃新闻(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77822);王亮《吴中雅集,名流写真:过云楼顾氏与光绪初年吴门真率会》,《典藏·古美术》第36卷:典藏专辑2017年3月(中国版3月号);拈花一笑《过云楼主人顾文彬:烟云过眼,风雅相传》,《书香上海》2022年8月18日。
〔4〕关于过云楼旧藏与日本的关系,参照以下主要先行研究:実方葉子《住友コレクションにみる中国絵画鑑賞と収集の歴史 資料編》,《泉屋博古館紀要》2007年第23号,第11―35页;《「安晩帖」をめぐって—日本における八大山人の受容と鑑賞》,関西中国書画コレクション研究会編《関西中国書画コレクションの過去と未来: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報告書》,2012年电子版,第120—127页;[日] 宫崎法子文,汪莹译《八大山人的甲戌年》,《紫禁城》2014年第7期;[日] 宫崎法子著,范丽雅译《关于桑名铁城的访华与<安晚册>的东传日本》,《中国书画》2024年第1期。
〔5〕关于顾文彬家族的收藏活动、藏品的形成及其特征,参照以下文献:陶大珉《从过云楼到怡园:顾氏书画鉴藏及其艺术交往》,樊波主编《美术学研究》第1辑,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2—471页;唐乃彦《百年过云楼:清顾文彬的收藏及其后人书画艺术》,《荣宝斋》2015年第6期;李军《苏州顾氏及过云楼收藏》,《中国书画》2017年第2期;孙庆《苏州碑刻博物馆藏顾氏<过云楼藏帖>》,《烟云四合: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第72—85页;沈慧瑛《解读<过云楼家书>》,《档案与建设》2017年第4期;沈慧瑛《江南收藏世家过云楼》,古吴轩出版社2021年版;范金民《官宦生涯与书画赏鉴:顾文彬过云楼的收藏》,《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阚红柳《从<顾文彬日记>看晚清琉璃厂书画文玩交易》,《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冯贤亮《太平天国战争后江南士绅的官缺候选、家族重建与文化追求:以同治九年顾文彬的家书为中心》,《清史研究》2023年第1期;艾俊川《<过云楼书画记>的学术追求》《顾道台的十万雪花银》《过云楼的书画生意》《现存<祭黄几道文>卷并非王世贞旧藏》,《E考据故事集:从清初到民国》,中华书局2023年版,第102—154页;姚凯琳《过云楼碑帖收藏概览》,《西泠艺丛》2024年第10期。
〔6〕[清] 顾文彬、孔广陶著,柳向春校点《过云楼书画记·岳雪楼书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页(该书引用页码均依据此版本,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以下同)。
〔7〕[民国] 顾麟士撰《过云楼·续书画记》(校勘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自叙。
〔8〕参见范金民《官宦生涯与书画赏鉴:顾文彬过云楼的收藏》,第16—34页;阚红柳《从<顾文彬日记>看晚清琉璃厂书画文玩交易》,《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艾俊川《顾道台的十万雪花银》《过云楼的书画生意》,《E考据故事集:从清初到民国》,第118—139页。
〔9〕关于顾文彬辞官后的致仕生活,参照以下文献:沈慧瑛《从<过云楼日记>看晚清士绅生活图景》,《档案与建设》2015年第8期;王亮《过云楼顾氏与光绪初年吴门真率会》,《烟云四合: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第100—115页;范金民《晚清江南士大夫的致仕生涯:从顾文彬为中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10〕[清] 顾文彬著,苏州市档案局(馆)、苏州市过云楼文化研究会编《过云楼日记》(点校本),文汇出版社2015年版,第488页。此外,《过云楼日记》及以下引用的《过云楼家书》年月日记载是旧历。
〔11〕同上,第546页。
〔12〕陶大珉《过云楼到怡园:顾氏书画鉴藏及其艺文交往》,樊波主编《美术学研究》第1辑,第432—434页。
〔13〕关于这点,笔者参照了同上论文第424—438页的内容。
〔14〕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请教江西美术出版社北京分社殷士元先生、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朱万章先生及中国美术学院冯春术教授,三位同人不吝赐教,提供了宝贵意见,谨此致谢(据2025年5月6日笔者与三位的微信通信记录)。
〔15〕[清] 顾文彬著,苏州市档案局(馆)、苏州市过云楼文化研究会编《过云楼家书》(点校本),文汇出版社2016年版,第52页。
〔16〕同上,第53页。
〔17〕同上,第57页。
〔18〕同上,第59页。
〔19〕[清] 顾文彬著,苏州市档案局(馆)、苏州市过云楼文化研究会编《过云楼日记》(点校本),第168页。
〔20〕[清] 顾文彬著,苏州市档案局(馆)、苏州市过云楼文化研究会编《过云楼家书》(点校本),第173页。
〔21〕同上,第131页。
〔22〕[清] 顾文彬、孔广陶撰,柳向春校点《过云楼书画记》卷第五,画类五,第166页。
〔23〕[日] 鶴田武良《金邠について—来舶画人研究》,《美術研究》第314号,1980年9月,第26—37页;[日]町泉寿郎《日本に伝存した西魏写本『菩薩処胎経』を巡る日中の人々》,《東アジア文化環流》第2卷第1号,2009年1月,第1—22页;《〔資料紹介〕養鸕徹定と金嘉穂の明治四年、長崎における筆談記録》,《日本漢文学研究》第4号,2009年3月,第107—130页。
〔24〕松翁道人抄录《瓊浦筆談》,手稿本,明治九年(1876)十二月,8ウ—10ウ。虽然古贺十二郎《長崎画史彙伝》(长崎:大正堂书店1983年版)载金邠“赴春德寺拜访铁翁禅师,尝试与其笔谈”,但未见相关笔谈记录,故目前所见金邠与日本学者交流之最早文献,应为《琼浦笔谈》。笔谈后由彻定的弟子抄录并加注,笔者所阅为明治九年抄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室藏),非原始手稿。
〔25〕[日] 鶴田武良《金邠について—来舶画人研究》《王寅について—来舶画人研究二》,《美術研究》第314号,1980年9月,第26—37页;第319号,1982年3月,第1—11页;《陳逸舟と陳子逸—来舶画人研究四》、《王克三と徐雨亭—来舶画人研究六》,《國華》第1044号,1981年8月,第34—41页;第1070号,1984年1月,第20—31页。
〔26〕陈捷《岡田篁所の『滬呉日記』について》,《日本女子大学紀要 人間社会学部》第11号,2000年,第231—245页;《明治前期日中学術交流の研究—清国駐日公使館の文化活動》,东京汲古书院2005年版,第10—13页,第124页,第214—217页;《一八七〇~八〇年代における中国書画家の日本遊歴について》,《中国—社会と文化》第24号,2009年7月,第161—178页。
〔27〕笔者查阅了以下陈捷、吴孟晋及西上实近年有关赴日清人书画家与日本汉学家及书画收藏家交流的若干论文,均未见再有对《沪吴日记》的引用或深入论述。西上実《王治梅と森琴石—近代文人画家と銅版出版事業の関わりについて》,西上実編《中国近代绘画与日本:特別展覧会》,京都国立博物馆2012年版,第243—252页;吴孟晋、陈捷《森琴石ゆかりの中国書画および書簡資料について—来舶清人との交流を中心に》,《京都国立博物館学叢》第44号,2022年6月,第79—108页;吴孟晋《交友と協業のコレクション─野﨑家と森家にある来舶清人の書画について》,関西中国書画コレクション研究会編《中国書画コレクションの時空:関西中国書画コレクション研究会設立10周年記念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報告書》,2022年电子版,第139—152页;《森琴石ゆかりの来舶清人の動向について》,重田みち編《「日本の伝統文化」を問い直す》,京都临川书店2024年版,第439—457页。
〔28〕梁永宣《清末金德鉴与日本冈田篁所的学术交流》,《中华医史杂志》2004年第34卷第3期;梁永宣、真誠柳《日中医学交流史(33)明治初·清末の医学交流—岡田篁所と中国医家の筆談録》,《日中医学》第22卷第4号,2007年11月,第34—37页。
〔29〕冈田在日记中多以其号“骏叔”或“乐泉”,本文为区别冈田与顾承及顾氏家族其他成员之间的笔谈记录混淆,特将其名统一标注为“顾”。
〔30〕该日记后由冈田之子整理,于明治二十三年(1890)12月出版,年月日记载是西历。笔者所阅为内阁文库藏本,非手稿本。本文引用页码均取依据此版本,引用之际,日记中原有着重号省略,日本汉字均改为简体字。[日] 冈田篁所《沪吴日記》(上),长崎私家版,明治二十三年12月,第6叶左。
〔31〕同上,第11叶左。
〔32〕[日] 冈田篁所《沪吴日記》(下),第4叶左—5叶左。
〔33〕同上,第6叶左—7叶左。冈田在笔谈中多次称金邠受聘尾州藩乃其举荐之功,但在《琼浦笔谈》中金邠对此并未着一词,颇有可能是冈田为结交包括顾氏家族在内的苏州人士而有所夸张。又如冈田称金邠将于来年秋季归国,实则据顾文彬家书及日记所载,金邠于当年5月即返沪定居,或许是远在长崎的冈田并不知晓藩校人事变动之故。
〔34〕[清] 顾文彬著,苏州市档案局(馆)、苏州市过云楼文化研究会编《过云楼家书》(点校本),第5页。
〔35〕同上,第45页。
〔36〕同上,第47—48、51、55、62、73— 76、230页。
〔37〕同上,第230页。
〔38〕[日] 冈田篁所《沪吴日記》(下),第35叶左。
〔39〕[清] 顾文彬著,苏州市档案局(馆)、苏州市过云楼文化研究会编《过云楼日记》(点校本),第184—185页。
〔40〕同上,第189页。
〔41〕[清] 顾文彬著,苏州市档案局(馆)、苏州市过云楼文化研究会编《过云楼家书》(点校本),第240页。不过,查《过云楼书画记》及《过云楼·续书画记》,皆未见《福田经》著录,今亦不知其流传去向。
〔42〕同上,第242页。
〔43〕同上,第249页。
〔44〕[清] 顾文彬、孔广陶撰,柳向春校点《过云楼书画记》,第23页。实则如以下论文所考,今藏于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旧藏于养鸬彻定之《华严经疏》断简,实非经卷本体,而为对玄奘所译《摄大乘论无性释》之注疏文本。顾文彬旧藏之《续华严经疏》断简亦属此类,并非经文本体,且过云楼所藏版本实为书道博物馆本之连续篇。佐藤厚《「撰者不詳「『摂大乗論無性釈』への注釈書」断簡(1):養鸕徹定旧蔵『華厳経疏』の実態:書道博物館所蔵》;《「撰者不詳「『摂大乗論無性釈』への注釈書」断簡(2):養鸕徹定旧蔵『華厳経疏』の実態:顧文彬旧蔵断簡》,《専修人文論集》第101号,2017年3月,第283—307页;第102号,2018年3月,第277—308页。
〔45〕此笔谈出自 [日] 鶴田武良《金邠について—来舶画人研究》(《美術研究》第314号,1980年9月)论文中第140页的《金邠·村瀬美香筆談書巻読解》,现代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
〔46〕虽然金邠自光绪五年(1879)后不复见于顾文彬日记,卒年亦无确考,然并不意味着其与顾氏家族自此断绝往来。依据1915年金邠赠长联予吴昌硕,吴为其《墨竹》题诗等交游事迹可知,彼时金邠尚与吴氏保持文墨往来。鉴于金邠与顾文彬父子之间有书画交流,吴昌硕与顾麟士亦有深交,笔者推测金邠应卒于民国年间,其与顾氏家族书画交往当延续至顾麟士一代。参照 [清] 顾文彬著,苏州市档案局(馆)、苏州市过云楼文化研究会编《过云楼日记》(点校本),第192页,第267页,第347页,第350页,第383—385页,第466页;沈慧瑛《金嘉禾名字号及籍贯年代考》,《苏州日报》2020年9月26日,第B01版。
〔47〕[日] 冈田篁所《沪吴日記》(下),第6叶左—7叶右。
〔48〕同上,第11叶左—12叶右。
〔49〕许锷,字达夫,号颖叔、瓢隐居士,室名“诗可楼”,苏州人。工诗,嗜酒,善画,尤精楷书。其书法取法于清末著名书家兼学者王文治,传世墨迹有以小楷书写之《倪文贞公传》(《倪元璐花卉图卷》后跋,现藏于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堪称清代小楷书法之佳作。其名屡见于顾文彬日记及家书,顾氏父子时邀其为新购书画题识,交谊颇深。由其频繁出入顾宅、往还密切观之,推测顾氏父子极为推重其学行,或曾延之为家塾师友。
〔50〕[清] 顾文彬著,苏州市档案局(馆)、苏州市过云楼文化研究会编《过云楼家书》(点校本),第144页。
〔51〕同上,第144页。
〔52〕[日] 冈田篁所《沪吴日記》(下),第13叶右。关于苏州江氏家族与过云楼及与长崎南画界的关系,参照唐权《苏州江氏家族来舶清人考:稼圃、芸阁、星畬的生平与赴日经历》,金程宇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24辑,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365—390页。
〔53〕[日] 冈田篁所《沪吴日記》(下),第14叶左。
〔54〕同上,第16叶左—18叶右。
〔55〕同上,第18叶右。
〔56〕同上,第18叶左—19叶右。
〔57〕同上,第21叶左—22叶右。
〔58〕同上,第23叶右—24叶右。
〔59〕同上,第24叶右。
〔60〕同上,第33叶右—34叶左。
〔61〕同上,第27叶右—31叶右。另关于钱子琴滞留长崎的时期及归国后在上海从事书画活动,以及与明治初期日本书画家的交流,参照以下文献。冈田篁所《脩竹楼坐右日記》,鹤田武良《王寅について—来舶画人研究二》,《美術研究》第319号,1982年3月,第78页;島善高(原作),徐寒冬译《钱子琴与明治时期日本文人的交往》,《日语学习与研究》2019年第2期。
〔62〕关于这点除了前揭注〔25〕鹤田氏论文以外,亦可参照以下文献。大庭脩《江戸時代に舶載された法帖の研究》,《書学書道史研究》第8号,1998年9月,第3—27页;松浦章《長崎来航唐船主による書法受容の一形態》,《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第53号,2020年4月,第A61—A82页;松浦章、许浩《赴日清人书法与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书法的接受》,《故宫博物院院刊》2024年第6期;卞凤奎、马成芬《江户时代中国法帖东传日本之研究》,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3年版。
〔63〕[日] 川边雄大《北方心泉—中国体験と書の受容について》,[日] 小川原正道編《近代日本の仏教学者》,东京庆应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8—100页。
〔64〕[日] 宫崎法子著,范丽雅译《关于桑名铁城的访华与<安晚册>的东传日本》,《中国书画》2024年第1期。
[日] 范丽雅 湖北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共同研究班员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5年第10期
美术观察公众号 25.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