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文共:6752 字
预计阅读时间:18 分钟
《飘》并非一部爱情小说。尽管米切尔以大量笔墨描写爱情。
故事讲述南方庄园千金斯嘉丽,在美国南北战争的烈火中历经背叛、失去、生死,以女性的狡黠与坚韧守护家园,一路寻爱却最终错失。
我特意用了“狡黠”而非“智慧”。
初读这本书,恰是对爱情最好奇的年纪。读完却异常困惑。
它没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粘稠,也没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清淡,更别谈“生死相随,化蝶翩飞”的哀伤。
也许是东方“古典之爱”中毒太深,看不透《飘》的“爱情”。
01. 读者的感觉:真不像爱情
书中男女你来我往的试探与拉扯,在我脑海中早已模糊不清。
印象至深的反倒是,亚特兰大沦陷之夜烧红半边天的大火,以及斯嘉丽逃回塔拉后,站在荒芜的田埂上,攥着萝卜,发出梆硬的誓言:
我向上帝发誓,向上帝发誓,北方佬休想将我打垮。等我熬过这一关,我决不再挨饿。也决不再让我的亲人挨饿!哪怕让我去偷,去抢,去杀人——请上帝为我作证,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再挨饿了!
让这说出这番话的女人去谈一场绵软的恋爱,就像是在看日本导演竹内亮对董明珠的采访:
竹:“最近有没有谈恋爱呢?”
董:“这个话题就很可笑。”
竹:“你没有想过找个老公吗?”
董:“为什么要找老公啊?”
竹:“您这么大公司的老板,应该需要人来安慰您的。”
董:“安慰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是最好的安慰。”
竹:“那您想哭的时候,特别脆弱的时候呢?”
董明珠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斯嘉丽为保住塔拉庄园“不择手段”的时候,也会是面无表情:
抢走妹妹的未婚夫弗兰克;孤身驾马车穿越险境经营木材厂;乃至扯下家中唯一像样的天鹅绒窗帘做成裙子,去监狱引诱瑞德以求资助;更不惜在战后,与昔日敌人北方佬做生意,成为遭人白眼的“皮包客”。
她所有行动的内核,与“爱情”无关,也看不到半分外部“爱情”的影子。她这一路更像是不屈者的生存与征服。
斯嘉丽真的爱艾希礼吗?
她可以一气之下嫁给查尔斯,转而嫁给弗兰克,又嫁给瑞德。她的心理与行动可以始终分离。
这种“爱”更像是骄傲者在受挫后不肯放下的执念,一场必须“扳回一局”的自我证明。艾希礼于她,只是一个符号,一面旗帜,一个她不愿醒来的梦。
斯嘉丽真的爱瑞德吗?
她打扮得性感漂亮去探监,只为获得他的资助拯救木材厂;她在大战中寻找瑞德,只是为了强者的庇护;婚后也还是执着于对艾希礼的幻想。清醒的瑞德总是半分讥诮半分苦涩地说:
你这次带来的商品,包装精美但要价太高。
你几乎让我相信了,可惜你始终学不会把爱意装进眼睛里。
那么,瑞德真的爱斯嘉丽吗?
一个是骄纵任性的坏女孩,一个是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深谙生存法则的“坏小子”。
两人本就是同类。
我们两个都是自私的坏蛋,斯嘉丽,只要我们自己安全、舒服,哪怕整个世界天翻地覆,我们也毫不在乎。
即便米切尔在“南北战争”的大冲突中,无数次将男女主角逼到生死边缘,将二人的拉扯写到极致,字里行间仍难寻暖意。
我比较认同毛姆的说法:
因此,我更愿将《飘》解读为:两个同样强悍、莽撞而自私的灵魂,在战火的熔炉中,耗尽全部力气去学习何为“爱”的故事。
那,就没有爱情了吗?
有的。它只是比这些“爱”来得更晚一些。晚到什么时候呢?
在那句著名的“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之后,
在书本合上之后,
在米切尔不曾写出的续章里。
02. 创作者的角度:真不是爱情
或许,这世上本就没有纯粹的“爱情小说”。
这背后是一个更复杂的命题:爱情是什么?
在此,我们可借助罗伯特·斯滕伯格的“爱情三角理论”作为思考的起点。
完整的爱情由三要素构成:
-
激情:强烈的吸引与渴望,是“我想和你在一起”的本能; -
亲密:温暖信任的情感联结,是“我们在一起很安心”的靠近; -
承诺:短期是“我决定爱你”,长期是“我愿终生守护”,是“我会永远爱你”的理性与责任。
喜欢:如友谊,温暖但无激情和厮守的决心;
迷恋:如一见钟情,热烈却无承诺的根基;
空洞之爱:只剩责任与名分的婚姻;
浪漫之爱:深陷热恋却未必有未来;
伴侣之爱:长久婚姻中的温情与坚守;
愚昧之爱:如闪婚,激情消褪易瓦解;
完美之爱:理论上最稳定理想的爱情形态。
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深刻着对“圆满结局”的执念,天然排斥残缺,也羞于直面“欲爱”。压抑、扭曲、理想化。
大多数故事,纵使命运百般拨弄,也要奔向婚姻与承诺而去。因为,有了“承诺”的盖章,激情可晋升浪漫;否则,就是失德。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结局是圆满的。演得不亦乐乎,挺像那么回事儿。
现实中,倒过来。
饮食男女,饭桌上谈的、被窝里想的、挤眉弄眼八卦的、跃跃欲试想付诸实践的,可都是“激情”。
幸而《金》和“三言二拍”屡禁不绝,我们才能在市井烟火缭绕中,一窥前人的真实,照照我们自己。
为什么清代艳情小说,远不如明代的敞亮、流畅、香艳、文雅?只因大脑被阉割,再辨不清“情爱”的层次,笔下只剩动物性的宣泄,却失了人性的明暗冷热。
低级的写作,为“性”写性;高级的写作,为“人”写性。
将“性”换作“爱情”,这句话依然成立。
明史看胡金铨,清史艳情看李翰祥,古典影视的高峰
主流文学素来背负“文以载道”的使命,而文学的本质终究是“人学”。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
于是,当代很少有人写爱情了,因为不好写,甚至不会写。
写真了,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落下;写假了,读者翻白眼“当我是三岁小孩?”
文学与现实之间,总隔着一层花里胡哨的窗花。
但我们的文学源头并非如此。它们曾足够真实,也足够犀利。
《诗》三百,全是活生生的“人”。
有《关雎》的纯粹迷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也有《卫风·氓》的爱情全程:从“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羞涩开端,到“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痛彻清醒,终至“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决绝告别——短短二百四十字,先人写得清醒而凛冽。
再后来,刘兰芝投水,祝英台跳坟,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千百年过去,我们在爱情的认知上,似乎并未走出多远。
崔莺莺与张生月夜私会,结局极可能是:
张生未必能轻易高中状元(参照任何朝代的科举录取率便知),即便有幸得中,也绝无可能回头迎娶“门户不严”的崔家女。至于崔莺莺的命运……
所以,唐人元稹的《莺莺传》,实在比明人王实甫的《西厢记》高出不止一层。
在元稹笔下,张生赴京赶考后,便主动遗弃了崔莺莺,并称她为“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尤物”。当他在京城另娶,崔莺莺也已他嫁后,此人以“表哥”身份求见,企图再续前缘,被崔莺莺以诗严词拒绝:
“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
这,就是高级的文学:
不灌迷魂汤,只喂药。一个伟大的时代,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真实,容纳这样的高级。
相比之下,西方文学在这一点上,头脑清醒一些。
这得益于他们老实地继承了文学遗产。
希腊悲剧里的爱情,从不浪漫。它常被置于命运、伦理与神意的困局之中,展现出毁灭性的力量。
在《美狄亚》中,极致的爱催生出极致的恨,使她手刃亲生骨肉;《希波吕托斯》里,爱神降下的诅咒引发继母对继子的不伦之恋,最终导致死亡;而《安提戈涅》则将亲情之爱与城邦律法置于不可调和的冲突之中。
这些故事共同指向:在宏大的命运与神意面前,爱情非但不是救赎,反而常常是引爆悲剧的导火索,将人推向疯狂与毁灭的深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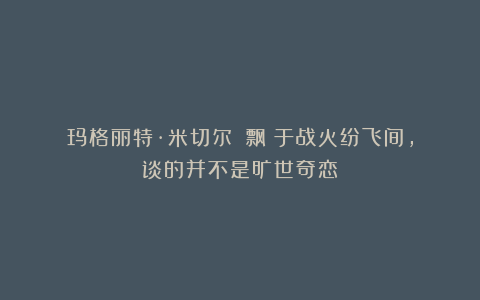
此后的西方爱情小说,大多沿袭这一内核,并为它注入不同时代的精气神。
于是便有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这些作品中的爱情,几乎写尽了斯滕伯格理论中“完美之爱”之外的所有形态。
“王子与公主从此幸福生活”的“完美之爱”不过是迪士尼制造的工业糖精。未经粉饰的民间寓言,远比我们童年所读的更加暗黑、残酷。
总结一句,或许有些偏见:
我们的“爱情”试图让人沉睡;而他们的,却要将人叫醒。
因此,如果只怀着读“爱情”的心去读西方“爱情”小说,虽无不可,却终究看轻了作者的野心与作品的深度。
正如《飘》。
米切尔治史十年,增删数次,毕生只得此一书。若我们只将它视作一段爱情传奇,她一定会很难过。这好比读《红楼梦》,若只懂宝黛的痴怨,虽无不可,却会错失经典的根本。
不以爱情解读经典“爱情小说”,是读者的自觉。
我试图描绘的是文明崩溃和重建的情景。……其中的人物,无论是好是坏,都必须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框架内行动。
因此,读《飘》得尽快舔掉“爱情”这层糖衣,尝一尝底下真实的苦味。
03. 到底怎么读?在历史的天空下
从米切尔的创作过程来看,《飘》更接近一部历史札记或者社会学文本。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部生动有趣的“美国内战小史”来读。
请注意,是“小史”而非“野史”。
米切尔以治史之严,写了这本小说。
《飘》耗时十年,绝不止在写字机前的敲敲打打。
她完成了关于南北战争“口述史”的系统性搜集与整理。
我写的故事,是我用了半生时间,听关于“战争”和“战后”的故事所积累起来的。
所有枯燥繁琐的工作,都是为了捕捉那代人的“语气、思维和说话方式”,以鲜活的个体记忆,重现时代氛围,还原出有血有肉的历史。
这正是社会史学家的工作方法。任何官方档案都无法提供这些珍贵的细节。
与此同时,她通过海量文献研读,建立起庞大的私人史料库。
《亚特兰大宪政报》从内战前到重建时期的合订本,大量南方将领和政要的回忆录,普通士兵和女性的日记与信件,以及历史专著等都是米切尔必读的资料。
她遗留的手稿与研究笔记中,记录了大量有关内战时期军衔、军服、武器、军乐的信息,甚至精确到不同战役中的行军速度;
还手绘了亚特兰大旧城地图,标记出人物可能行走的路线和重要地标的位置,以确保空间信息的准确性;
剪报簿里也全是关于物价、时装、社交公告的片段。
这些厚厚的史料,最终出现在小说中的,却不到十分之一。正是这种严谨的态度,让《飘》中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
斯嘉丽腰围与那个时代紧身衣的极限,都有据可查。
对人物服装的描述可具体到特定的面料产地与染色工艺。
每一次战役、军队的行进路线和伤亡数字,与历史记录严丝合缝。
为确保人物的思维、动机与谈吐都严格契合其出身、阶层与时代背景,她还为每个角色——从南方贵族、北方军官到家奴与投机商——都撰写了详尽的人物小传。
因此,《飘》中的人物,近乎真实的个人,而非助推情节的工具人。
米切尔对历史细节的严谨可见一斑。在给一位历史教授的信中,她写道:
如果我写了一个发生在1864年的故事,那么我有责任确保1864年的人不会在1865年才出现,或者说1865年的话。
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米切尔写了一部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传记体历史著作。就好像《史记》是信史,同时也是伟大的文学经典。
04. 到底怎么读?在个体的困局中
我们还可以把《飘》当作一部“自传体纪录片”来看。
米切尔描写人物近乎“摄影”:斯嘉丽的原型就是她自己,瑞德的原型是她的第一任丈夫,斯嘉丽与瑞德的暴烈情感其实就在说他们那段短暂的婚姻……
米切尔的生平比小说更“小说”。
1939《乱世佳人》首映主创合影:男女主角、米切尔、电影制片人
因此,相较于一般虚构作品,《飘》中人物更血肉饱满,性格更立体鲜明,命运轨迹也更合理切肤。
书里曾令我困惑的“爱情”,如今看来,更接近佛家所说的“三苦”: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
人生一途,得到了也失去了,失去了也得到了。反反复复的“得”与“失”之间,沉沉浮浮,留下痕迹斑斑,串起整个人生。
人皆困于此。
▶︎ 斯嘉丽,困于对“虚幻”的执念。
她执着的,是对艾希礼的幻梦,以及对“塔拉”所象征的、永不回头的旧日时光。
她失去了什么?与瑞德之间真实涌动的爱意,与媚兰坚实温暖的友谊,与父亲和孩子间纯粹的亲情——最终都消散在风里。
所幸,她那浑然天成的“狡黠”,在历经重重苦难之后,终于磨出一丝“智慧”。
这已足够——足够支撑她去践行那句鼓舞自己也鼓舞读者的话: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你,我,她与他,何尝不是斯嘉丽?无论追求什么,不妨沉心自问:这真是我想要的吗?无论失去什么,也别因恐惧而原地哭泣。
▶︎ 艾希礼,困于“旧时代的幻影”。
这位南方的旧日绅士,被困在了一个被炮火摧毁的黄金时代。他是新世界里游魂,看不清前路,也寻不到归途。
他多想活在梦里,可现实却逼着他与贵族的荣光、旧日的秩序、绅士的尊严一一诀别。
他一生都在“避免失去”。可他抱得越紧,失去得越多——独立、尊严、立足之地,皆随风而逝。
我们心里都住着一个艾希礼。骨子里的怯懦,对新秩序的惶惑,对旧我的沉醉,让我们踟蹰于原地,不敢迈步。
艾希礼啊,不如脱下长袍,在泥泞中痛快打滚?当时代剥去你的尊严,能再次拾起它的只有自己。
▶︎ 瑞德,困于“清醒的悲观”掩盖下的“恐惧”。
童年的创伤与世人的冷眼,让瑞德早早学会了自我保全。
他恐惧脆弱,便以玩世不恭作伪装;恐惧失去,便以若即若离来控制;恐惧不被爱,便用冷嘲热讽来试探。
他穿着全副铠甲走入感情的战场。铠甲固然挡住了明枪暗箭,却也冷冰冰地隔断了与他人的真实拥抱。
他与斯嘉丽,一个因恐惧而不敢全力去爱,一个因“狡黠”而操控“爱”,一起写了这出“错位”的情感悲剧。
最终,瑞德深切渴求的爱情和亲情,都化作泡影。
我们心中也住着一个瑞德。蜷缩在坚硬的壳里,听着外界的动静,揣测着他人的心意。明明内心柔软又温柔。
▶︎ 我们的内心,同时住着《飘》的灵魂。
斯嘉丽的生存本能,艾希礼的沉溺过往,白瑞德的清醒悲观,与媚兰那悲悯宽恕的爱……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人格。
如果您正在读《飘》,把可以它当作一场认识自我的“修行”。
“以史为镜,可知得失”。恰好,它也是一部史书。
05. 小说结尾:时间的寓言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米切尔写尽恢宏历史与个体沉浮,最终凝成这“画龙点睛”之句。
它冷冷地不给人答案。
历史与命运也从不给人答案。
斯嘉丽在失去一切后说出这句话,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在彻底领悟“得失乃人生常态”后,依然选择向前的、悲壮、坚韧的生命姿态。
它悲悯地给人破局的机会。
客观时间自有其轨迹,历史长河奔涌向前。
但对于历史中的个人,却未必。个体时间可能是发散的、循环的,甚至是一个令人困守原地的点。
如海德格尔所说:人是“被抛”的存在。
我们无缘无故地被抛入某个时代、某个家庭、某个身体、某个事件,这些初始条件构成了我们无法选择的“事实性”,一种无形的牢笼。
这种牢笼,时空并存。
达利《记忆的永恒》(1931,局部),探讨时间相对性与流动性
若没有外部刻意的参照,我们真的能感受到时间在“向前”吗?或者感受到自己在“随着时间向前”吗?
抑或,只是陷在日复一日的微循环里?或经历着某种螺旋式的起落?又或是被童年的一道伤痕、一段无果的爱恋、一场痛彻的永别……永远困在了某一天甚至某个瞬间?
而米切尔这句“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呈现的正是历史的“大时间观”:
线性,单向,不容置疑地向前。
它提醒我们:每一个个体,无论因何受困,明天都必将到来,并且注定是“新”的一天。
而人,也一定能够破局,跳出“小我”的囚笼,汇入历史奔涌的洪流,义无反顾地,朝明日走去。
只要死不喊停,生就有机会。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