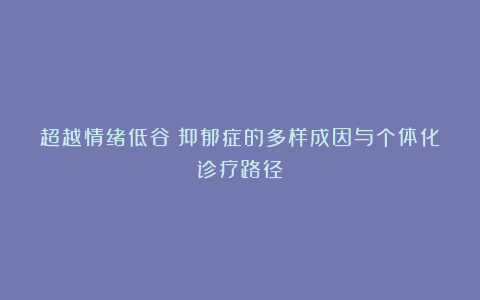抑郁症(Depression)是全球最常见的精神心理疾病之一。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估计显示,全球约有超过3亿人受到抑郁症困扰,在青年和中年人群中,它已成为导致工作能力受限、生活质量下降及自杀的主要健康负担之一。
抑郁症并不是单纯的“心情不好”,而是一种兼具情绪、认知、行为、生理变化的综合性障碍。其典型症状包括:
·情绪低落:持续的悲伤、空虚或易哭泣;
·兴趣或愉快感降低:对以往喜欢的活动失去兴趣;
·思维和注意力下降:难以集中注意、反应变慢;
·睡眠与食欲异常:早醒或嗜睡、暴饮或食欲不振;
·能量不足与自我评价低下:易疲劳、感到无助或内疚;
·严重时出现自伤或自杀意念。
抑郁症的持续时间通常超过两周,并明显影响学习、工作或社交功能。
·性别差异:
女性患病率约为男性的1.5–2倍,这与激素变化、社会角色压力等因素有关。
·年龄分布:
-首发高峰在20–40岁,年轻人群常受学习和职场压力影响;
-老年人则多因躯体疾病、社会孤立等因素诱发。
·特殊人群:
产后抑郁、更年期抑郁、青少年学生抑郁增势明显;长期慢性疾病患者(如糖尿病、肠易激综合征、肿瘤)中发病风险也显著较高。
1.诊断体系
目前临床主要依据《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版(ICD-11)》和《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诊断以症状学评估为核心:
–情绪低落、兴趣缺乏为主症;
–辅助症状(食欲、睡眠、能量、专注、罪疚、自杀意念等)达一定数量与持续时间;
–评估量表: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PHQ-9抑郁症筛查量表、蒙哥马利抑郁量表(MADRS)等常用于量化病情。
2.传统分类方式
临床上目前仍以临床表现为分类依据,如:
–典型(忧郁)型抑郁症:显著情绪低落、早晨加重、体重下降;
–非典型抑郁症:情绪反应性较强、嗜睡嗜食、体重上升;
–焦虑型抑郁:伴强烈焦虑与躯体不适;
–季节性抑郁、产后抑郁、双相抑郁期等。
这些分型主要帮助医生选择抗抑郁药物、确定重症程度,但在病因或机制层面缺乏区分力,因此同样诊断的患者,疗效差异依然巨大。
当下临床治疗以“三大支柱”为核心:
联合方案:如药物+心理干预、药物+经颅磁刺激(rTMS),逐渐成为主流。
尽管现有治疗能帮助多数患者缓解症状,但仍约有30–40%的患者对常规药物反应不佳,被称为“难治性抑郁症”。研究发现,不同患者的抑郁发作并非源自同一种脑化学异常,而是由多种体内机制失衡引起,包括:
·肠道菌群和代谢异常:如色氨酸-犬尿氨酸代谢、短链脂肪酸缺乏、嘌呤/肌苷(inosine)通路紊乱;
·神经可塑性与炎症机制: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BDNF)降低、谷氨酸过度释放、小胶质激活;
·应激-激素系统异常:HPA轴过度活跃导致皮质醇长期升高;
·表观遗传调控与早期创伤记忆的交互。
★ 精准分型诊疗模式
这些结果促使科研界提出一种新方向——基于分子通路与生物标志物的抑郁症多机制分类(biological subtyping of depression)。
通过整合肠道代谢组、血清分子、基因与影像数据,医生可以更精准地判断患者属于哪一类机制主导(如“炎症-代谢型”或“神经可塑性低型”),并选择最可能有效的治疗方式。这种新的“精准分型诊疗模式(Precision Psychiatry)”,正在逐渐改变过去“同病同治”的局限,为抑郁症的个体化治疗打开新的大门。
尽管“情绪低落”是抑郁症最显性的外在表现,但在生物层面,它更像是一个多层系统失衡后的临床终点。现代研究认为,抑郁症不再被视为单一的“神经递质不足”,而是一种由神经网络、代谢-免疫反应、心理应激和遗传易感共同驱动的复杂脑-身综合征。
早期(20世纪后半段)的研究认为,抑郁主要由5-羟色胺(5-HT)等单胺类递质不足引起。然而,长期临床观察发现,不同患者间药物反应高度差异,且一半以上患者伴随代谢、炎症或内分泌异常。这些发现提示:抑郁症的根源在于整个身-脑系统的稳态失衡。
通过整合多组学(基因组、代谢组、神经影像组)与临床数据,研究者逐渐将抑郁的核心生理机制划分为三大根源性模块:
这些模块并非互相排斥,而是如同三条交织的支流,在不同个体中各自占主导比例。
同一患者可能同时存在“菌群失衡+应激高皮质醇”或“低可塑性+炎症反应”等复合机制。
临床诊断正逐步从单一症状学转向“整合机制-标志物分层诊断”,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治疗精准度,也为未来的抗抑郁药物研发提供了更清晰的靶点方向。
如果说抑郁症是一场脑与身体间沟通失序的“系统性危机”,那么肠道菌群与机体代谢的失衡,就是这场危机最重要的触发点之一。
研究表明,约有45%–55%的抑郁症患者存在明显的代谢与肠道生态异常,其中至少三分之一可被归入“肠-菌-脑代谢轴异常(Gut–Microbiota–Brain Axis Dysfunction)”范畴。
人体肠道中含有超过10¹⁴个微生物,这些微生物通过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嘌呤、色氨酸代谢物等)影响神经递质合成、免疫炎症信号及表观遗传调控。这些信号通过迷走神经-内分泌-免疫通道传递到脑内,调节情绪、认知与应激反应。
以下为五种主要的代谢-菌群通路亚型总结:
·肠-脑化学沟通障碍
肠道产生超过90%的5-HT(血清素)。当炎症上调IDO1酶时,色氨酸被“改道”进入犬尿氨酸通路,减少5-HT合成,形成“情绪原料短缺”。
·代谢与炎症的双向循环
高脂饮食、肠屏障破坏等因素导致脂多糖(LPS)进入血液,激活全身炎症,炎症因子又可进入脑内,引发神经炎症。
·表观遗传重塑
研究发现,肌苷缺乏可激活脑内EZH2-H3K27me3甲基化通路,抑制神经可塑性基因表达,形成“情绪封闭状态”。
·能量与神经可塑性枢纽
短链脂肪酸(SCFA)缺乏时,神经可塑性相关基因表达下降,导致神经可塑性降低和精神疲乏。
临床意义:不同代谢-菌群亚型对治疗方式的响应差异,正推动“精准抑郁干预模型(Precision Depression Therapy)”的形成。
小结
情绪并不仅存在于脑中,也“滋养”于肠道与代谢之间。
从肌苷到丁酸盐,从犬尿氨酸到胆汁酸,每一种代谢产物都是情绪的化学语言。通过识别这些语言,我们或许能够真正理解“抑郁”的物质根源,并为不同患者提供机制匹配、靶向精准的治疗方案。
该类型约占全部抑郁症患者的25–30%,主要表现为情绪迟钝、思维缓慢、注意力不集中,其本质是脑网络的活跃度、灵活度与突触可塑性下降,使大脑进入一种“低功率运转模式”。
主要涉及三条相互交织的通路:
1.突触可塑性与神经营养线路
突触可塑性与神经营养线路(BDNF–TrkB–CREB轴)核心是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的减少,导致神经元突触重塑能力下降。多项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海马体积缩小,而运动和经颅磁刺激等治疗可提高BDNF水平。
2.谷氨酸和单胺类递质的信号传导系统
不仅是传统的单胺递质(5-HT, 去甲肾上腺素(NE)和多巴胺(DA))失衡,谷氨酸/NMDA受体信号过度活跃导致的神经毒性也至关重要。这解释了为何氯胺酮(NMDA受体拮抗剂)能产生快速抗抑郁效应。
3.神经炎症与胶质细胞调控通路
过度活化的胶质细胞(如小胶质细胞)会释放炎症因子,抑制突触形成,导致神经信号阻断。这一亚型常被误诊为“难治性抑郁”。
临床暗示:当药物反应差而影像显示海马/前额叶功能减退时,应考虑“神经网络低激活型”抑郁。
小结
情绪障碍的本质,不仅是“缺乏快乐”,而是“大脑网络失去灵动与连接”。
通过重启这些沉睡的回路——无论是利用经颅磁刺激、运动、氯胺酮或新型神经调控技术——我们正逐渐把抑郁症从“化学失衡”的旧定义,带回它真正的神经生物学本质。
该类型约占抑郁症患者的20–25%,多见于青年、女性及有童年创伤史者。其主要特征为症状受生活事件诱发,伴明显焦虑与失眠,并表现出应激轴长期高活化和神经内分泌失衡。
人体的应激核心系统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 axis)。在易感个体中,持续应激会导致皮质醇长期分泌过量,使神经元处于“应激中毒”状态,引发海马萎缩、前额叶功能下降和杏仁核过度敏感。
压力可通过多种表观遗传机制(如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等)深刻影响基因的表达模式,在分子层面上改变神经系统的功能,从而在生物学上“刻录”下心理创伤的持久印记。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个体对环境刺激的反应方式,也影响了长期的情绪调节能力。主要受影响的基因包括:
此类型抑郁的治疗是“从心理到分子”的系统重建过程。
重点共识:社会支持也是一种分子疗法,社会连接能反向调节糖皮质激素受体敏感度与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水平。
小结
“情绪受伤”具有生物学记忆。长期的压力与创伤不仅改变心理状态,也能在基因表达与脑结构层面留下可测量的痕迹。这意味着未来的抑郁防治,不只是药物与心理的对话,更是环境-基因-情绪三方共振的整合治疗。
抑郁并非单一疾病,而是一个由代谢、神经、应激等多机制交织形成的异质性综合征。约60–70%的抑郁症患者包含两种机制叠加表现,如“代谢-炎症+神经可塑性低下”或“应激-炎症+肠道菌群失衡”等复合型结构。
精准精神医学(Precision Psychiatry)的兴起,正推动抑郁症诊疗模式的变革。最近,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一项研究利用脑成像和机器学习,将抑郁症分为了六种不同的生物亚型(biotypes),并为其中三种亚型确定了更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为个体化治疗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1.机制导向诊断:通过检测生物标志物,为患者找到主导病理通路。
2.个体化治疗决策:根据分子和组学结果选择特定干预路径。
3.动态疗效监测:追踪生物标志物,实时调整治疗。
4.多组学整合平台:正在全球范围进入临床试点阶段。
抑郁症的未来治疗将不再是“用一种药、治一堆人”,而是“为一个人,设计一整套生物-心理干预方案”。
·近期目标(1–3年):建立标准化生物标志物检测体系;多中心验证分型算法;AI临床辅助诊疗系统试点。
·中期目标(3–5年):实现全组学融合诊断;新型多靶点药物投入临床;分子亚型诊断纳入指南。
·长远目标(5年以后):建立“动态抑郁画像”,实现“在发病前预测,在情绪崩溃前防治”。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人们认识到:
抑郁症不是一种单病,而是多种生物与心理机制的编织体。“精准分型”不只是科研语言,而正在逐步进入临床,为每位患者提供科学可测的机制依据、靶向有效的治疗方案和心理-社会-生物三维整合的康复路径。
这意味着,未来医生不再仅依据情绪描述开药,而是读懂“肠道、神经、基因”的语言,结合精神症状、躯体情况、影响因素、病程特定以及功能缺陷,用数据与机制多维度为患者重新点亮情绪的生理之光。
相关阅读:
肠道菌群检测报告解读——肠道菌群代谢产物包括激素,神经递质等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