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站在一起看风景
我们站着,不说话
就十分美好
你指指远处的山
我看看更远的云
手牵着手
温度在传递
像两棵春天的树
共享着同一片泥土
有时风来了
树叶轻轻相碰
那细碎的声音
落在心底也是暖的
不用确认什么
不用反复描绘明天
当夕阳缓缓西沉
我们的影子依偎在一起
就这样靠着吧
从青春看到白发
皱纹里蓄满时光
眼神依然清澈
当夜色漫过山峦
我们变成剪影
在这永恒的窗口
连星辰都学会了
彼此的诺言
■ 有一种底气,叫做你能行
当乌云把天空压得很低很低
雨点像豆子般砸在额头上
你只是慢慢扶正那把旧伞
把湿透的云彩折好
塞进背包最里层
走着走着 鞋里钻进沙粒
你就坐在路沿
倒出那些硌脚的小石子和抱怨
看见远方的雾墙压过来
反而掏出小本子
画了一扇能推开的窗
不断有人从旁边超车
带起一阵风
你不再踮脚数他们的背影
只是调整自己的呼吸
像山里的老树根
在泥土里默默记着
又扎实地生长了一寸
当陡坡突然横在面前
你拍拍膝盖说:
“不过是要弯腰走的路”
那些硌脚的石阶
不知不觉变成了软垫
浓雾终将成为身后的背景板
现在每一个笨拙的脚印
都在等待某个清晨
蜕变成翅膀的形状
把所有怀疑折成纸飞机
任它们顺着融雪漂走
你站在刚刚解冻的河岸
对着水面倒影
用不大却清晰的声音说:
“嘿,我能行”
■ 如果爱
如果爱是一首诗
我愿是清晨那阵骚动
轻轻碰醒你的睫毛
把热牛奶放在床头
看你揉着眼睛笑
如果爱是一首诗
我愿是午后那截光
从百叶窗溜进来
停在你的衣领上
暖着 又不发烫
如果爱是一首诗
我愿是傍晚那盏灯
守着你翻书的影子
直到夜色漫过窗台
也不熄灭的陪伴
如果爱是一首诗
我愿是半夜那场雨
在你说怕黑的时候
把每滴答声都变成
催眠曲的节拍
如果爱是一首诗
我愿是平凡日子里
你随手就能碰到的
那杯温水 那把伞
那双旧拖鞋
如果爱是一首诗
我愿是你翻开又合上
却始终在床头等待的
那本从不喊累的
沉默的注解
■ 这些年
这些年像一本写坏的账本
数字横七竖八地瘫着
想要合计些什么
手指在计算器上悬空
这些年变成雨天的水洼
踩过去就溅起泥点
新买的布鞋
渐渐长出霉斑点
这些年是半杯冰凉的咖啡
糖块沉在杯底未肯融化
电话号码隔在开头的那一页
后面都是空白
这些年不断在调试琴弦
却始终凑不成曲
他们说该唱支歌了
我张了张嘴未出声
这些年站台总是湿漉漉的
列车带走暖意
我攥着皱巴巴的车票
在长椅上越坐越沉
■ 一碗芝麻粥
瓷碗里漾着灰白的漩涡
芝麻的香浮在雾气之上
像那年冬日 灶台边
母亲搅动着渐渐稠密的光阴
飘进鼻腔的暖意
是记忆深处泛黄的片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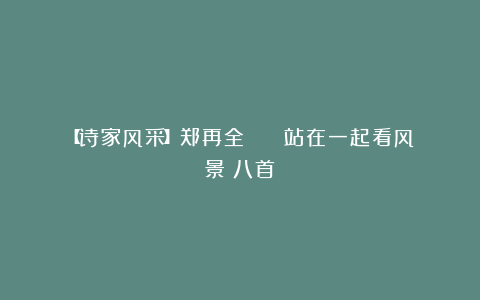
当舌尖触到温润的甜
忽然听见 晨光里
汤勺轻碰着锅沿的叮当
碗底沉积的暗色
是岁月熬出的印记
我尝到霜色爬上鬓角的滋味
尝到被柴火熏暖的时光
在指节间缓缓凝固
这满碗绵密的暖意
分明是融化的月光
带着母亲鬓角星子的微光
把清亮亮的早晨
熬成浓稠的黄昏
当最后一口暖流淌过咽喉
忽然看见 旧厨房里
那个弯腰吹动火苗的身影
正把我的童年
煮成永不散场的晨光
■ 走着
鞋底总在计算些什么
柏油路却越摊越长
我们说起明天
明天就翻过身去
变成泛黄的月份牌
站台与站台互相追逐
地铁卡的滴声逐渐暗哑
有人掏出硬币
有人整理衣领
所有远方都长着
相似的眼睛
梧桐叶突然黄了
某个拐角
你提及多年后的傍晚
话茬轻得像云
我们都没伸手去接
钟声在楼层间传递
书包变作公文包
水泥地长出
新的斑马线
而鞋带依然系着
相同的结
路灯一盏盏亮起
我们——
踩着彼此的影子
走向下一盏
尚未点亮的
路灯
■ 那条小溪
——记村前沙埕嘴小溪
像一匹被风揉皱的绿绸缎
清凌凌的波纹总在轻轻摇晃
水草是溪流深绿的脉搏
在卵石间摇头晃脑打着节拍
那些被童年踩得光滑的鹅卵石
还在老地方做着温热的梦
阳光碎成金灿灿的糖霜时
我们光着身子扎进粼光
变成泥鳅在清凉里穿梭
母亲抡起棒槌的声响
和着知了的鸣叫起起落落
她把泛白的粗布衣衫
在清波里揉成一团云朵
多年后我回到同样的浅滩
溪水仍哼着童年的歌谣
可当水花溅起的刹那
突然看见时光在倒流——
那串奔向远方的脚印
正湿漉漉地退回岸边
卵石硌疼的脚底板
提醒这双脚已习惯皮鞋
我成了带着尘嚣的客人
小溪却用它清凉的舌头
一遍遍舔着我的裤管
像在认领迷路的游魂
水中央那棵老万年青树还在
只是弯腰的弧度又深了几分
如同母亲去年冬天的照片
溪水带走了那么多日夜
却始终冲不走水底
那些星星点点的鹅卵石
它们像散落的纽扣
系着故乡渐渐松开的衣襟
此刻有蒲公英掠过水面
带着我中年的怅然
飘向对岸的油菜花田
而小溪依旧不紧不慢
用它明亮的绸缎
包裹所有归来与远行
当暮色染红潺潺的水声
我突然听懂——
它日夜流淌的不是水
是溶解了悲欢的时光
正在我们共同的血脉里
循环往复地奔涌
■ 包菜
父亲弓着背
在田里忙活了大半年
一亩二分地的包菜
绿汪汪得像片海
那天集市喇叭喊
“包菜三毛二一斤”
父亲蹲在田埂上
卷烟卷了三次才点着
镰刀挥下去的时候
菜叶子溅起青涩的汁
邻居挑着担子来回走
猪圈里传来欢实的哼哧
暮色漫过田垄时
父亲在空地里站成
最后一棵倔强的包菜
深深扎进泥土里
广东诗人(gdsrj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