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天人合一”这一中国传统美学核心理念为切入点,探讨漓江画派在当代语境下对文人山水画艺术理想的承续与转化。研究指出,漓江画派并非对传统的简单模仿,而是在阳太阳、黄独峰等先驱探索的基础上,由黄格胜等人通过系统性艺术实践,将“天人合一”理念从古典哲学命题转化为具有现实指向的创作方法论。以《漓江百里图》《漓江百景图》为代表的大型创作,不仅延续了山水画“以形写神”的美学传统,更通过写生本位、家园意识与大景构图等策略,实现了对自然、人文与个体精神三者关系的当代重构。文章认为,漓江画派的兴起是中国绘画在现代化进程中对本土文化基因的自觉回归,其艺术实践为传统山水精神的当代转化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路径。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与作品解读,系统梳理了该画派在思想传承与艺术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漓江画派;天人合一;山水画传统;黄格胜;写生实践;家园意识
引言
中国山水画自魏晋以降,始终以“天人合一”为根本艺术理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物我交融。这一理念既源于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学观,亦融合了儒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伦理情怀,成为贯穿中国绘画史的核心精神脉络。进入20世纪,随着西方艺术观念的引入与社会结构的剧变,传统文人山水画面临价值重构的挑战。如何在现代性语境中延续“天人合一”的美学理想,成为中国画家必须回应的时代命题。
在此背景下兴起的漓江画派,作为21世纪以来具有广泛影响的地域性绘画群体,其艺术实践呈现出对传统山水精神的深度认同与创造性转化。该画派虽以广西漓江流域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为主要表现对象,但其意义远超地域题材本身,而在于通过系统性的创作探索,重新激活了“天人合一”这一古典命题的当代生命力。从阳太阳、黄独峰等早期探索者,到黄格胜等集大成者,漓江画派逐步建立起一套融合写生实践、家园情怀与宏大叙事的艺术体系,使“天人合一”不再停留于抽象哲思,而成为可感知、可操作的视觉表达。
本文旨在梳理漓江画派对“天人合一”艺术理想的承续路径,分析其如何通过代表作品实现传统理念的当代转化,并探讨这一转化对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启示意义。研究采用艺术史分析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聚焦关键人物与核心作品,力图揭示漓江画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所建构的独特艺术逻辑。
一、历史脉络:从阳太阳、黄独峰到黄格胜的承续链条
漓江画派对“天人合一”理念的承续并非凭空而起,而是建立在几代广西画家持续探索的基础之上。其中,阳太阳与黄独峰作为先驱者,为后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阳太阳(1909–2009)是广西现代美术的奠基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长期致力于融合中西艺术。他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漓江春雨》《象鼻山》等作品,虽采用水墨媒介,但已融入写生观察与光影处理,展现出对自然真实性的追求。阳太阳主张“师造化而抒己意”,强调画家应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表达个人情感。这一立场既延续了文人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传统,又为后来者开辟了写生与创作结合的道路。他笔下的漓江,不仅是视觉对象,更是情感寄托,初步体现出“天人合一”中“情与景会”的美学特征。
黄独峰(1914–1997)则更直接地承接岭南画派“折衷中西”的理念,同时注重传统笔墨的锤炼。他长期在广西写生,作品如《桂山秋色》《漓江渔火》以苍劲的笔法与浓烈的色彩表现南方山水的郁勃生机。黄独峰强调“笔墨当随时代”,主张在传统程式中注入现实感受。他的艺术实践表明,“天人合一”并非静态模仿自然,而是通过笔墨语言实现人与自然的精神对话。其“以气运笔,以情驭墨”的创作观,为漓江画派后来强调“笔墨即心象”提供了重要启示。
至黄格胜(1950– ),这一承续链条达到新的高度。作为阳太阳、黄独峰的学生,黄格胜不仅继承了前辈对写生的重视与对笔墨的钻研,更通过系统性创作与理论建构,使“天人合一”理念在漓江画派中得以“明晰和肯定”。他明确提出“山水即家园”的艺术观,将自然景观与人文记忆、个体生命体验紧密联结,使“天人合一”从哲学命题转化为具象的创作母题。其代表作《漓江百里图》《漓江百景图》不仅是对漓江风貌的视觉记录,更是对“人—地”关系的深度诠释,标志着漓江画派在思想与实践上的成熟。
二、理念转化:“天人合一”在漓江画派中的三重维度
漓江画派对“天人合一”的承续,体现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写生本位、家园意识与大景叙事。这三者共同构成其艺术理念的当代转化路径。
第一,写生本位:从“卧游”到“在场”的实践转向。
传统文人山水画多强调“卧游”,即通过想象与记忆重构自然,而漓江画派则确立了“写生即创作”的根本原则。黄格胜坚持“画到哪里,看到哪里”,主张画家必须亲临现场,与自然直接对话。这种“在场性”使创作过程本身成为“天人合一”的实践仪式。在《漓江百里图》的创作中,黄格胜历时三年沿江写生,足迹遍及桂林至阳朔的每一处滩涂与村落。他不仅记录视觉信息,更捕捉气候、声音、气味等多维感知,使作品成为“活”的生态整体。这种写生观,将“天人合一”从书斋中的冥想转化为身体性的体验,赋予传统理念以现实根基。
第二,家园意识:从“山水”到“家园”的情感升华。
传统山水画中的“天人合一”多具出世倾向,强调超然物外的境界;而漓江画派则注入强烈的“家园”情感,使自然景观成为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载体。黄格胜提出:“我画的不是风景,是我的家乡。”这一立场使漓江从地理概念升华为精神符号。在《漓江百景图》中,画家不仅描绘山水,更刻画渔夫、村妇、梯田、鼓楼等人文元素,构建出“人—地”共生的生态图景。这种“家园”意识,使“天人合一”从哲学抽象转化为可感可触的生活世界,体现出对乡土中国的深切关怀。
第三,大景叙事:从“小品”到“史诗”的结构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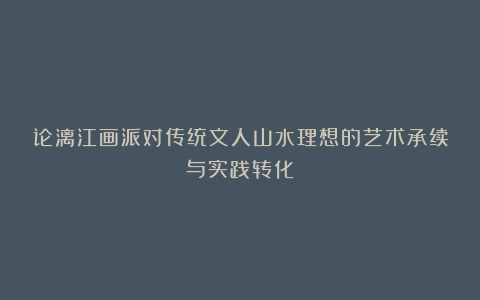
传统文人山水多为尺幅小品,强调“一木一石”的精微意趣;而漓江画派则开创“大景山水”范式,以宏大构图展现地域的整体风貌。《漓江百里图》长达百米,采用散点透视与移动视点,完整呈现漓江流域的空间延展性与生态连续性。这种“史诗性”叙事,使“天人合一”不再局限于个体心境的抒发,而上升为对民族地域文化的集体书写。黄格胜通过满构图、浓墨重彩与块面分割,强化视觉冲击力,使山水成为承载历史、文化与情感的“精神地貌”。
三、代表作品分析:《漓江百里图》与《漓江百景图》的典范意义
《漓江百里图》与《漓江百景图》是漓江画派最具代表性的两部巨制,集中体现了其对“天人合一”理念的实践转化。
《漓江百里图》(1986年始作,历时三年)是黄格胜艺术生涯的里程碑。全卷以水墨为主,兼施淡彩,画面峰林耸峙、江水蜿蜒,村落星罗棋布,渔舟穿梭其间。其艺术价值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空间的真实感,画家通过写生积累,精准还原了漓江地貌的地质特征与空间节奏;二是笔墨的表现力,采用“积墨法”层层叠加,表现山体的厚重与雾气的氤氲,墨色浓而不滞,透而不薄;三是情感的深度,画面中随处可见的细节——晾晒的衣物、炊烟、孩童——使自然景观充满人间烟火气,实现了“天”与“人”的有机融合。
《漓江百景图》(2000年代)则以组画形式呈现,涵盖山水、村寨、民俗、节庆等多元主题。与《百里图》的线性叙事不同,《百景图》采用“散点式”结构,每幅作品独立成章,又共同构成完整的地域图景。其创新在于:一是题材的拓展,不仅表现自然风光,更关注少数民族生活、城乡变迁等现实议题;二是语言的多样化,部分作品融入版画的块面感与民间艺术的装饰性,丰富了视觉表达;三是时间的维度,通过对比传统与现代场景,隐含对生态与文化变迁的思考。这两部作品共同证明,漓江画派的“天人合一”不仅是美学追求,更是文化责任的体现。
四、理论意义:传统山水精神的当代转化路径
漓江画派的实践表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天人合一”理想在当代并未失效,而是需要通过创造性转化获得新生。其转化路径可归纳为三点:
其一,从“出世”到“入世”。传统山水画多具隐逸色彩,而漓江画派则主动介入现实,通过写生与创作回应地域发展、生态保护等当代议题,使“天人合一”具有现实关怀。
其二,从“个体”到“群体”。文人画强调个人心性表达,而漓江画派则以群体形式展开创作,形成“共绘家园”的文化行动,使“天人合一”成为集体文化认同的象征。
其三,从“笔墨”到“生态”。在传统语境中,“天人合一”主要通过笔墨趣味体现;而在漓江画派中,这一理念已扩展至对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的整体关注,具有更广泛的当代意义。
结语
漓江画派的兴起,是中国绘画在现代化进程中对本土文化传统的一次自觉回归与创新实践。通过对“天人合一”艺术理想的承续与转化,该画派不仅延续了山水画的精神命脉,更通过写生本位、家园意识与大景叙事等策略,实现了传统理念的当代重构。从阳太阳、黄独峰的早期探索,到黄格胜的系统性创作,《漓江百里图》《漓江百景图》等作品标志着这一转化的成熟。漓江画派的经验表明,传统并非僵化的遗产,而是可被激活的创造性资源。在当代艺术语境中,唯有深入传统、扎根现实,方能实现真正的文化创新。漓江画派的实践,为中国绘画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值得深思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