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同志希望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价赶快搞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剪刀差的情况,是以国民收入为一百,剪刀差价占百分之三十,而农民直接的税收负担,全国平均不过百分之十左右,如果现在要求完全消灭剪刀差价做到等价交换,国家积累就会受影响。但是剪刀差价太大,使得农民无利可图,那也是错误的。总之,在不影响国家积累的情况下,逐步地缩小工农业品的剪刀差价,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是完全必要的。
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剪刀差对农民生活水平的负面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很多人据此将施行剪刀差的政权视为不爱护农民的政权,反对者则将剪刀差视为一种为了快速进行工业化、带领人民走向全面富裕的“大仁政”,自诩为自己是“真正关心农民”的。这种争论一直屡见不鲜。
我觉得讨论“真正关心农民”都是各派为了争取一般通过所释放的话术。针对“剪刀差”问题,我的看法是:从清代到六七十年代,城乡贸易一直就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状态,城市对农村的“剪刀差”出于维护城市利益的目的长期被承认,所以应当讨论的是“哪些政策有利于避免农民不被剪刀差夺取利益”而不是“谁是真正关心农民的”?
古代以来中国城乡关系就不存在“斯密式增长”,也就是通过城乡的商业贸易,推动农村资本主义化。在这种基于古典经济学的观念中,小农农场随着商品化而让位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农场,随之而来的是城镇中“原始工业”和工业的兴起,最终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中外史学家会寻找“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学者邓拓等人)或者基于城乡市场规模寻找传统农村发展模式的正确之处。虽然明清中国农村商业化规模在同期世界中实属较高,而且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城乡之间的贸易,农村的粮食和经济作物流向城市,城市向农村出售布和盐等手工业品,下图是吴承明化的三类商品在城乡之间流通的示意图,可以看出这些商品的价值量达到3。8亿两以上,占清代总产值的10%以上。
图源: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但是正如吴承明指出的那样,作为第一位商品的粮食,它的长距离运销,主要是由于若干地区严重缺粮所引起的,主要不是由于手工业和经济作物区扩大商品生产所推动的。这一点由张瑞威对长江沿线的大米贸易分析得到证实,长江中游向下游运米主要出现在长江三角洲大米短缺、价格暴涨的时期,年景好的时候,长江三角洲的农民更愿意食用本地的大米。
商品粮销往城市是很少的,城市用粮主要是由农村向城市的单向输出来解决(例如征收赋税或者漕运),这是没有交换的,张瑞威也注意到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大米市场整合较差,华北大米价格比江南更低,归根到底是华北主要主食不是大米的背景下,清朝政府通过漕运从江南运输大量的大米到达华北作为禄米发放给八旗兵丁,后者再放到市场上甩卖换银导致华北米价更低。这就是超经济强制形成的交换,很难说符合斯密增长,毕竟小农没有从城市交换得到什么。
丝、茶主要是销往城市,但也不过二千余万两。这就是说,城乡之间的交换不大。虽然城市手工业已有一定的发展,但其产品主要是供城市消费,很少与农村进行交换。因此,吴承明指出,古代中国国内市场,还是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布(以及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结构。
这样的城乡贸易模式意味着,城市发展是无法直接让农村在地快速发展。黄宗智已经证明了农业商品化水平极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出现了内卷化的现象,他对19世纪江南城乡贸易有系统总结:
当然,这种贸易也不同于亚当·斯密特别强调的城乡之间的双向贸易。在斯密看来,城市的工业品与农村的“原始”产品之间的交换,在促进经济的质变性发展中起了关键性作用。然而,城乡间的交换显然只构成清代长江三角洲贸易的极小部分。小农购买的主要生活必需品是由其他小农生产的;除了少量次要的必需品,他们极少购买城市产品。即使到20世纪,城市产品的渗入仍然很有限,只是棉纱或棉布,以及火柴和火油。小农涉足的这种小商品贸易市场的社会内容,并不是斯密提到的那种城乡交换的互利关系,而是受剥削和为活命的艰难挣扎。部分贸易是由农村剩余向城镇的单向流动构成的,其主要形式是纳租而非交换。另一部分是小农为谋生而进行的交换。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至于这种贸易模式下出现“剪刀差”是必然的结果,尤其是随着近代城市化的发展,工业产品价格天然会高于农村,这是城市对农村具有的优势权力的必然结果。吴承明计算认为,在粮食贸易中,农民所得价格比工业原料品和出口品都要低,大约不超过消费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而工业品在农村的价格,即农民所付价格,大约要比产地高出一倍。外国粮食的倾销、银价下降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工业产品虽然也有下降,但是没有农产品显著,吴承明将这种问题归结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形成不等价交换的结果。
但是如果观察粮食压价的原因,我们不难看见,农村议价能力低最主要还是城市对农村的绝对优势,城市的官员和商人对农村的农民和地主产生支配作用,后者想“口袋里的马铃薯”那样无法形成有效的组织和城市人谈判,吴承明提到的农民因为缺钱买工业品,不得不以赊销、换货等方式高价购买工业品、低价购买粮食。近代中国进一步接入国际市场,以及国家更关注城市的发展,都只是城市权力优势格局的延续的扩大,很多地方的农村被视为“被牺牲的局部”,为了发展城市只能减少对农村的投资。除此以外,近代绅士向城市的集中趋势也降低了农村的议价能力。这本质是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关联导致的,中国工业化是外来而非内生的,这意味着工业企业必然会向大城市和通商口岸集中来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规模效益,这当然会导致集中生产的工业品对分散生产的小农形成降维打击。王玉茹对近代农村物价所得和所付价格的比较,可以看出农村所得物价长期低于所付物价,证明剪刀差的存在和城乡交换的不平等。
面对这种局面,改善农民生活的思路显然是两条:一条是允许农民自由流动,向资本更多、剪刀差收入的城市流动来改善自身生活;另一条是在地的工业化,通过吸纳农民为工业人员,减少被剪刀差剪的人数的同时,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增加农村议价能力。
和这两个思路思路比较,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政策大体上没有改变农民被剪刀差剪的命运,也没有改变过密化(内卷化)的现实。集体化时期土地归集体或者国家所有,然而正如陈耀煌发现的,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本质是“行政整合自然村” 逻辑的升级,这种体制与其说是为了实现规模化经营生产,不如说是延续近代以来国家强化汲取农村(为了救国或者为了打仗)的趋势,方便国家统购统销,不通过商人等中间人直接获得农村生产的剩余。所以,黄宗智指出生产队和传统家庭农场的关联:
在某些方面,集体农场不过是旧有家庭农场的扩大。若干家庭组成一个生产队,成为一个单一的所有权单位。与家庭农场一样,它既是一个消费单位,又是一个生产单位。其生产粮食的大部分用于满足本队社员的消费。因此,集体单位的经济决策,同样是同时根据消费和生产决定的。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不过,集体化并不是单纯把小农经营换个名字,集体化本身就意味着国家深度的干预,尤其是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让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干涉农村的生产,在某些方面可以实现土地资源的集中利用,有时候也可以根据需要去种植一些有效益的作物提高收入,还可以推广一些新技术增加生产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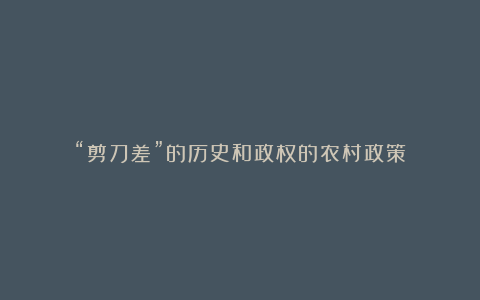
然而,集体化总体上依然是小农经济的延续,仍以传统农具(镰刀、锄头、木制水车)、传统耕作方式(精耕细作、稻桑轮作)为主,机械化水平极低(仅少数公社有机耕队)。最关键是,集体化将农民拴在土地上,使得农业过密化的现实无法得到缓解,生产队不得不投入过量的劳动力在土地上,因此劳动力的收入(每公分价值)事实上处于下降的趋势,迫使小农家庭不得不专注于自留地和副业弥补收入的减少,最后反而维护了过密化的现实,也就是张乐天所说的“过密化技术偏好”:
然而,我们不应错误地根据上述情况推断松江所发生的是增加劳力投入和提高产量一对一关系的直线式密集化的简单状况。事实上,那儿有着无可辩驳的资本化和发展的证据。改进水利、机耕、化肥和新品种均有助于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在不同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出现劳动报酬增加的真正的发展。
但是,这些现代化投入的引进伴随着极端的劳动密集化,而后者不可避免地导致边际报酬递减。双季稻通常要求双倍劳动(和资本),但并未带来双倍产量……因此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大力推行全盘三熟制,无可避免地带来了单位工作日平均报酬的降低。小麦和棉花种植的某些改进中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例如种植小麦时开掘地下排水道当然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但这是在投入高度密集的劳动代价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样的密集化和三熟制一样带来了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故也可称为内卷化。
农村工业化在集体化时代也是存在的。早在1958年“公社工业化” 就成为重要口号,农村工业首次大规模铺开。之后到70年代大规模混乱稳定以后,农村工业在 “农业机械化” 和 “五小工业”(小烘炉、小砖厂、小药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政策推动下进入恢复性发展阶段,社办企业发展起来。当时农村集体企业的发展长期被限制在“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的框架内,主要生产各类机械设备和化肥,为实现70年代农业机械化做好物质基础——当然,这种技术在过密化经营的现实中很难长期实现农民个人收入的增长,但是确实让一部分的劳动力摆脱了过密化的问题。
社办工业很多成为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起源,它的出现除了主要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实现机械化,有一部分也是城市工业发展的需求。正如黄宗智在分析华阳桥公社乡镇企业的时候指出的那样,从国营企业的角度来看,将生产工序的某些部分分散到农村去,主要是为了摆脱掉一些亏损和低效益的工作。农村工本低,即使是国营企业亏本的生产,也可以接手。农村企业比较优势是过密的劳动力,国营企业具有农村不具有的资本积累。国有企业这么做从根本上是因为城乡二元体制的确立,这些低效益的产业需要低成本劳动力来完成,但是城市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民进程,只能招募少量合同工等非正式工人来工作,不如外包给村社企业。
但是,农村工业化本身是受到限制的。70年代农村工业化目的很大程度上被局限在农业生产,因此大量上马的是农机和化肥工业,国家为了鼓励五小工业发展,不仅拨款给地方进行投资办厂,还对地方进行收支包干,二三年内所得利润60%留给县财政,结果各地不顾实际无序建设五小企业,引起地方企业之间剧烈的竞争,亏损严重的同时也没有提高生产效率。
地方小企业的大量发展很不经济,投资效益偏低,企业建起来之后,却经常缺乏原料和资源供应。例如在没有铁矿石和煤炭的地点大建小钢铁厂。地方重复建设非常严重,例如为了达到所谓“一个省一个大化肥厂,一个地区一个硝铵厂,一个县一个小化肥厂”的目标,许多地区要依靠从远方购买煤炭来建化肥厂。这也导致了企业经济效益的低下。例如到1976年,全国1500个小化肥厂中有1066个亏损,亏损总额达到5.9亿元。
周飞舟《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
五小企业的混乱和市场的“无政府化”具有相似的地方,双方都是在生产指令失灵(前者是国家政策,后者是价格)的情况下生产者无脑投资的结果。不同之处是,五小企业在当时生产弹性更差,如果遭遇严重亏损不好倒闭,也无法转型其他生产(政治挂帅),张乐天就举出案例说明当时村社企业生产方式的固化:
1977年,国内机械行业生产过剩,农用电机等产品错,Y农机厂的领导不得不开发新产品,开拓新的业务渠道,从火油炉,簸箕一直到给上海修理汽车、为青海生产门锁。但是厂领导却因此受到了批评,还一度被免职。公社农机厂生产滑坡,出现亏损,厂里的干部工人说:“上海汽车,青海门锁,又气又错。”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以粮为纲”限制了农业生产选择的灵活性,也缩小了村社工业的生产面
如果从长期来说,农村工业化不太可能长期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人口流动才是大势所趋。如前所述,中国近代以来的工业化是城市>>农村的工业化,无论是外国投资,还是晚清以来和国家密切相关的官督商办企业-官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都是围绕着城市发展的,并无形成农村工业化的机遇。五小工业、村社企业和乡镇企业也是在城乡二元化模式和国家有意鼓励的情况下才出现。随着城乡二元化体制的动摇,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可以获得进城劳动力,减少外包乡镇企业形成的运输成本,因而对乡镇企业的投资很难扩大,乡镇企业经历80-90年代的兴盛后衰落也是意料之内的。
站在国家的角度,无论是哪个政权,他们首先都要为了维系国家和政权的存续——“真正关心工人”的结果是61-62年的“2000万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说到底还是国家财政养不活那么多工人,农村生产又陷入混乱的必然结果。归根到底,各类政策是为了稳定秩序而不是“真心为了XX好”,生产力还没有到没有所有制也不影响社会秩序的情况下(这也很难达成),国家需要理性地计算收支,谨慎地对待经济生产秩序。天下大乱三年老人家就受不了,不得不搞三结合来恢复经济秩序;上海张哥想在全国红色司令部上海实行干部工人供给制,从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结果此事由马天水布置综合计划组和财政局、劳动局测算,由写作组的经济组负责联系各方测算结果。最后的结果让所有怀念供给制情节者止步:财政开支将增加好几倍。现实的约束让任何政权都很难说“真心关心”,毕竟现实就是没钱。
上海公社作为实现巴黎公社的尝试因为没钱而失败
“真正关心农民”这种话术不如分析“哪些政策有利于农民”有意义。无论是民国还是共和国,他们城乡的差距都很明显,城乡贸易剪刀差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毕竟他们都需要发展城市来“寻求富强”;过密化也是农村生产的现状,农民陷入“没有发展的增长”,无论是非经营性地主还是集体经济都无法改变过密化生产的模式(经营地主可以,但是这种地主在华北有发展上限,而在长江三角洲容易被过密化冲垮),这就必须分析具体政策是否可以让农民实现“具有发展的增长”。事实证明,60-70年代的农村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因为其对过密化技术的倾向,导致农民收入几乎无增长。社队企业在农村虽然遍地开花,但是大量的企业因为主观客观原因经营不善,规模无法扩大,也无法承担吸纳过剩劳动力的能力,导致这种去过密化的路线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