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作为20世纪中国画变革的关键人物,其“李家山水”体系的建构不仅体现在笔墨结构的革新,更在于对传统中国画色彩体系的突破性探索。本文立足山水画专业视角,系统梳理李可染从早期写生到成熟期“黑、满、重、亮”风格形成过程中用色观念与技法的演变轨迹。
通过对其不同时期代表作品的色彩语言进行图像学分析,结合其画语录中的理论阐述,揭示其“以西润中”的用色策略——即在生宣纸上实现写意性色彩表现的内在逻辑:从早期受林风眠影响的抒情性色彩,到中期写生中对自然光色的提炼与主观强化,最终在“为祖国河山立传”的创作理念驱动下,创造性地将逆光表现、积墨积色、浓重矿物色与生宣特性相结合,构建出具有崇高感与时代精神的色彩图式。研究表明,李可染的用色变革并非简单移植西方色彩,而是根植于中国画审美本体,通过材料、技法与观念的多重突破,拓展了水墨写意的色彩表现维度,为当代中国画的色彩语言发展提供了兼具历史深度与现代性的范式。
关键词: 李可染;山水画;用色变革;墨彩关系;写意性;生宣;中国画现代化
一、引言
20世纪以来,中国画的现代化转型始终围绕“传统与革新”的核心命题展开。在这一宏大叙事中,李可染(1907—1989)以其“为祖国河山立传”的艺术理想和“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的革新精神,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实践者之一。其开创的“李家山水”体系,以“黑、满、重、亮”的视觉特征和深邃厚重的意境,重塑了现代中国山水画的审美范式。学界对李可染的研究多聚焦于其笔墨结构、构图创新、师承关系及艺术思想的宏观梳理,而对其用色体系的系统性、阶段性研究则相对薄弱。
色彩作为中国画表现语言的重要维度,长期处于“随类赋彩”的辅助地位,尤其在生宣纸上实现写意性、表现性色彩的探索,更是传统中国画的难点。李可染在这一领域的突破,不仅关乎个人风格的成熟,更触及中国画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如何在保持水墨写意精神的前提下,有效吸纳西方绘画的光色观念与表现技法,拓展中国画的表现力与现代性。本文拟从山水画专业的技术与美学双重维度切入,通过对其创作生涯中用色实践的历时性考察,结合其画语录的理论阐释,深入剖析李可染用色变革的内在逻辑、技术路径与美学价值,进而揭示其对中国画色彩语言发展的深远启示。
二、早期探索:写生实践与抒情性色彩的萌发(1940s–1950s初)
李可染的用色变革始于其1950年代初开始的系列写生实践。这一时期的用色,虽仍以传统水墨为主,但已显露出对自然光色的敏锐感知与主观表达的强烈意愿。1954年与张仃、罗铭的江南写生,被学界视为其艺术转型的起点。在《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1954)等作品中,李可染开始尝试突破传统程式化的设色方法。他不再拘泥于“随类赋彩”的固有色观念,而是注重捕捉特定时间、光照条件下景物的色彩氛围。画面中,青绿与赭石的运用不再是平涂的装饰性色块,而是与水墨皴擦结合,通过薄染、罩染等技法,营造出湿润、清新的江南气息。此时的色彩虽未脱离文人画雅逸的基调,但已体现出对“写生”这一现代绘画方法的自觉运用。
值得注意的是,李可染早年曾受教于林风眠,其色彩观念深受林氏“调和中西”思想的影响。林风眠主张“用中国的笔墨画现代的画”,其作品中强烈的主观色彩与装饰性构图,为李可染提供了早期启示。在1956年的《雨后斜阳》中,我们能看到这种影响的延续:画面以大面积的暖赭色渲染夕阳余晖,冷暖对比鲜明,色彩的情感表现力被显著强化。这种“抒情性色彩”的尝试,标志着李可染开始将色彩从“补笔墨之不足”的附属地位,提升为独立的情感载体与氛围营造手段。他在画语录中曾言:“画山水,要画出空气来。”这里的“空气”,不仅指空间感,更包含光与色交织的视觉氛围。早期写生中的色彩探索,正是为“画出空气”而进行的技术准备。
三、中期深化:逆光表现与“积色”技法的成熟(1950s末–1970s)
1959年《六盘山》的创作,标志着李可染用色观念的重大转折。他开始系统性地运用“逆光”表现手法,这成为其色彩语言的核心特征。在《六盘山》中,山体被处理为深沉的剪影,而天空与云霞则以朱砂、赭石等暖色层层积染,形成强烈的明暗与冷暖对比。这种逆光处理,不仅增强了画面的立体感与空间纵深,更赋予山水以庄严、崇高的视觉意象。逆光的引入,迫使李可染必须重新思考色彩在生宣纸上的表现极限。传统浅绛、小青绿设色难以承载这种强烈的光感,他转而借鉴西方绘画的“厚涂”与“叠加”理念,发展出独特的“积色”技法。
“积色”并非简单地叠加颜料,而是在生宣纸的特性约束下,通过控制水分、颜料浓度与叠加次数,实现色彩的深度与层次。李可染常在墨色已干或半干时,以饱和的矿物颜料(如朱砂、石青、石绿)进行多层罩染。每一层都极薄,但多次叠加后,色彩呈现出宝石般的厚重感与内在光泽,如《万山红遍》(1963)中层林尽染的红色,即是通过数十遍朱砂的积染而成。这种技法与“积墨”法异曲同工,共同构建了“黑、满、重、亮”的视觉特征。其中,“亮”尤为关键——它并非来自留白,而是通过深色背景的衬托与高纯度色彩的并置(如朱红与墨黑)所产生的视觉“亮感”。李可染在画语录中强调:“用墨要大胆,要敢于用重墨、浓墨,但要用得活。”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用色。他的“用色要胆大”,体现在敢于使用高纯度、高饱和的色彩,并将其置于画面的视觉中心。
此外,李可染还创造性地将“拓印法”融入用色。在《杏花春雨江南》等作品中,他用纸团或布团蘸取颜料,在画面上拓印出斑驳的肌理,模拟自然界的光影闪烁与色彩交融。这种非笔触性的色彩表现,打破了传统“笔笔见笔”的用色规范,增强了画面的写意性与偶然性。这一时期的用色,已完全超越了早期写生的客观再现,进入高度主观化、象征化的境界。色彩成为表达“所要者魂”——即时代精神与个人情感——的核心媒介。
四、成熟期的升华:崇高意境与“为祖国河山立传”的色彩图式(1970s–1980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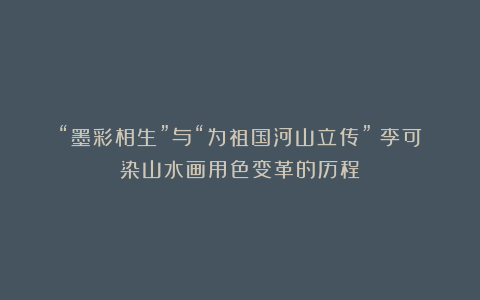
1970年代以后,李可染的山水画进入完全成熟期,其用色体系也臻于化境。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1985)、《高岩飞瀑图》(1987)等,将“黑、满、重、亮”的风格推向极致。色彩的运用更加纯粹、凝练,服务于整体意境的营造。此时的“黑”,已非简单的墨色堆积,而是通过“墨破色”、“色破墨”、“积墨积色”等复杂技法,使墨与色在生宣纸上相互渗透、交融,形成深邃如夜、厚重如铁的视觉效果。这种“黑”并非死寂,而是蕴含着无限生机与光感,正如他在画语录中所言:“黑入太阴雷雨垂”,黑中蕴藏着宇宙的元气与力量。
“亮”的表现则更加精妙。除了通过冷暖、明暗对比产生视觉“亮感”外,李可染更善于利用色彩的纯度与材质特性。他常在深色山体的边缘或结构转折处,点染极小面积的高纯度朱砂或石青,如“画龙点睛”般瞬间点亮画面。这种“亮”是精神的闪光,是“为祖国河山立传”这一崇高主题的视觉象征。在《漓江胜境图》(1984)中,漓江水面的倒影以极淡的花青与赭石渲染,与两岸浓重的墨色山体形成虚实相生的对比,色彩的“空灵”与“厚重”并置,营造出既雄浑又秀美的意境。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李可染在成熟期对生宣纸“渗化”特性的控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利用生宣对水分与颜料的敏感性,通过干湿、浓淡、快慢的精确把控,使色彩在纸上自然晕染、渗透,形成微妙的过渡与丰富的肌理。这种“写意性”正是中国画的核心价值。李可染的用色变革,其根本意义在于证明了:在生宣纸上,同样可以实现具有表现力与现代感的色彩写意,而无需放弃水墨的流动性与偶然性。他的成功,建立在对材料物理属性的深刻理解与对传统笔墨精神的坚守之上。
五、理论阐释与历史定位:李可染用色变革的内在逻辑与启示
李可染的用色变革,绝非孤立的技术实验,而是其整体艺术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画语录为我们理解其用色逻辑提供了关键钥匙。他强调“可贵者胆,所要者魂”,这里的“胆”体现在敢于突破传统用色禁忌,大胆使用重色、亮色、纯色;“魂”则指色彩必须服务于作品的精神内核——对祖国山河的礼赞与对时代精神的讴歌。他主张“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其用色实践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深入研究传统青绿、浅绛设色法(“打进去”),又大胆吸收西方印象派、后印象派的光色观念与表现技法(“打出来”),最终创造出既非传统亦非西化的“李家山水”色彩体系。
从历史维度看,李可染的用色变革,是对20世纪中国画“色彩困境”的一次成功突围。自晚清以来,面对西方绘画的冲击,中国画家在色彩运用上或固守传统,或全盘西化,少有能真正实现“中西融合”者。李可染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始终以中国画的审美本体(尤其是写意精神与笔墨价值)为坐标,有选择地“拿来”西方元素。他借鉴西方的光色分析,但摒弃其科学再现的机械性;他运用浓重的色彩,但始终以“墨”为骨,保持水墨的主导地位。这种“以西润中”的策略,确保了其变革的“中国性”。
对当代中国画坛而言,李可染的用色实践提供了三重启示:其一,材料与技法的创新必须根植于文化精神的表达,技术服务于“魂”;其二,在生宣纸上实现写意性色彩表现是可能的,关键在于对材料特性的深入探索与对传统笔墨的创造性转化;其三,中国画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而应是在开放视野中,以我为主,实现传统的创造性再生。李可染的“墨彩相生”之道,为后人开辟了一条通往“现代中国画”的坚实路径。
六、结论
综上所述,李可染山水画的用色变革,是一个从写生观察到主观提炼,从技术实验到美学升华的完整过程。他以“为祖国河山立传”的宏大叙事为驱动,通过“逆光”表现、“积色”技法、生宣特性的精妙控制等手段,在生宣纸上实现了写意性色彩的重大突破。其色彩语言既吸收了西方绘画的光色观念与表现力,又坚守了中国画的写意精神与笔墨本体,创造出“黑、满、重、亮”的独特视觉图式。这一变革不仅成就了“李家山水”的艺术高度,更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画的发展方向。李可染的实践证明,中国画的色彩表现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其关键在于以开放而审慎的态度,进行根植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当代中国画坛,重审李可染的用色智慧,对于推动中国画色彩语言的当代发展,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