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以篆书尤其是《石鼓文》书法成就最为著称,然其隶书艺术亦独具风貌,长期被学界相对忽视。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吴昌硕传世隶书作品及相关文献,考察其隶书学习历程,揭示其隶书在不同阶段的风格演变:早期取法《张迁碑》《衡方碑》等汉隶经典,笔法方整朴厚;中晚期则逐渐融入篆籀笔意,形成结体纵长、波磔弱化、线条浑厚如“屋漏痕”的独特书风。学界所谓“以篆籀法作隶”之说,实为对其隶书本质的精准概括。本文进一步论证,吴昌硕的隶书并非独立发展,而是与其篆书实践深度互文:篆书为其隶书提供笔法支撑与气韵基调,隶书则反向丰富其篆书的结构变化与节奏韵律。二者共同构成其“金石气”书风的有机整体,彰显其“融通诸体”的艺术理念。
关键词:吴昌硕;隶书;篆籀笔法;石鼓文;书法风格;互文性
一、引言:被遮蔽的隶书成就
吴昌硕(1844—1927)作为晚清民国书坛巨擘,其书法以篆书,尤其是取法《石鼓文》的雄浑苍茫书风而名世,影响深远。学界对其篆书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从笔法、结构、章法到审美意蕴,均有深入探讨。相较之下,其隶书艺术虽偶有提及,却常被视为篆书的附庸或次要实践,未能获得应有的系统性关注。
然而,细察吴昌硕一生书法创作,其隶书不仅存世作品数量可观,且风格鲜明,贯穿其艺术生涯始终。从早年临习汉碑的朴拙之气,到晚年“以篆籀法作隶”的浑穆境界,其隶书呈现出清晰的风格嬗变轨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隶书在结体上多取纵势,波磔笔画趋于弱化甚至隐去,线条质感与篆书高度趋同,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吴氏隶书”面貌。
本文认为,吴昌硕的隶书绝非简单的书体尝试,而是其整体书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与其篆书实践构成深刻的互文关系,共同服务于“金石气”这一核心审美理想的建构。通过对吴昌硕隶书的系统研究,不仅可以还原其完整的学书历程,更能深入理解其“融通诸体”的艺术理念与创造性转化能力。
二、学书历程的梳理:隶书的阶段性风格演变
吴昌硕的书法学习始于家学熏陶,其父吴辛甲即善书。据《吴昌硕年谱》及自述材料,其早年广泛涉猎诸体,隶书为其重要研习对象。
早期(约1860年代—1880年代):取法汉隶,朴厚方整。
吴昌硕早年隶书主要取法《张迁碑》《衡方碑》《封龙山颂》等方笔汉隶。此期作品如《临张迁碑四条屏》(约1870年),用笔方峻,起收果断,结体宽博,波磔分明,体现出对汉隶经典法度的严谨遵循。此时的隶书尚具明显的“碑体”特征,强调金石刻凿的力度与秩序感,与其同期篆书(初学《石鼓文》)的探索并行不悖。
中期(约1890年代—1900年代):篆隶交融,风格初变。
随着吴昌硕对《石鼓文》理解的深化,其书法笔法发生根本性转变。中年以后,其隶书开始明显融入篆书笔意。典型如《隶书七言联》(1895年),虽仍可见隶书结构,但线条已趋于圆厚,波磔减弱,起笔多藏锋圆转,收笔含蓄内敛,结体亦由横扁向纵长过渡。此阶段,其“以篆入隶”的探索已初见端倪,隶书的“金石味”日益浓厚。
晚期(约1910年代—1927年):风格成熟,篆籀为体。
至晚年,吴昌硕的隶书完全成熟,形成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代表作如《隶书“溪流石作”五言联》(1920年)、《隶书“华馆”横披》等,其特征极为鲜明:
结体纵长:打破隶书“扁方”传统,字形普遍拉长,取纵势,与篆书体势趋同;
波磔弱化:隶书标志性的“蚕头燕尾”波磔几乎消失,代之以浑厚圆劲的提按,或化为含蓄的顿挫;
线条篆化:通篇线条圆润饱满,中锋逆行,如“屋漏痕”“锥画沙”,充满弹性和张力,与《石鼓文》笔意如出一辙;
章法浑穆:字距紧凑,行气贯通,整体气息雄强朴茂,极具视觉重量感。
此期隶书,已非传统意义上的汉隶,而是“以篆籀法作隶”的典范,堪称“篆体隶意”或“金石化隶书”。
三、“以篆籀法作隶”:学界观点的再阐释
“以篆籀法作隶”一语,最早见于近现代书论家对其隶书的评述。此说精准地抓住了吴昌硕隶书的本质特征,即用篆书的笔法、气韵来书写隶书。
“篆籀”原指篆书体系,尤指大篆、籀文,其笔法强调中锋圆笔、藏头护尾、力透纸背。吴昌硕将其用于隶书,实现了对隶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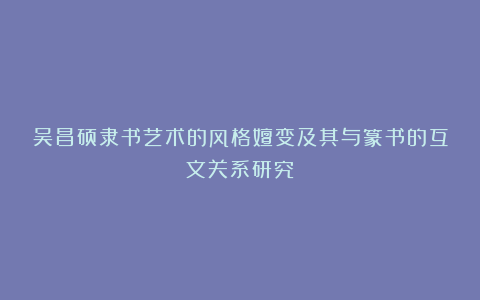
其一,笔法的统一性。传统隶书强调提按顿挫与波磔的节奏变化,而吴昌硕则以篆书的“平动”“绞转”笔法为主,减少提按幅度,使线条更加凝重统一。这种处理,弱化了隶书的“书写性”节奏,强化了“铸造感”与“雕刻感”,更契合其追求的“金石气”。
其二,气韵的贯通性。篆书线条连绵不断,气息内敛而悠长。吴昌硕将其引入隶书,使原本较为“断续”的隶书笔画(因波磔分割)变得连贯流畅,通篇气息更加浑厚一体。如其隶书对联,上下字之间、左右联之间,皆有笔势呼应,如龙蛇游走,气势磅礴。
其三,审美理想的趋同。吴昌硕毕生追求“古、拙、雄、厚”的审美境界,而传统汉隶中的秀美、飘逸一路(如《曹全碑》)与其理想相悖。通过“以篆籀法作隶”,他成功地将隶书纳入其“金石审美”体系,使其与篆书、绘画、篆刻共同构成统一的艺术语言。
因此,“以篆籀法作隶”并非简单的技法移植,而是一种基于深层审美诉求的艺术重构。
四、篆隶互文:两种书体的共生关系
若将吴昌硕的篆书与隶书割裂看待,则无法真正理解其书法艺术的完整性。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文性”关系,彼此滋养,共同发展。
其一,篆书为隶书提供笔法根基与气韵基调。
吴昌硕对《石鼓文》数十年如一日的临习,使其形成了高度个性化的篆书笔法系统。这种以中锋逆行、圆劲浑厚为核心的笔法,成为其所有书体的“母语”。当其书写隶书时,这种笔法自然流露,使隶书线条获得与篆书同等的质感与力度。可以说,没有其成熟的篆书实践,便不可能有其“金石化”的隶书。
其二,隶书反向丰富篆书的结构与节奏。
反观其篆书,尤其是晚年作品,亦可见隶书的影响。其《石鼓文》书法在保持篆书基本结构的同时,结体时有纵长化倾向,部分笔画(如捺脚)略带隶意波挑,章法上更注重疏密对比与错落节奏。这种变化,正是隶书实践对其篆书的反向渗透。隶书的“势”与“节律”,为相对静态的篆书注入了动态活力。
其三,共同服务于“金石气”的审美建构。
无论是篆书还是隶书,吴昌硕的终极目标都是营造“金石气”——一种古拙、雄强、苍茫、浑厚的艺术气质。篆书以其本源性的古文字形态直接体现“古”与“拙”;隶书则以其对汉碑的改造,强化“雄”与“厚”。二者合力,使吴昌硕的书法世界呈现出统一而丰富的金石美学景观。
因此,吴昌硕的篆书与隶书并非平行发展的两条线,而是一个有机互动的生态系统。其艺术创造力,正在于打破书体壁垒,实现“诸体融合”。
五、结论:融通诸体的艺术典范
吴昌硕的隶书艺术,是其整体书法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早期对汉隶经典的严谨临习,到中晚期“以篆籀法作隶”的创造性转化,其隶书经历了一个清晰的风格嬗变过程,最终形成结体纵长、波磔不显、线条浑厚的独特面貌。
“以篆籀法作隶”不仅是对其隶书技法的描述,更是对其艺术理念的概括。这一实践,体现了吴昌硕打破书体界限、融通古今的创造性思维。其篆书与隶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文关系:篆书为隶书提供笔法与气韵,隶书则反向丰富篆书的结构与节奏,二者共同构建了其“金石气”书风的坚实基础。
吴昌硕的隶书研究,提醒我们重新审视其书法艺术的完整性。他不仅是一位“篆书大师”,更是一位“诸体兼善”的通才。其“融通诸体”的艺术实践,为后世书法家提供了宝贵启示:传统书体的创新,不在于标新立异的形式拼贴,而在于对艺术本质的深刻理解与对不同书体内在规律的创造性整合。吴昌硕以其一生的探索证明,真正的艺术高峰,往往矗立于诸体交融的广阔原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