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定陶即皇帝位,国号“汉”,史称西汉;公元25年,刘秀在鄗城即皇帝位,国号仍称“汉”,史称东汉。两段历史隔着王莽篡位与绿林赤眉的混战,首尾相距二百三十年,却共用同一个国号。于是常有人发问:它们究竟是一个朝代的自然延续,还是两个彼此独立的政权?答案其实早已写在古代史家的笔下,也埋在考古出土的简牍、铭旌与宫室废墟之间——它们不是同一个朝代,而是同一刘姓皇统的两次建国,史家合称“两汉”,分开来看则各有完整的兴亡轨迹。
刘邦vs刘秀
刘邦建国,起点是平民起兵。他出身泗水亭长,反秦战争中被诸将推为“汉王”,五年楚汉之争后称帝,定都长安,削异姓王、封建同姓,确立“汉家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关中本位:皇帝直接掌握关中精锐,以列侯、刺史层层钳控关东;财政上承秦旧律,货币、度量衡、律历皆重新统一;意识形态里则杂用黄老与儒术,到武帝时正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西汉十二帝,前后二百一十四年,外戚、宦官虽时有干政,但中枢权力始终出自长安未央宫,最高统治集团是随刘邦起事的“丰沛元从”及其后裔,社会结构也以军功爵制为骨架。可以说,西汉是一个从零开始构建的新王朝。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公元9年,王莽受禅,改国号“新”,西汉遂亡。其后十四年,天下分崩,赤眉、铜马、绿林各拥刘姓宗室为号召,实为群雄割据。刘秀虽是高祖九世孙,却并非皇统近支,父亲只是南顿令,本人起于白衣。他先在更始帝麾下为司隶校尉,后单骑渡黄河,得河北豪族支持,于鄗南即位。即位诏书自称“中兴”,却不得不另起炉灶:政治中心东移,定都洛阳;统治骨干是南阳、河北的世家大族与颍川、弘文的儒生集团;军事上废除郡国都尉,罢轻车、骑士、材官,改以中央募兵与豪族部曲并立;经济上因关中残破,不得不依赖关东谷仓与黄河漕运。制度虽标榜“汉家故事”,内里却是对王莽失败的直接回应:不再信任理想化的复古改制,转而向地方豪强势力妥协,于是东汉成为“豪族政权”的典型。这些结构性的差异,使东汉与西汉形似而神异。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古人早已意识到这种断裂。班固作《汉书》,叙事止于王莽篡位,不把光武以下纳入;范晔作《后汉书》,另起本纪、列传,与《汉书》截然分开。东汉人自己也不敢把新莽时期算作汉室正统,而称“汉道中绝”,于是年号“建武”“中元”“永平”皆含“再受命”之意。若西汉、东汉本为一朝,史家无需分撰两书,君臣也无需反复申明“中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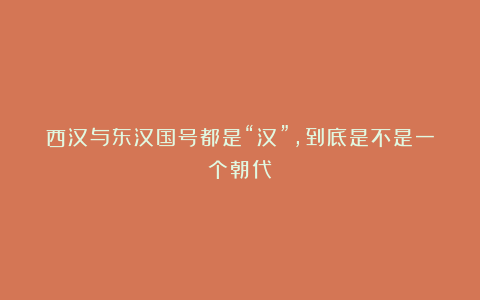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当然,连续性同样显而易见:皇族姓刘,宗庙共祀高皇帝;律历、礼仪、玺印、绶色皆承旧制;谶纬里仍以“赤帝子”为皇权来源;对外仍自称“大汉”,匈奴、西域、倭国亦以“汉”视之。但这种连续性属于“皇统”与“文化符号”,而非政权实体。正如东晋仍号“晋”、南宋仍号“宋”,虽国号不变,史家却分别称“西晋—东晋”“北宋—南宋”,无人把它们视为一个朝代。两汉之例,与此同科。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今日考古也可佐证:长安未央宫遗址终于王莽末年,洛阳南宫则始建于建武二年,宫室尺度、布局、官署名称虽模仿旧京,却非原址重建;西汉帝陵分布在咸阳原,东汉帝陵集中在洛阳邙山,各自形成独立的陵寝体系;出土印章中,西汉县宰称“令”或“长”,东汉中叶以后普遍称“宰”,官制细节亦有递变。地层与器物不会说谎,它们提示着两个时代真实的物理间隔。
长安未央宫
因此,称西汉与东汉为“一个朝代”,既不符合古代史家的断代传统,也难以解释制度与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更准确的表述是:它们同属“刘汉皇统”,却是两次建国、两个都城、两套统治集团的产物,合则统称“两汉”,分则各为独立的历史阶段。国号相同,不过是古代“家天下”体制下,皇族对自身品牌的有意延续;而历史学者与考古地层却告诉我们,长安的鼓声早已沉入渭水,洛阳的晨钟敲醒的是另一个崭新的帝国。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