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朝代,历经的都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创的都是千年未有之大功业,但名声都很差,它们一个是秦朝,一个便是中华民国。
先说秦朝。
在秦以前,自战国、春秋上溯至周、商,可以说都是邦国时代,实行的封建制。所谓封建,即封土建国。简单来说就是古代的帝王在打得天下后,为了犒劳联军,酬谢功臣和巩固政权,便“裂土田而瓜分之”,将天下按大小、等级分给自己的后裔、前朝的遗民以及立功的将士,让他们在地方作“诸侯”,分区管理,辅佐王室。这就是当时的诸侯国,或者叫邦国。
秦统一六国后,中国历史进入帝国时代,实行的是郡县制。所谓郡县制,就是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由中央垂直管理地方郡、县二级政权的一种行政制度,地方官员也实行由皇帝直接任免的流官任期制。
据说六国初灭,时任廷尉的李斯就跟丞相王绾起了争执,就国家采取封建制还是郡县制各执一词,当时站王绾的朝臣好像还要多一些。后来是秦始皇力排众议,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确立了郡县制。
按钱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的观点,“秦始皇和李斯,则比较站在较开明较合当时历史大流的地位,要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寝兵理想。”而不仅仅只为了谋求一姓一家私政权的统治与镇压,便将天下分封给自己的子弟、宗室、姻戚和功臣。“这一个远大理想之实施,而非出于政治上之阴谋与私心。他在当时,实在是追随于战国以来,政治上不许有两个政府,社会上不许有两个阶级的“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时代思潮而努力求其实现的。”所以当时就有人夸赞他说“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
虽说秦朝从建立到覆亡,只有短短的15年,历二帝,但历经的却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创的也是千年未有之大事业。自此,中国历史从邦国时代,正式进入到大一统的帝国时代。
2
再说中华民国
辛亥革命以前,中国是皇权与相权相互制衡的帝治时代;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历史便正式地进入到党治时代。
帝治时代的政权组织形式上面已经谈到了,党治时代的政权组织形式复杂多变,这一百多年来一直处在摸索演进之中,直到近几十年来才渐趋稳定,这个大家相对比较直观,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中华民国自建立到败退台湾,也只有38年时间,先后经过了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三个历史时期,但历经的也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创的也是千年未有之大事业。自此,中国历史从帝治时代,正式进入到党治时代。
3
如此大破大立、波澜壮阔的朝代,历经的都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创的都是千年未有之大功业,但他们在历史上名声都很差,这是为什么?
冯至说鲁讯先生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时曾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
这是一句很有真知灼见的话。
在历史上,如果一个王朝寿命太短,它自然就来不及修自己的历史,便只能留给下一个朝代去修了。比如秦朝就是西汉的司马迁给修的史,王莽的新朝是东汉的班固给修的史,《隋书》是唐朝的魏征主持编写的,至于中华民国的历史,这个就更不用说了。
后朝人修前朝史,一是在写的时候没有什么禁忌,什么好的坏的都敢写,也不用担心会有什么人过来砍了你的脑袋。
二是古时候能著书立说的都是“士”这个阶层,他们一般都有过在本朝从政的经历,都是吃过、或者正在吃着朝庭的俸禄,最起码祖上也是吃过朝庭俸禄的,因此他们受“意识形态余绪”和“政治情结遗风”的影响,修史时难免会偏向本朝,往往不是那么客观。而且过去的时间越短,这种“余绪”、“遗风”就越浓,倘若时过去的时间长久一些,这种东西就会淡很多。
三是如果这时候皇权再过来干预一下,那就更不得了了。
历来的朝代更迭,要么通过政变,要么就是靠造反起家的,就没有一个例外(当然老早的时候也有禅让的,但后来就很少了,偶尔有那么一两次,也都让得不情不愿的,只是刀都架在脖子上了,不能不让罢了)。这样一来,如果把前朝的历史写的太过于伟光正,那本朝的取而代之就会缺乏法理性、正义性,就成了乱臣贼子。而只有把你写的生灵涂炭、饿殍遍野、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了,我的取而代之也就顺天承运、替天行道了,救万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建不世之功勋。
写《三国志》的陈寿自己便是四川南充人,又在蜀汉做过官,后来又在西晋继续做官,所以他在写《三国志》时就比较偏颇,一屁股坐到了蜀汉那一边去了。对于曹操自然也就没有说过什么好话。后来脱胎于《三国志》的《三国演义》,更是视蜀汉为正统,直接把曹操当作奸贼了。等到后来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却以曹魏为正统,至于蜀汉、孙吴,那自是不屑一顾的,大约是在心里早把他们当成乱臣贼子了。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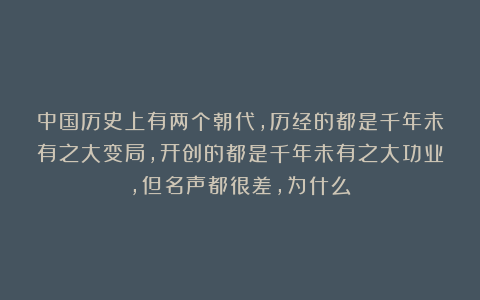
但如果一个王朝的寿命足够长,一百多甚至两三百年那样,就另当别论。
中国人向来很注重修史,钱穆先生在他《国史大纲》的引论里也说,“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二者无间断,三者详密”。
王朝初立,天下甫定,分封行赏便提上日程。皇权给予臣属的,除了物质层面的赏赐外,精神层面的褒奖更不能少,这时候修史立传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这不仅关系到生前,更关系到身后,是荫及子孙后辈的大事,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才是不朽的功业呀。中国历史上的的士大夫,非常看重“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的。
如果一个王朝的寿命足够的长,那它也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去删减、去修改、去润色、去涂抹、去遮蔽、去遗忘,只把那光鲜亮丽,流光溢彩的一面呈现出来。而其他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湮灭在历史的尘埃里了。
李世民大家都知道,李渊的次子,杀(悖)伐(逆)果(伦)断(常),玄武门之变屠兄戳弟逼父、尽诛子侄,夺得了皇位。虽说一朝登顶,君临天下,但皇位终究来得不那么光彩,不那么名正言顺,所以就很在意史官怎么记载这件事。
贞观15年的一天,他找来做起居注(管理“记录皇帝每天干了哪些事”的档案)的褚遂良问:“卿知起居注记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意思是你管理起居注,都记些什么事呀,我这做皇帝的能看看吗?
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检戒,不闻帝王躬身观史。”诸遂良就说,起居注就是古时候左右史所记帝王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好事和坏事都记,用于今后检讨警戒。又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皇帝自己看起居注的事。很委婉的拒绝了李世民的要求。
李世民不甘心,就又问道,“联有不善,卿必记之耶?”意思是我如果有做得不对的,你一定会如实记录吗?
诸遂良说:“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做臣子的必须要尽忠守职,我的职责就是如实做记录,所以您干了什么,我都要记下来。
李世民这时候就已经很尴尬了,但旁边有个更不长眼的叫刘洎的黄门侍郎,还给补了一刀,“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人皆记之矣。”这个好理解,就是即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都记着那!
李世民很是悻悻,但他也不跟褚遂良硬来,于是就找到房玄龄,说他还想看看史官的记录。房玄龄就跟他说,他们记得东西不做技术处理,很直截了当,您看了不一定受得了,还是不要看的好。李世民就说,老房你还不了解我吗?我看了可以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呀,我也要不断学习来提高自己嘛。
你说房玄龄还能说什么,就把《高祖实录》还有《今上实录》找来给他看了。李世民看了之后,认为史官们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录站位不高、立场不清,于是亲自指导进行了修改,认定玄武门之变是和西周的“周公定三监”一样,是当然的、正义行为。于是一段历史公案就此了结(有了官方定性)。
这个还算是比较比较温和的干预,历史上还有更惨烈、更血腥的干预,那就是北魏建国以后,因为修史而引发的两次冤狱。
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第一个王朝是北魏。北魏的开国者拓拔氏是鲜卑游牧民族,它们在入主中原之前文明程度较低,文字大约也没有成形,或者很可就没有文字,基本上还是一个刻木结绳的状态,更不要说汉文明里的伦理纲常观念了。
比如北魏的开国皇帝道武帝拓拔珪,他的母亲贺兰氏在生下他没多久,他的父亲献明帝年纪轻轻的便死了,都没来得继位。然后他的母亲贺兰氏依照氏族部落传统的“收继婚制”,又被他的爷爷昭成帝收取为妻,并育有子女,这样一来伦理纲常也就乱成了一锅粥。还有就是因为生存环境恶劣,文明程度较底,氏族部落之间、部落内部常常为了争夺资源、争夺权力而相互杀伐征讨,所以拓拔早期历史中弑父杀妻、屠兄戮弟、忤逆悖伦、母后专擅的情事肯定也有不少。
所有这些,都为北魏后来的因为修史而引发的两次冤狱埋下了祸根。
道武帝是一个深具历史感的人,北魏建国之初,他为了给自己的创业治国大业造势,让一个叫邓渊的人依照拓拔部民的口耳相传,主持编写了《代歌》,还给配了乐,用来记录、歌颂拓拔氏“祖宗开基、君臣废兴”一类的事情。邓渊这个人“明解制度’多识旧事”、“性贞素,言行可复”,后来道武帝又让他修史。于是邓渊根据之前的《代歌》,还有其他的一些资料,又搞了个《代记》出来,但是没过多久,他因为一个和修史不相干的案子的牵连,就被道武帝给杀了。
又过了二十多年,道武帝的孙子拓拔焘继了大统,当了皇帝,几年后又恢复了史馆,然后让一个叫崔浩人的主持修撰国史。这样又过了差不多二十年,崔浩在邓渊《代记》的基础上,领着一帮子人又搞了一个《国记》出来。
崔浩这个人才艺通博,究览天人,很是干练,深得太武帝拓拔焘宠信,官做到了司徒(大约相当于国务院总理),还被封为东郡公,权力很大。他这个人据说做事很凌厉,得罪了不少鲜卑贵族,有时甚至连太子拓拔晃的意见都听不进去。他后来大概是有些膨胀,有些飘飘然了,经不住人撺掇,让他“刊石立衢”,“欲彰浩直笔之迹”。他还果真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碑林,把他主持修撰的《国记》刻在了石碑上,广而告之。
这个碑林就在大马路的边上,引起往来的很多行人观看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都到太武帝面前告状,说崔浩有意“暴扬国恶”,又指责《国记》“备而不典”。太武帝震怒,就把崔浩给杀了,一起株连灭族的除了同族的清河崔氏,还有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以及河东柳氏等。另外一起修史的秘书郎吏、长历生等那些下属也未能幸免,一起被杀的有好几百人,史称“国史之狱”。 自此以后,北魏历史上又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设史官这个职位,可见这个事情的影响有多大。
按田余庆先生在《拓拔史探》里的考证和推测,邓渊的死,就是他修的《代记》里记载了拓拔先祖们好多乌七八糟的事,忤了道武帝的逆鳞,才招来了杀身之祸,以至于后面二十多年里朝庭都没有设史官一职。到了太武帝时代,拓拔焘又让崔浩等人来干这个事情。可很多人都是邓渊一案的亲历者,所以这事一开始进展很慢。后来拓拔焘又专门给崔浩颁了一诏,让他来主持干个事情,还特地要求“务从实录”。按田先生的分析,正是因为“邓渊史狱遗留下巨大影响”,“所以后诏才强调“务从实录”,实际上是太武帝亲自承诺不会重复出现邓渊史狱,以安史臣之心。”
可是伴君如伴虎呀,崔浩不光是自己死的很惨(说是在押赴刑场的途中,关上囚车里的崔浩被几十个士卒往头上撒尿,“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而且还被灭了族,连带着跟他一起干事的下属也遭了殃。连田先生也感叹说“希君之旨以实录为依归,以直笔相标榜者,终于栽倒在直笔之下!人主的复杂心态使希旨者祸福无常,给史学造成祸害,问题不正出在分寸之间吗。”
唐朝的刘知几在《史通·序传》里说过,“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这是一句很意味深长的话,意思就是隐藏坏的一面,陈述好的一面,所言真实不假,那就是真实记录。
好比一个人,一辈子干过很多事,有好事也有坏事,甚至干过的坏事更多,也更恶劣,但修史的人,只是如实的记录他干过的好事,坏事一字不提,那这个人在历史上呈现出来的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同样的一个王朝也是这样。
其实在历史上,不止皇权会干预修史,朝庭中很多有权势的人物也会想到利用国史来巩固家族地位,荫及子孙,然后通过各种手段威逼利诱史官们在修史的时候为他们的先人说好话、作佳传,当然前提是这个王朝的寿命得足够的长。史官们也是人呀,哪能人人都有司马迁一样的操守,大多数人也只好“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这个限于篇幅就不在这里一一举例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