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经略湖北的“加油”文化渊源(张继才/姜 倩)
——张之洞经略湖北的“加油”文化渊源
张之洞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洋务运动后期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改革家、教育家。他的事功主要在湖北,其事业的巅峰也在湖北。除了1867至1871年在湖北出任学政之外,自1889年,他在湖北担任湖广总督18年。在这18年中,他以深邃的眼光、宽广的视野、非凡的胆略、坚定的意志匡济时艰,锐志革新。他缔造江汉政绩最著,推动了武汉乃至湖北的近代化。湖北近代化起步较晚,落后发达省份约30年,但张之洞锐意进取,使湖北后来居上,武汉也驾乎津门,直追沪上。张之洞为什么能建功武汉、成就湖北?人们在探索他成功的密码。无论怎样,他的作为与其成长的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与其价值观形成时期的环境息息相关。换言之,与他价值观形成时期他的父亲在兴义府培育的“加油”文化大有关系。“加油”文化是黔西南的文化标识,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其精神特质是“守正笃行,久久为功”,其丰富的内涵可以从多角度解读。这样的探讨可以进一步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
一、家国情怀:“能挽河山”与“缔造江汉”
张锳、张之洞父子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具有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和胸怀。
张锳迁建试院,捐资兴学;加固招堤,抵御洪水;修筑道路,联通广西。他治理兴义府,鞠躬尽瘁。在任时勤政爱民,功劳卓著,“宣宗闻其能,特召对”。张锳千古留名,载入史册,民国《安龙县志》称赞他“大功之速且伟”,民国《南皮县志》称赞他“为国为民以死勤事”。
湖北兵工厂即汉阳兵工厂
张之洞经画恢弘,综理微密,筑铁路、开矿山、办工厂、建学校、练新军,缔造江汉,造端宏伟。他的幕僚辜鸿铭说:“文襄自甲申后,亟力为国家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辞世,皇帝上谕褒扬他:“服官四十余年,擘画精详,时艰匡济。经猷之远大,久为中外所共见。”溥仪帝师陈宝琛为他写了墓志,称赞他“公抱体国之忠,救时之略,膺疆寄垂三十年”。当然,张之洞出任封疆大吏时,中外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他总督两广前,法国以越南为跳板,向我国广西渗透。他奉命主政两广,抵御法国侵略。张之洞运筹帷幄,重新启用能征善战的老将冯子材,招纳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痛击法国侵略者,捍卫国家领土,巩固祖国边疆。张之洞主政湖广时,甲午战争爆发,他积极呼吁抵抗日本侵略者,不仅出谋划策,而且支援前线。两江总督刘坤一奉命率军北上后,他署理两江总督,在东南沿海积极布防。这也是他的家国情怀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无论在怎样的条件下,他都维护民族利益。
张之洞的远大抱负孕育于兴义府,受他父亲影响很大。从小他就对父亲敬佩有加,十一岁时撰写的《半山亭记》充满了对父亲的敬仰之情。当然,他的老师胡林翼、韩超也是志存高远之士,对他也有影响。他的抱负在他十二岁编的《天香阁十二龄课草》中就有多次流露。《吊十八先生文》高度赞扬十八先生为国尽忠的气节。在《送景幼嘉之官黄平序》中,他提出,为政一方,至少应该做到政简刑清、狱讼衰息,时丰岁稔、政通人和。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胸襟和抱负,实属难能可贵。黔西南与武汉两幅楹联是“加油”文化对张之洞熏陶的经典例证。“携酒一壶,到此间畅谈风月;极目千里,问几辈能挽河山。”这是张锳远大的抱负。“昔贤整顿乾坤,缔造皆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米欧遥。”这是张之洞广阔的胸怀。两副楹联可谓异曲同工,精神实质一脉相承。可以说,在耳濡目染中,张之洞胸怀大志;在文化熏陶下,张之洞积功兴业。《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报道张之洞逝世的消息时,称赞他“是一个纯粹的爱国者”。
二、重教理念:“最得士民心”与“兴学爱士”
张锳、张之洞父子治理地方时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特别重视兴学育才,这是他们的治理理念。
张锳重视子侄辈的教育,延聘名师硕儒教育下辈。但是,他更加重视士民的教化,因为他是具有浓厚家国情怀的地方官员。在《植桂轩记》中,他说:“余植桂,卜郡士贵。郡士,吾子民也。郡士贵,犹吾子孙贵也。卜贵,何必定私吾子孙?愿斯桂也,早芳而多花,异日郡士科名之盛,有如此桂,是吾愿也。”张锳似乎感动了上苍,1852年秋,六桂齐放,兴义府六人中举,包括张锳之弟和儿子张之洞,在兴义府的历史上,这是空前的。张锳在教育上颇多建树,他重修兴义府学,兴建义学2所,修建府城书院、普安盘水书院、册亨书院、安南县书院、兴义县文庙,迁建兴义府试院。最令人感动的是流传至今的知府“添灯油”劝学的故事。《南笼续志》称赞他“最得士民心”。张锳兴学重教,兴义府文风甚盛,人才脱颖而出。张锳任职兴义知府10余年间,兴义府城考取举人20余名、进士2人,选拔各类贡生近40人。
张之洞主持修建的武泰闸
张之洞总督湖广前有过多次主管教育的经历,任湖广总督后,他大力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他最早成立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学务处,使教育管理做到以专责成,为全国各地仿效,直接推动了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他率先在湖北制定新学制,直接参与主持清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学制——《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他在湖北推行教育兴革:进行书院改制,建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建立起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专门教育、特殊教育的近代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人才,使湖北成为清末近代教育最发达的省份。他还是废除科举制的重要推手。张之洞被誉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徐世昌评价他:“兴学爱士教子尤有法,大学士之洞其最著也。”辜鸿铭说:“文襄之知人爱才,有大臣风度也。”张之洞病逝,四川总督赵尔巽上奏,请求将其在四川学政任内兴学育才事绩宣付史馆,编入列传,得到批准。
张之洞很好地传承了父亲张锳重视教育的治理理念,换言之,张之洞传承了“加油”文化的精髓。张之洞从小生活在兴义府,接受优良的教育,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27岁时参加殿试并一举夺魁(探花),这是张锳家庭重视教育、言传身教的硕果。张锳在兴义府营造的兴学重教的良好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张之洞的世界观。实际上,少年张之洞对父亲兴学重教是十分钦佩的。在11岁所作《半山亭记》中,张之洞就赞美道:“岁在壬寅,家大人先守是邦,文风雅俗,焕然一新。”张之洞无形中吸收了父亲的思想。收录于《天香阁十二龄课草》中的《送景幼嘉之官黄平序》中,张之洞就有这样的爱士施仁的观念:“惟崇经讲道,爱士施仁,说礼乐而敦诗书,先器识而后文艺。”
三、民本思想:“惠政感之深”与“利国便民”
张锳、张之洞父子虽出生于官宦之家,但他们没有官家子弟习气,他们关心民瘼,有深厚的民本情结。
张锳心系百姓,为民解困。他捐建义学2所,使府城义学增加到6所,目的是解决少数民族子弟读书的困难。他将棉花业和原有田租所得用于解决6所义学的办学经费。他甚至悉心规划,为各级各类学校筹资,“自发蒙至成进士,均为筹定资费,俾寒士得图上进”。他筹措资金,修建兴义府进入广西的道路70里,方便百姓来往。他培修招堤,使府城免遭城东北陴溏海子洪水的浸灌,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他兴修义仓,积谷备荒,增修育婴堂,抚养孤幼。张锳以“多善政”载入史册。《南笼续志》给予很高的评价:“郡官历任之久,莫锳若;惠政感之深,莫锳若;以及保危城平大乱,大功之速且伟,尤莫锳若!”百姓感恩于他:“合郡士民乃私立’遗爱祠’以祀之。”
在湖北,张之洞经纬万端,政绩斐然,在交通、经济、教育、军事、市政诸方面,均有建树。他建立了湖北近代工业体系,其中,汉阳铁厂为亚洲最早的重工业,武昌纺织四局奠定了湖北仅次于上海的纺织业中心的地位;他建立的新式学校之多、类型之全,使湖北教育在全国处于领跑地位;他建立的湖北新军无论是规模还是素质,都仅次于中央军北洋新军,湖北枪炮厂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枪炮厂。他的市政改革推动了武汉等城市市政近代化。张之洞辞世时,上谕称:张之洞“凡所设施,皆提倡新政,利国便民”。陈宝琛《张文襄公墓志》曰:文襄公“用财浩繁,大率取之中饱私规,不竭民膏,不侵库款”。的确,他的作为并非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造福百姓。例如,他修马路,“交会通达,民生日阜”;他建纺织四局,“此为富民塞漏上策”。水利工程是最典型的惠民工程。他在武昌修筑了武金堤和武泰闸、武青堤和武丰闸,在汉口修筑后湖长堤40余里,排除水患,保护百姓安全。在长江堤岸修筑后,江边有大量土地可供耕种。他成立清丈局,清丈土地后,开出优惠条件,提供给百姓耕种,解决百姓生计。在建筑堤防的同时,张之洞疏浚河流与湖泊,将积水排除在堤外,防止城市内涝。水利工程集除弊与兴利于一体,武泰闸建成后,四乡船民纷至,土特产品云集,武泰闸、鲇鱼套居民陡增,商业繁荣。
张锳、张之洞还有一个惊人的相似点,即在一地任职历时久。张之洞曾谢绝调动到京城或外地,原因是他不想湖北的事业半途而废,而是想一鼓作气,实现他的愿景,这还是“加油”文化熏陶的结果,因为,张锳也曾是这样做的。他的民本思想、为民情怀是“加油”文化氤氲浸淫的产物。在兴义府成长时期,他目睹父亲的勤政,钦佩父亲的政绩。张之洞《半山亭记》中有相当深的印记:父亲主政,兴义府“文风雅俗,焕然一新”,原因是父亲“固常与民同乐”。他能体会父亲的心境:“题诗励士,把酒劝农,四境安恬,五谷垂颖者,则太守之真乐也。”
四、廉洁精神:“以廉洁而知名”与“廉正无私”
张锳、张之洞父子都久历疆寄,位高权重,主政一方,独当一面,有相当多的发财机会,但张氏父子却两袖清风,甚至一贫如洗。
张锳在兴义府任知府10余载,收入不菲,但他勤俭自守,捐俸银却很慷慨。他捐建了两所义学,为当地少数民族子弟提供读书的机会;他迁建试院,捐银1000两;他主持纂修《兴义府志》,捐银2000两付梓。他约束下属,严禁贪腐。他教育家人,崇尚节俭。民国《安龙县志》褒扬他“以廉洁而知名”。
当年兴建中的抱冰堂
张之洞素性节俭,廉洁自律。他捐俸银于公益,数量远超其父,当然,张之洞收入也远远高于父亲。他早年做京官时,官微权轻,收入菲薄,生活拮据。捉襟见肘时,甚至靠夫人典当衣物,置酒以过生日。后来外放,担任六年多的考官和学政,考官和学政都是美差,此生足以衣食无忧。但张之洞却廉洁自持,不义之财不取一分一毫。赴武昌上任总督伊始,张之洞便主动约法三章。1889年10月27日,他致电江夏、汉阳两县官员,告知其抵达武昌的时间,要求“所有公馆及衙署供应,务从简朴,不得华侈繁费,不准用绸缎、锦绣、燕菜,不准送门包、前站礼。一切使费,所有到任供张,如有公款,无过领款之数,如无公款,用过若干,开账照数发还。万勿故违,致干未便”。赴任仅数月,他又将督署常年供支银两千元充公,交给善后局。按惯例,这笔钱由他自己支配,这是合法合理的。1890年夏,湖北水势汹涌,张之洞一面告诫各地备汛,一面亲赴荆江险段查勘水情、堤工。7月7日,他致电荆州道、府和江陵县官员,告知将到荆州查勘堤工,自己一行人食宿在军舰,无需由地方提供服务。张之洞乘着轮船奔赴石首、荆州等地,又由陆路赶往钟祥、潜江等地,再从汉水回到武汉,一路风尘仆仆,劳累奔波半月之久,以致在酷暑中大病一场。驻节武昌时,他还规定,宴会的标准严格控制在五簋八碟,不得超标。无论是做湖北学政,还是做湖广总督,以他的法定收入与合理收入,完全可以做到锦衣玉食,至少应该比较体面。但张之洞却经常面临家庭的经济压力,因为,张之洞乐善好施,捐资兴学、印书、赈灾,十分大方。1905年,畿辅有200名学生来湖北读书,每人每年需交学费100元,张之洞便将他兼任湖北巡抚的公费银14 800两交给学务处,充当这些学生的学费。实际上,张之洞个人是完全可以支配这些资金的。有学者不完全统计,张之洞一生捐款至少在271 275两白银以上,还不包括一些登记数额的捐款。张之洞如此清廉,自然获得广泛赞誉,其被认为“清操俭德,直大臣中所仅见”。他辞世时,上谕褒扬他“廉正无私”。他廉洁奉公的事迹载入史册,《清史稿·张之洞列传》称赞他“家不增一亩”。
为纪念张之洞治理湖北政绩而建的奥略楼
张之洞廉洁奉公的美德不仅源自他父亲在兴义府任内培育的廉洁风气,更主要的是源自他的家传。张家数代为官,清廉自持,家风醇正。张锳教育家人:“贫,吾家风,汝等当力学。”张之洞在优良家风中,受到教化和熏染。他对父亲的清廉是敬佩的,对清官是向往的。父亲去世时,他作《铜鼓歌》以示哀悼与怀念。诗中赞美了父亲的高洁品德:“此诗述德因爱物,子孙永宝当不佻。藏之宗祏无忘在莒事,亦知乃祖乃父于国宣勤劳。剖符领郡三十载,不蓄长物甘萧条。”即是对父亲的赞美,又何尝不是自身的追求。
晚清末造,政局杌陧,社会动荡,张之洞总督两湖,成效卓著,实属不易。诚如他的弟子张继煦所说:“费无量数之苦心,经无量数之痛苦,铢积寸累,卒能有所成就。”“故公一生精力,几尽用之于鄂,而事业之展布,亦于鄂为最著。”张之洞之所以能缔造江汉,成就湖北,推源溯流,“加油”文化是重要源头。
(本文为黔西南州2025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社科专项课题第10号“张之洞缔造江汉与’加油’文化关系研究”研究成果)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9期」
「张继才,武汉工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湖北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姜倩,武汉工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武汉工商学院湖北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黔西南千年琴事与“加油父子”的礼乐琴韵
1987年在兴仁交乐汉墓出土的东汉陶器——抚琴俑。1990年被选送北京参加中国文物精华展,且为该次展览海报选用文物
古琴是我国最早的弹拨乐器,相传为伏羲所创。据文字可考之史,其渊源至少可追溯至周朝,距今已有三千多年。《诗经》中“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等句,皆为明证。汉代古琴大师桓谭在《新论》中云:“琴,神农造也……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至南宋刘籍《琴议篇》,更将“琴”升华到“琴之道”,赋予其通神明德、修身养性、翼赞王化的崇高意义,是为“为义之琴”。
一、盘江千年琴事
在南北盘江环绕的黔西南,最早的文字见于兴仁交乐、兴义万屯汉墓群中的青铜铭文与汉砖砖塑文字。而此地古琴之最早实证,当推1987年在兴仁交乐汉墓出土的一件东汉陶器——抚琴俑。此俑高34厘米,琴长35.8厘米,整体为立型空心灰陶,男俑载巾,身着右衽长衫,跪坐抚琴。其坐姿并不是汉代标准双膝并拢接地、毕恭毕敬的“跽坐”,而是相对随意的“跪坐”。尤为精彩的是,其面部蚕眉杏眼,短须高鼻,满面春风,喜容可掬,栩栩如生。抚琴俑出土不久,就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1990年被选调北京参加中国文物精华展,现珍藏并展陈于黔西南州博物馆。经研究,兴仁交乐汉墓年代下限约在汉桓帝、汉灵帝间(147—189年),由此确证,早在两千年前,承载儒学精髓的礼乐文明已进入黔西南大地。
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藏“南皮张氏家藏”《五知斋琴谱》
然而,随着三国时期群雄逐鹿中原,伸向黔西南的汉文化触角被截断。蜀汉政权为经略包括黔西南在内的西南地区,采取了民族自治形式的羁縻制度。顾颉刚、史念海著《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引用相关史籍记载:“蜀平南蛮后不置州县,即以夷人理夷事,夷民感其信任之诚,誓不复叛,遂无后顾之忧。后世羁縻州县土司制度之建制,尚不脱诸葛公之遗意也。”后世的土司制度即源于此。黔西南的历史轨迹随之转向:唐时属南诏国;至宋,很大部分区域成为自杞国境;元朝虽一统云贵,但土司制度依然没有改变。这段漫长的岁月,黔西南区域的汉文化在此期间几乎绝迹,毋论风雅琴事不可寻,连重大事件的文字记载也寥寥无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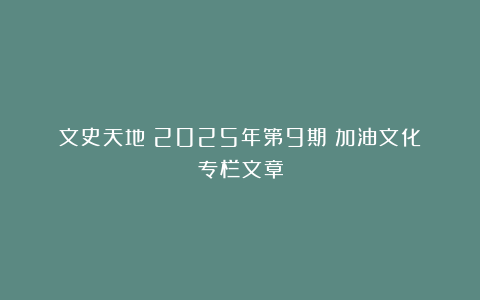
明朝朱元璋平定云贵之后,对当时的贵州西部采取“开一线以通云南”的治理政策。是时,黔西南大部地域,分属中央政权所置贵州上六卫之安南卫、普安卫。至此,礼乐记载再见于世。嘉靖三十年(1551年),普安州知州高廷愉在续修《普安州志·学校志》中有云:“礼乐之兴,实系于人。生于斯者,应竭尽其力,不懈追求;而为官者,应激励并振兴之。如此,则中原文化之传承,岂能逊色于他人?”可见时人对礼乐复兴之期许。
可是,礼乐文明的覆盖与教化终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设立卫所保障“开一线以通云南”的政策之下,除了卫城、所城所在地,终明一代,黔西南大片区域依然为大小土司所辖,教育发展步履维艰。直至雍正九年(1731年),贵州巡抚张广泗才疏请获准建南笼府试院,南笼知府黄世文于府署旁兴建试院,后迁于东门外大佛寺山麓。惜嘉庆二年(1797年)毁于兵燹,次年,南笼府(治今安龙县)改名兴义府。嘉庆六年(1801年),试院改建于城东三里许。然而,选址府城外的试院,居民寡少,兼无旅店,士子感慨跋涉辛苦。加之号舍不足,损毁失修,致使屋材朽坏,渐显破败。
庆幸的是,礼乐文教之种,终在黔西南留下点点星火。由张锳编纂、成书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的《兴义府志》就录存诸多弹琴、咏琴、借琴遣怀之诗句与故事。如兴义府前街人桑湛《松棚》,贞丰人张庆长《绝命诗》,普安人邵元善《退思室记》,南笼人景殿飏、李琼英之《寄怀郑竹香》《秋琴》《秋城》,等等。其中琴诗,意境深远,深得琴学精髓,所涉《流水》《白雪》《幽兰》等曲目,演奏难度系数较高,足见当时黔西南文士非止于抚琴自娱,其琴曲鉴赏与演奏技艺或已达相当水准。《兴义府志·隐逸传》记载明代普安万历丙子举人杨念祖“渊懿博雅,恬退不仕,日弹琴赋诗自娱”,即为一例。
《兴义府志·名宦传》记载,临桂举人廖大闻,道光十八年(1838年)署兴义县知县,其专咏兴义县之风土人情之长诗《黎峨杂咏》里有:“……三年边俸道如何,轮指冬春两度过。琴筑争鸣犹响水,烟云设色仰黎峨……”诗里的“轮指”,即古琴右手指法,三指在同一弦的同一个位置次第作“摘、剔、挑”,连发三音。“琴筑”则指古乐器琴和筑,古人常弹琴击筑而歌。《史记·苏秦列传》记:“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廖诗描绘之声景,隐然透露出彼时兴义区域礼乐氛围之余韵。
二、一代名知府的礼乐再造
黔西南教育勃兴、礼乐重光之转机,始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是年,直隶南皮(今河北沧州南皮县)人张锳赴任兴义知府,携眷而至。据张之洞幕僚许同莘所著《张文襄公年谱》载:“……续娶朱夫人,嘉庆甲戌进士四川和州知州临桂朱绍恩女。道光十七年丁酉八月初三日,朱夫人生公(引者注:张之洞)于兴义府官舍。道光二十年庚子,公四岁,朱太夫人卒。太夫人善鼓琴,遗琴二。公既长,对琴辄流涕……”(按:张之洞实生于贵阳六洞桥,朱氏并未至兴义府。许同莘所记地点有误,然据张之洞诗文记载,其母善琴并遗二琴之事属实)。
中国嘉德2022秋拍的张之洞旧藏古琴
知府张锳甫一莅任,即躬身践行,大兴礼乐。其首倡善举,即为兴义府学子夜添灯油,助其苦读。目睹城外旧试院之破败景象,张锳旋即倡议新建。经与府属士绅、州县及普安厅商议,张锳率先捐银千两,于府城内旧东门直抵北城墙处购地近十亩,兴建新试院。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十三日,规模宏阔、建筑精良之新试院落成,计有房舍209间,几案帷褥皆备,时誉“甲于天下”。其二堂门楹,仍悬嘉庆四年(1799年)知府陈熙藩所题楹联:“坛坫重新,说礼乐而敦诗书,满郡无非桃李;文思广被,听弦歌如游邹鲁,连城尽乐薪槱。”此联意境,正与张锳之志契合。
知府率先垂范,治下学风蔚然。张锳到任当年,安南县即重建莲城书院;次年,贞丰州建成册亨书院,普安县建成盘水书院;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张锳在任期间,尚未置县之新城(今兴仁市)亦建成培风书院。兴学之举不止于此:新试院落成,张锳将各州县所捐剩余银两划回。如兴义县余银五百两,即令知县周湜与当地士绅购田,以其岁租充作兴义文武童生参加府试、院试之卷费,永解学子后顾之忧。
张锳于《咸丰兴义府志·学制》中欣然记曰:“圣朝文教遐宣,兴郡虽苗疆,彬彬弦诵,有邹鲁遗风矣……”
“彬彬弦诵”之盛景跃然纸上。书院与古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即相得益彰。肇始于唐、兴盛于宋的书院,以传承儒家经典、弘扬文化为己任,尤重道德修养与学术精研;而古琴,则凝结着古代文士“清、微、淡、远”之审美理想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儒家情怀,是其精神追求之象征。二者在文化内核上高度契合,共彰华夏文明之精髓。书院清幽雅致的建筑环境,为古琴提供了绝佳的演奏空间;而古琴艺术融入书院教育,则成为涵育学子综合素质之重要途径,不仅提升其艺术修养、审美情趣与道德品格,更能调节身心,缓解课业之压力,培养专注与恒心。礼乐相济,文质彬彬,书院遂成古琴文化传承与滋养的沃土。
张锳所倡之“加油”夜读,更因礼乐之兴而倍添华彩。《兴义府志》收录张锳自撰《植桂轩记》,详述一桩雅事:“余守兴郡,十余年于兹矣。忆昔道光二十二年,为郡士建试院,拓高轩,选佳士,与儿辈弦诵其中,多士琴书安雅,雍雍如也。余顾而乐之,手植六桂于庭,因以名轩……咸丰二年,上距植桂之年越十年矣。旋秋闱揭晓,登第者人之数符桂数,亦六,多昔弦诵轩中者。郡士四:徐子世德、胡子尔昌、缪子振经、张子德俊;又其二,则余弟甘苹,子之洞,捷北闱者也,人符桂数,奇矣哉!……”由此可知,张之洞少时即浸润于书院弦歌雅韵之中,琴声书声交织,为其日后宏阔人生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
三、少年张之洞诗文里的西南琴韵
自幼受书院琴韵熏陶成长的张之洞,既承正统儒学之精髓,又深沐礼乐文化之芬芳。其母朱夫人早逝遗留下的两张古琴,成为他生命中最深沉的印记,伴随其一生。直到晚年,他都把生母留下的两把古琴带在身边,有诗云:“梦断杯棬泪暗倾,双琴空用锦囊盛。儿嬉仿佛前生事,哪记抛帘理柱声。”琴,已化为他对慈母的无尽追思。
张之洞对礼乐辅翼教化之功的深刻体认,亦得益于其师承。恩师胡林翼于《论语衍义》中明言:“礼乐者,国家之元气。礼乐一日不变,则国家一日不衰。方古昔盛时,君作于上,臣谋于下,乘时应运,德位崇隆,而犹不敢苟。故材艺兼长,《周官》未成全帙;父子皆圣,《雅》《颂》必待数传。盖必使出之自我者极于精详,而后被之于人者同归陶淑,此先进之礼乐也。”兴义府城珠泉书院讲席童翚,亦为张之洞师,其《企石山房诗存》中有《省垣寓楼即景》:“谁家调轸试琴声,按谱初弹手尚生。一碧天光凉似水,疏帘不卷月阴清。”由此可知,童翚不仅善琴,更悉琴道。又有《题朱晓山学博消夏图》:“古琴挺三尺,修竹森万竿。看竹不一问,抚琴良独欢。”师辈言传身教,琴中之道已深入少年张之洞之心。
少年张之洞对于琴之“弦外之音”,已深有体悟。咸丰四年(1854年),即其十七岁在兴义府所作课草,全册诗文186首中,咏琴之作竟多达20篇。如《舜在床琴》:
竟入他人室,何来逸韵闻。徘徊聆雅奏,恍惚见都君。
不改挥弦乐,空烦下石勤。床宜名不死,琴自谱南薰。
摄注销炉篆,桃笙展簟纹。操时聊解愠,眠处即看云。
莫堕湘娥泪,休矜傲弟勲。怜他颜忸怩,和气与氤氲。
诗中“都君”即指舜帝。《史记·五帝本纪》载,尧禅位于舜时,“乃赐舜纟希衣,与琴,为筑仓廩,予牛羊”。此处之琴,实为权力象征,故舜父瞽叟与弟象谋害舜后,首要争夺之物便是此琴。舜即位后,以尧所赐之琴作《南风歌》,“南风”“南薰”之象,寄寓了对政治清明、民生安乐之热望,开“弦歌治国”礼乐时代之先河。
其另一诗作《乘桴浮海》则云:
竟舍苍生去,言从沧海深。三山闻落木,一叶似飞禽。
鹿任中原逐,龙蟠大泽吟。风云无际会,身世此浮沉。
祇载诗书去,相偕剑佩临。荒凉千里目,悲悯两人心。
丛桂香多露,扶桑葚满林。师襄如可访,重与理牙琴。
此诗既抒逐鹿中原、风云际会之壮怀,亦表心系荒凉、悲悯苍生之幽情。末句“师襄如可访,重与理牙琴”,则饱含对礼乐育才功能的深切认同。《孔子家语》载,孔子学琴于师襄子,其悟性令师襄叹服。后因诸侯争霸、“礼坏乐崩”,师襄子愤而弃官,隐遁海滨。张之洞此典,寄寓了对重建礼乐秩序的深切渴望。
《论语·阳货》记孔子之叹:“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春秋末期,礼乐徒具形式,诸侯只求排场奢华,而失其根本精神。孔子强调,先王制乐,旨在涵养民德、导引和睦。乐虽借钟鼓而鸣,必先有内心之和顺愉悦,方为真乐。若失此本心,纵使钟鼓铿锵,亦不过虚有其表。夫子对此舍本逐末之痛心疾首,令少年张之洞深有共鸣。古琴所承载的礼乐真精神,亦令其终生眷恋不忘。
光绪元年(1875年),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编撰《书目答问》,于《子部·艺术类》中,特为学子开列《琴操》《琴史》等著名琴学典籍,将古琴文化作为“艺”之重要部分郑重纳入,足见其对此道之珍视。
黔西南州兴义笔山书院陈列馆中的古琴表演
纵观张之洞一生,琴非仅为抒情寄志之具,更是其精神操守之象征。其诗文中常以琴喻志,借“清音”象征士大夫之耿介。他所推崇的“清流”政治,主张“持正守静”,其内核正与古琴“中正平和”之道相通。在其三十多岁任湖北学政时,留有《题伯牙台》诗:“瑶琴已碎有余哀,知己谁为冠古才。流水高山人不见,野花香到伯牙台。”慨叹世道多戕,知音难求。而其在晚年诗作中,屡以“孤桐”“素丝”自况,彰显其坚守节操之志,古琴在其精神世界中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见。面对晚清动荡时局,其忧患与担当愈加深沉,光绪三十年(1904年),已六十七岁的张之洞自南京过芜湖时,有《过芜湖吊袁沤簃四首》诗云:“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双井半山君一手,伤哉斜日广陵琴。”再次以琴寄怀,痛忆庚子事变前与爱徒袁昶谈诗论琴,其乐融融,而今人琴俱亡,论琴与谁?谈诗更无人。琴,已成其一生中安顿心灵、寄托无限感思与家国情怀的载体。
结语
清《五知斋琴谱》云:“自古帝明王,所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咸赖琴之正音是资焉。然则琴之妙道岂小技也哉?而以艺视琴道者,则非矣!”琴韵所关,礼乐所韵,乃修齐治平之志。昔日知府张锳重视礼乐,劝学兴教,化育一方,张之洞承继其父为国育才之理念,为近代中国之教育发展,作出诸多贡献;今日之黔西南,承续张锳、张之洞父子“加油劝学”精神与文教传统,力行“文教兴州”战略。千年古琴之雅韵,穿越时空,依然缭绕于“康养胜地、人文兴义”的高质量发展晴空之中,诉说着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根脉与不竭的精神源泉。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9期」
「杨曼,职业古琴教师,交乐古琴馆负责人,黔西南州古琴非遗项目立项人;杨雷,古琴文化传播人」
版式:刘 丹 刘 丽
责编:王封礼
审核:姚胜祥
总监:丁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