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瘠甲于天下”是西海固历史上的代称,1972年,联合国粮食开发署将西海固列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评价,如今西吉已成为西部福地。由于复杂历史的变化和生活条件的反射,成就了西吉诸多文学人才。如火仲舫、郭文斌、了一容、马金莲、马存贤、尤屹峰、赵炳庭等,都已成为全国知名作家,西吉县被中国作协命名为全国“首个文学之乡”。
2023年一次机遇,火仲舫先生赠予我他再版的长篇小说《花旦》,对该作品我认真进行拜读,雷达、雷抒雁、高洪波、毕飞宇、叶广芩等名家的点评和石舒清的《序言》首先吸引了我。雷达评论说:“这是一部长期酝酿的有准备之作,作者在努力还原历史与生活之时,始终内在地高扬着理想的精神,遂使《花旦》洋溢着不可遏止的激情和源源不断的动力。”石舒清在《生活的魅力》的序言中坦言:“我读《花旦》,始终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结实、辛辣,像西海固的许多东西那样,给人一种货真价实感。”他们都是全国知名人士,不会轻易对一部作品下结论的。我读《花旦》,感同身受。西海固的风土人情像行云流水一样,随着阅读思维在心中徜徉,使人欲罢不能。无独有偶,时隔十多年,他一连创作出版了好几部文学作品,据说,仅长篇作品就达10部,加上散文、纪实文学、剧本等,达到五六百万字,实话说,我都搞不清他究竟创作了多少作品。令人欣喜的是,最近他又推出了一部长篇小说《“花旦”外传》。说实话,我还没有来得及品读,就被网上的消息所吸引,从美籍华人张佐堂教授的序言中,我领略到了这部《“花旦”外传》与《花旦》的相互关联和异同来。两部作品的主角都是出身于西北的艺术才俊“花旦”,她们的命运都多舛,也以“西北民俗表现为蓝本”,作品对黄土高原人文肌理的细腻描摹,都可圈可点。然而,两者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却是“同工异曲”,前者的主人公齐翠花遭爱兵痞骚扰和世俗偏见的挤压,处处受困,而后者李婉荣则跌入了贪官妙设的陷阱,把青春抛洒在异域他乡。从两部作品的表现手法领会,《花旦》和《“花旦”外传》以及其他文学作品,绝非简单的文学叙事,而是火仲舫以笔为犁,深耕地域文化的结晶。其乡土文化价值与创作责任感,在原著的细节铺陈中更显厚重,本人特别喜欢,在此发表一点自己的感想和认知。
一、乡土文化价值:不止于“呈现”,更在于“活化”
火仲舫对西北乡土文化的书写,跳出了“罗列民俗符号”的浅层模式,而是将文化基因融入人物命运与故事脉络,让濒临被遗忘的传统“活”在文字里。
原著中对“秦腔”演绎场面的刻画堪称典范。不同于一般作品仅提及秦腔的表演形式,《花旦》和《“花旦”外传》都以相当的篇幅详细描摹了秦腔艺人的“打戏功”——从清晨五点的“压腿踢腿”到“鹞子翻身”的技巧细节,什么是“搜门”,什么是“豹子头”,什么是“三锤”“七锤”和“倒四锤”,作者都一一道来,从后台化妆“勒头”时的麻绳缠绕力度到演出前“开嗓”用的冰糖与胖大海,正如石舒清在一篇文章中所言:《花旦》中齐翠花为招弟的化妆,堪称“化妆的说明书”。甚至记录了老艺人传下来的“戏词口诀”:“唱苦不抢板,唱乐不飘音”。《花旦》中“打路”“鬼怨”,写出了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真谛,《“花旦”外传》中的《打神告庙》,那舞出梨花的水袖和跌落神坛接着一个凌空觔斗,再来一个“卧鱼”,这些细节不仅还原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秦腔艺术的传承密码,更通过主角“花旦”在现代社会中坚守秦腔艺术的挣扎,折射出传统艺术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存困境。读者既能从文字中触摸到秦腔的艺术温度,也能理解这门技艺背后承载的地域文化精神——那是黄土高原人“苦中作乐、刚柔并济”的生命底色。此外,作品对西北“婚俗”的书写同样极具价值。火仲舫通过《花旦》《“花旦”外传》及其他作品中对传统婚俗的反思——既认同其中“重情义、守本分”的内核,又反对“朝三暮四”和“彩礼攀比”的陋习,让传统婚俗不再是静态的文化标本,而是成为探讨“传统与现代如何共生”的载体,赋予了乡土文化当代思考的价值。
此外,作品对西北“婚俗”的书写同样极具价值。火仲舫通过《花旦》《“花旦”外传》及其他作品中对传统婚俗的反思——既认同其中“重情义、守本分”的内核,又反对“朝三暮四”和“彩礼攀比”的陋习,让传统婚俗不再是静态的文化标本,而是成为探讨“传统与现代如何共生”的载体,赋予了乡土文化当代思考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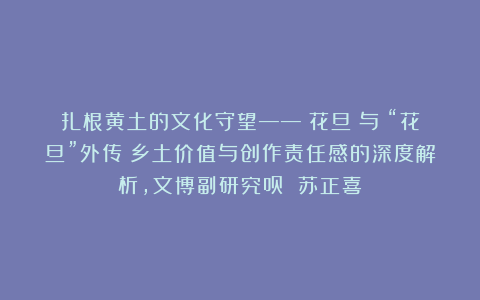
二、创作责任感:不止于“记录”,更在于“传承”
火仲舫的创作责任感,既体现在对地域文化的“抢救性记录”,也体现在对文学青年的“托举式扶持”,这种双重担当在原著及作者的创作实践中清晰可见。他已高龄,而且参加社会公益事业,还义务培养文学后备人才,如此多的作品,他是如何完成的?精力从何而来?最近读了一篇郭宁的文章,才知道了其中的一些情况。文章认为:火仲舫作为宁夏文学的重要代表,其创作实践不仅展现了西北大地上的风土人情,更折射出时代变迁中的社会现实与人性探索。他的文学世界根植于西海固这片曾经苦瘠天下的土地,却在这片文学沃土上开出了绚丽的花朵。从文本内部看,《花旦》中的齐翠花,尽管处处受制于人,但她仍然执着地带徒弟,传承秦腔艺术,红家三兄弟、红立贵、红招弟、红顺子、红琴英都是她一手教出来的秦腔新秀。而《“花旦”外传》中的李婉荣无奈走向异国他乡,但仍然带着她的头饰妆奁,也时不时唱一段秦腔,以表达心中对艺术的热爱。红琴英正是《“花旦”外传》中李婉荣的姥姥。显然,火仲舫通过文学创作,让这些“文化摆渡人”的故事被更多人了解、理解,以避免他们的技艺与精神随时间消散。这种“为平凡文化守护者立传”的书写,本身就是创作责任感的直接体现。
从文本内部看,《花旦》中的齐翠花,尽管处处受制于人,但她仍然执着地带徒弟,传承秦腔艺术,红家三兄弟、红立贵、红招弟、红顺子、红琴英都是她一手教出来的秦腔新秀。而《“花旦”外传》中的李婉荣无奈走向异国他乡,但仍然带着她的头饰妆奁,也时不时唱一段秦腔,以表达心中对艺术的热爱。红琴英正是《“花旦”外传》中李婉荣的姥姥。显然,火仲舫通过文学创作,让这些“文化摆渡人”的故事被更多人了解、理解,以避免他们的技艺与精神随时间消散。这种“为平凡文化守护者立传”的书写,本身就是创作责任感的直接体现。
从文本外部看,火仲舫的责任感延伸到了创作之外。据了解,在《花旦》及《“花旦”外传》的创作过程中,他将多年来的文学积垫运用到了极致。他从小参加村里的社火班子,从跑龙套到演角色,再到当导演、编剧本,历时十多年,并走访宁夏、甘肃、陕西等地的好多村落,收集整理了大量民俗口述资料,其中包括即将失传的“民间故事”“谚语歌谣”和传说。更难得的是,他在退休后还牵头成立了“西北民俗文化研究会”和“钟声文学工作室”,指导青少年挖掘本土故事,演绎红色经典。当有人问他:你这样分文不收,劳神费事,究竟为了什么?他的回答很简单:为了心里踏实!
1998年,从基层调往固原地区主持文联工作的他,在地区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与其他有识之士树起了西海固文学的大旗,培养了一大批崭露头角、势头旺盛的青年作家队伍,又提议在家乡西吉创建中国文学之乡获得成功。最近,在固原市文联、作协的大力倡导支持下,又顺应西海固文学发展态势,牵线搭桥,组成了作家与文学少年手牵手结对志愿服务活动,为全市百名作家进农家、进校园“双百”活动开了好头。总之,火仲舫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文学传承”的使命——不仅自己写出好作品,更要为地域文学的延续“搭梯子、铺路子”。
《花旦》与《“花旦”外传》的价值,早已超越了小说本身的范畴,它是一位文学创作者“守土有责、传薪有任”的生动写照,也是火仲舫用文字为西北乡土文化立起的一座座“里程碑”。火仲舫的文学情怀和创作精神给我们启示:真正有力量的文学,永远扎根于脚下的土地,永远心系着大众文化的传承。 二0二五年十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