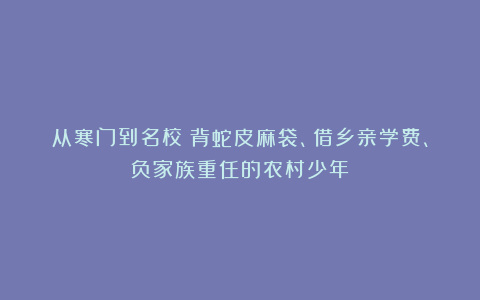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4060 篇文章
题图:来自作者。
作者:喻书琴,1979年出生于湖北小县城,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文艺学硕士、家庭辅导硕士;记者、译者、编辑、编剧、公益人;童年家暴创伤后遗症(PTSD)的受害者、疗愈者、记录者、研究者;铭心女性疗愈工作室负责人;北京橡树慈善基金会受虐女童救助项目发起人;长期深耕创伤女性疗愈和成长领域,译有《卿卿如晤》、《负伤的治疗者》等图书、著有《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一个女子的心灵成长》、《铁链下的突围与救助——当代中国女性纪实访谈》、《女孩在沉默》、《女孩在藏匿》、《女孩在逃离》、《她乡》等小说;2025年致力于九十年代大学青春自传体群像长篇小说《那时烟霞》的文学创作和影视探索。
第 一 卷
大一上学期:彷徨 法通
第 五 章:寒门学子
1997年9月6日,夜色苍茫。
从惠州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铁轨震颤,灯光昏黄,空气浑浊沉闷。顾明洋双肘抱膝,半坐半倚,身影在颠簸中略显僵硬。
这个来自广东潮汕小渔村的少年,肤色偏深,带着海风吹拂与烈日炙烤的古铜色。五官轮廓分明,眼窝深邃,下颌线条硬朗,眉宇间自有一股严肃之气,即便沉默不语,也让人觉得难以亲近。
然而,他一开口,低沉温厚的嗓音却如同海边湿润的夜风,裹着南方边陲的腔调,柔和、温吞、充满磁性,只是,每个词都要小心翼翼地斟酌再三。这独特的嗓音,打破了他外貌的严肃,透出几分质朴的暖意。
这少年身上带着一种安静的气息,不喧哗,不张扬,如同潮湿海岸边一块孤立的岩石,内敛而坚执。
▲ 顾明洋坐上40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供图:喻书琴)
19岁的顾明洋,是生平第一次远行。小学在本村,初中到镇上,高中到县里——在高考之前,他甚至从未跨出过县界。而此刻,他竟要独自辗转3000公里,奔赴遥远的北京。
为了省钱,他买的是最慢的绿皮火车车票。40多个小时的长途颠簸,他几乎未曾合眼,身体因戒备而始终紧绷。
每当有人经过,他便浑身紧张,死死攥紧红白蓝蛇皮袋的提手,还有腿上的斜挎布包——里面是捆着布条的5000元。
那是全村乡亲们东拼西凑出来的学费和生活费。他不敢有一丝疏忽,唯恐钱财和行李瞬间不翼而飞。
——————————
此刻,隔壁车厢隐隐飘来老式磁带机暗哑的歌声,是郑智化的名曲《水手》。
“……年少的我喜欢一个人在海边,卷起裤管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
《水手》是顾明洋最喜欢的歌,他眉心微舒,眼神里掠过一丝深深的乡愁。
是啊,年少的他,曾经一个人在海边,卷起裤管,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带着堂伯父送他的那艘手工小木船。
▲ 顾明洋拾捡贝壳(供图:喻书琴)
堂伯父身为村里的族长,曾牵着童年时代的他去看大海,海天辽阔,海鸥滑翔。
“明洋啊,我们潮汕男儿,天生要敢闯敢拼。等你长大成人,一定要搭船去看看海彼度(注:潮汕方言,意为那边)的世界……”
“海的彼度?是高山吗?是峡谷吗?是森林吗?”小小的他坐在沙滩上,听着海风,拾起贝壳,凝望小木船,心中生出无尽的憧憬。
磁带机的歌声继续回荡——
“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有另一个世界,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
那歌声仿佛点燃了他心中的火焰。从此,他更加努力学习,每次都考班里第一名。
除了功课,他家务活也格外殷勤,一放学就喂鸡喂猪,放鸭放鹅,拔草拔菜,甚至穿针引线贴补家用——他可是村里唯一一个会绣花的男孩子!村里长辈都夸他聪慧勤勉,知事懂礼。
▲ 顾明洋割草、砍柴、生火、喂鸡(供图:喻书琴)
中考时,顾明洋的第一志愿是报考中专,九十年代中期的中专在农村地区最受欢迎,录取分数也最高。因为一旦考上,三年后就可以参加工作,养家糊口。
但放榜时,他离中专的分数线偏偏还差3分。堂伯父托了人脉,说只要花笔钱,就能去附近的造船学校。
可家里翻箱倒柜,四处借钱,还是凑不齐这笔费用。明洋不忍让父母负担过重,便毅然劝阻:“阿爸阿妈,我还是上高中,努力考大学吧!”
他的中考分数远远超出当地重点高中的录取线,顺利进入县一中。
初到县城,高手如林,他难免忐忑,幸而入学第一次考试,他考入班里前三。这次小考,成了他人生路上无比重要的节点——它给了他第一次进入陌生世界的信心和力量。
三年高中,所有学子卧薪尝胆,冲刺高考——那场决定一生命运的考试。谁不是寒窗十年,背水一战?
▲ 顾明洋紧张备战高考(供图:喻书琴)
他终于杀出重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政法大学。
报考法大,也是堂伯父的主意。这位略通文墨的老人沉吟点头:
“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两个字听着够气派!应该毋输北大清华咧。以后能进衙门,食皇粮,当公家人——就考它啰!”
——————————
磁带机的歌声继续回荡——
“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像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
名牌大学是考上了,可学费和生活费却成了心头的大石。明洋在院子里翻晒鱼干,望着父母四处张罗借钱的身影,心里一阵酸楚。所幸,乡亲们慷慨解囊,东拼西凑,总算借齐了5000元。
▲ 顾明洋父母筹借学费(供图:喻书琴)
父亲坐在门槛上,手里夹着一杆烟袋,黝黑的脸上布满风霜。声音低沉,语气凝重:
“兜仔(注:潮汕方言,意为儿子)啊,你下学年学费的事,莫挂心。怒海讨生活,没出路的。我过几日就去东莞食品厂做工,你堂阿伯在彼度(注:潮汕方言,意为那里),他会照应我。你只管放心去念书。”
母亲一边抹泪,一边低声叮咛,眼角红肿:
“兜仔,路上毋好(注:潮汕方言,意为不要)同生人乱讲话,也毋好喝生人递的水。我在你秋衣褂里缝了个小袋,钱都放好了,你要小心点。火车上小偷多,提防着啊。到了学校,就快快去找潮汕同乡会,遇到事,记得揾老乡帮衬(注:潮汕方言,意为请老乡照顾)。”
村里最年长的叔公领着他踏入“顾氏宗祠”。宗祠门口镶嵌墨色对联一幅:“海邦肇绪尊先泽,鲤湖承祈续后昆”,横批则是“源远流长”。青砖厚墙在岁月里沉静无声。
祠堂内光线昏沉,几缕晨光透过木窗的雕花缝隙,落在先祖牌位的朱漆匾额上。檐下青铜香炉之上,檀烟袅袅升起,顾明洋跪于蒲团,额头触地的一瞬,氤氲的香火气息渗入胸臆,他忽然感到,肩头那一道任重道远的无形压力。
▲ 顾明洋在顾氏宗祠祭祖(供图:喻书琴)
叔公从兜里掏出一卷带着汗味和烟味的毛票,硬塞进他手里:
“明洋啊,你考大考嗰几日,叔公有去顾氏祠堂,向列祖列宗烧香拜老爷,求老爷保贺(注:潮汕方言,意为神灵保佑)!这回真个保贺咧,你是咱庄头头一个考上大大学的男仔,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啊。
这点小盘缠,是全庄头乡亲们一点心意,你就收落,毋好推辞,听着无?”
随后,叔公又从包里取出一只盛着井水的旧输液瓶,捧出一小块用塑料袋和黄线盛包扎的黄土,一并郑重地递到他手里。
“明洋,呢个呢,叫’乡井水、乡井土’,到了北京,你要是水土不服,就去你学校边仔揾井(注:潮汕方言,意为大学附近找口井),把老家水和土洒落去,保你——大吉大利呢。”
宗祠门口,送行的人影渐渐聚拢。几位阿爷阿婆也颤巍巍伸出手,将一包包简陋的点心塞到他怀里。浑浊的眼睛里闪着殷切的光:“点心拿着,路上慢慢吃。等你念完大学,做了公家人,咱村里阿弟阿妹们,还得仗着你多帮衬呀。”
顾明洋望着他们干瘪如柴的手指,满布沟壑的脸庞,佝偻的身影如田埂上折弯的老树。他喉头一紧,泪意翻涌,却只是默默颔首,郑重与他们道别。
——————————
“亲爱的旅客朋友们,列车已到长沙站……”
绿皮火车车轮轻轻颠簸,长长的走道里,一位长发粉裙的女孩推着行李箱款款下车,裙摆与车窗透进的夕光一同摇曳。
顾明洋的心蓦地一沉——安妮?
他又瞬即自嘲摇头。此女身形略丰,而安妮更纤瘦些;只是那一袭长发,一抹粉裙,恰与记忆中的倩影重叠。
安妮。
长发飞扬,粉裙飘逸的安妮;家住市区,每天骑着单车往返学校的安妮;在隔壁班窗前安静落座写字的安妮。
高一那个薄暮,他埋首课本,抬眸,便看见窗外清丽淡雅的她。顷刻间,少年的心湖被微澜点碎。
▲ 顾明洋看见窗外的女孩(供图:喻书琴)
从此,他特别留意,几乎每日都会从那个窗口远远望着她。上课、考试、上课,、考试,这就是明洋三年高中机械生活的99%,只有剩下的1%,是因安妮而萌发的青春期悸动。
不过,三年里,他们几乎没有说过话。唯一一次交集,是他作为本班数学课代表,去给隔壁班的数学老师送资料,安妮正好站在数学老师身旁,冲他淡淡一笑。那一笑,飘渺又遥远。
学业的重担、城乡的距离、背景的鸿沟,将他这份朦胧情愫锁于心底,止于唇齿。
高考放榜,他和县城同学道别后,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沿河而行,竟远远看见安妮和一个男孩,在黄昏中牵手漫步。那个男孩应该就是传说中她的男朋友吧!
▲ 顾明洋意外邂逅女孩和其男友(供图:喻书琴)
安妮也看到了顾明洋,再次冲他淡淡一笑。那一笑,依然飘渺又遥远。
那一刻,他心里五味杂陈,感慨万分,那一幕,像是为他的高中三年画上句号,也令他心底的那份朦胧情愫悄然合卷。
或许,每一个男生的高中时代,都和顾明洋一样,在书山学海的苦行僧生涯中,曾远远地,默默地,怯怯地,凝望着一个长得像安妮或者沈佳宜的女孩。
她们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会永远停驻在少年视线的尽头,终生定格为他们远眺的白月光,心底的朱砂痣。
——————————
“亲爱的旅客朋友们,列车已到达终点站北京西站……”
列车进站,车门开启,乘客蜂拥而出。顾明洋背着九十年代民工进城惯用的红蓝白大蛇皮袋,被人潮推搡着向检票口挤去。
▲ 顾明洋到达北京西站(供图:喻书琴)
检票员是一位大嗓门红袖章的中年妇女,板着脸,声音冷硬:“你买的是半票?有大学录取通知书吗?拿给我看看,没有的话,可得补全票啊!”
“有的有的。”顾明洋手忙脚乱,把行李上上下下翻了个遍,居然都找不到!
他额头直冒冷汗,最后才发现,那张被汗水浸湿得有些模糊的录取通知书,竟然就搁在外套里衬的口袋里,真是虚惊一场!
检票员挑眉,看了他一眼,漠然地摆了摆手:“行了,走吧!”
只是,那凌厉的眼神像一根针,刺痛了他的自尊。这座庞杂、陌生、似乎处处充满严厉审视的大城市,会接纳他这个来自遥远小渔村的少年吗?
磁带机的歌声继续回荡——
“总是一副弱不禁风孬种的样子,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是啊,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
离开北京西站后,顾明洋又换乘市区公交,辗转抵达海淀区学院路一座中规中矩的苏式楼房前。
然而,门卫保安却摇手告知:“这里是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本科生部在昌平哪。”
昌平?那是哪里?顾明洋一时怔住,心头茫然。
虽然身心俱疲,仍得继续奔波。终于,他等到了那辆传说中著名的345支公交。车厢里人声鼎沸,拥挤不堪,他费尽气力才挤上去。
▲ 顾明洋追赶345支(供图:喻书琴)
345支一路昏天黑地,尘土飞扬,望着车窗外单调荒凉的郊区景象,他心中既迷惘又震惊——自小幻想的“海的另一边”,不是高山,不是峡谷,不是森林,而是一个叫昌平的郊野……
——————————
当他拖着那个红白蓝相间、鼓胀得几乎要裂开的蛇皮袋,踉踉跄跄走到校门口时,已是汗水淋漓,浑身酸痛。
法大门前,一辆辆小轿车来来往往,衣着光鲜的新生们在父母陪伴下谈笑风生。顾明洋下意识地抖了抖满是尘土的旧球鞋,又伸手理了理因长途奔波而油腻的头发。鲜明的对比如同冷风拂面,他心头倏然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自惭与孤寂。
然而,下一秒,当他抬头仰望横梁上方“中国政法大学”那几个熠熠生辉的大字时,猛地挺直了腰杆。
因为他知道,进入校门的这一刻不仅仅属于他自己,也属于他的父母、他的家族、他的宗族,更属于3000公里外那个对他寄予厚望的小渔村。
磁带机的歌声继续回荡——
“耳畔又传来汽笛声和水手的笑语,永远在内心的最深处,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梦,就是考出去,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让家人和乡亲们过上好日子。这个梦,支撑着他熬过了小学、初中、高中,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接下去,还有大学最后这四年。
顾明洋深吸一口气,拖着沉重的行囊,迈着孤单的步子,走进校门,暗暗告诫自己:心无旁骛,努力治学。
▲ 顾明洋站在法大校门口(供图:喻书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