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 侵权必究
□ 苏培栋/ 文
林村原本叫土村,蜷在无垠山坳里。后来,一片林子毫无缘由地生长出来,村子便改了名。村里人丁不旺,隔三差五,总有户人家会出点意外。清晨,本该泛起鱼肚白的天空,却沉淀着一层灰霾。我从院子东侧的窗户望出去,就能看见那片林子。林子里的每一株树都高达千尺,每一片叶都阔及数十米,它隔绝了阳光,从外界望进去,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幽暗。周边雾气浓得化不开,雾里仿佛有流光旋转,诱人前往。村里的老辈却说它美,说里面有长翅膀的鱼、三个头的鹿、吊在树枝上的鸟、九条尾巴的猫、会说人话的狐狸。我心里直犯嘀咕,只当是老人家的诳语。
“你爸现在是村长,什么时候把那杆枪拿来给我们瞧瞧?谁不想进林子看看呢?”阿利嘴角还沾着饭粒,就跑到我耳边喋喋不休。是的,村里有一杆枪,和林子一样,从我爷爷那辈就有了。爷爷曾是村长,在村里一言九鼎,这枪便由我家保管,代代相传,如今到了父亲手里。
我扭过头,不愿看阿利的嘴巴一开一合,那像两口深井,总想把人看穿。我从未见过那杆枪。并非不想,只是每次提起,父亲总会厉声喝止。我此生大概都忘不了那个夜晚——昏暗的钨丝灯滋滋作响,父亲半张脸陷在阴影里,狰狞如野兽。“我怎么会知道那枪的来历!我怎么会知道他经历过什么!”我心底呐喊。
“我说过多少次了,我拿不到那杆枪。”
“阿平,怎么和朋友说话呢?”母亲从内屋撩帘出来,手上还滴着水,应是刚洗完碗,“阿利,快进来坐。”
内屋的地板光可鉴人,映出来客的倒影。一张巨大的方桌占了房间三分之一,阿利那张布满雀斑的大脸,也占了我视野的一半。
“阿妈,阿爸呢?”
“又到进林子的日子了,晌午才回。”说完,她又转身进了厨房,大概是去取水果。
阿利的目光,直勾勾钉在头顶的阁楼上。我知道,那里是存放那杆枪的地方,虽然此刻枪已被父亲带走。
母亲将三个橘子放在桌上,“家里没什么好东西,别客气。”“谢谢阿姨,我吃不了这么多。”阿利把橘子塞进他那件破旧衬衫的口袋,鼓鼓囊囊,最后一个实在无处可放,又讪讪地放回桌面。
“出去玩会儿吧。记住,别总跟村头破庙里那个老乞丐……”母亲的话音未落,我的半只脚已迈过门槛,内衬袖子紧攥在手心。她又在说阿勒。大家都误会他了,我不愿听人这样说他。
他们都骂阿勒不学无术,只会乞讨,我曾也这么以为。直到那天,他在破庙里向我招手。他很瘦,肋骨轮廓清晰可见,身子总像狐狸般佝偻着。心底有个来自远方的声音,催我走近。我递给他一个橘子:“阿妈说,多吃橘子,能长高,长壮,做顶天立地的人。”他慈祥地笑了,抚摸我的头。手掌布满硬茧,胡须像针,扎得我脸生疼。
阿勒其实什么都会。他会占卜,会吹笛,知晓许多不为人知的旧事。今天,他要给我讲老辈的故事。
顺小路向东,经过岔道,路过王大婶、张大爷、阿利家,便是村头。
王大婶坐在家门口布满青苔的石墩上,磕着瓜子。她脸颊的肌肉一抽一抽,舌头如鱼般灵巧卷出瓜子皮,又小又圆的眼睛盯住我和阿利:“疯娃子,跑慢些!碰坏我的新桌子,叫你阿妈赔!顺便告诉她,前儿借的鸡蛋该还了。”鱼鳃般翕动的脸颊上粘着一片瓜子皮。张大爷摇着破蒲扇,猫似的蜷在藤椅里,门口依旧立着那簇“鸡毛”,他坚称是凤凰羽,不许人靠近,说会蹭走他的福气,得用黄金来换。到了阿利家,他听说我要去找阿勒,翻了个白眼,两颗眼珠像剥皮的葡萄,自讨没趣地溜回家了。
我独自走向破庙。
“嗬,阿平来了,我算准了你这时辰到。”
我伸出一直攥着的手,用油纸包着的几张煎饼递给他。“我料到你也会给我带吃的,好孩子,可惜村里像你这样的不多。”
阿勒几口吞下煎饼,瘦瘪的肚子似乎隆起一些。他像狐狸般捋了捋胡须,开始讲述:
“林子出现后,你爷爷正值壮年,带着几个人就进去了。他们看见了长翅膀的金鱼、三个头的麋鹿、挂在树枝上的鸟、九条尾巴的猫、会说人话的狐狸。当时人们欣喜若狂,围着异兽跳起舞,那些生灵也一同欢跃。出来后,他们把见闻告诉了全村。后来,人们造出了枪。再次从林子归来,他们带回大量猎物,却也个个带伤——脸上是猫爪般的血痕,腹部有鹿角捅穿的口子,腿也瘸了,像是从高处坠落。’被异兽伤的?’’不是。’’那怎么回事?’’不知道。’没人弄得清。你爷爷说,他们为分猎物起了争执,走着走着就散了,林子里的异兽却突然狂躁起来。后来人们发现,凡是进过林子的人,身上都慢慢显出野兽的特征,先是爪牙,再是体毛,最后连性子都变了。可村里人只盯着那些猎物,对受伤者嗤之以鼻,说他们染了脏病。其实我知道……”
“后来呢?”我左手搓着右手,掌心全是汗,盼他往下说。却见阿勒猛地望向村口,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呜咽,胡须似乎都根根直立。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是父亲回来了。
“阿爸!”
——他们身上带着伤,咳嗽声不断。
再回头,阿勒已换上一副笑脸,小跑到王大婶面前,弓着腰讨饭吃。王大婶和路边的小孩却用石子砸向他瘦削的脊背。阿勒脸上依旧是那副笑,只是添了许多讨好与无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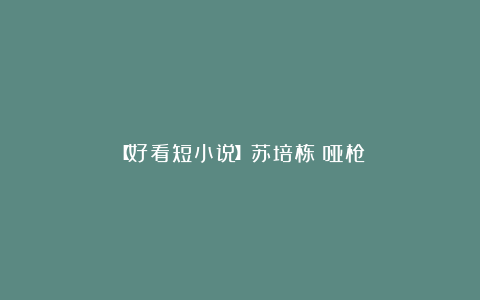
父亲用锋利的、能穿透我的眼神看过来,手掌推着我的后背,催我回家。我想多留一会儿,他却用那尚有余温的枪口,命令我回去。
他们带回许多猎物。我远远望着。王大婶依旧磕着瓜子,腮帮一鼓一吸。张大爷和几个老人争得面红耳赤,蒲扇徒劳地扇着风。我看那些猎物并无甚稀奇,只是凑近了,便有一股恶臭袭来,肮脏的血浸红了土地。我觉得整个村子都被笼罩在这片肮脏的红色里,里面住着一头头野兽,只剩下争夺利益的生存本能。
夜侵袭得很快,抹去了天边最后一缕残光。我躺在床上,失神地望着洁白无瑕的墙壁,听着隔壁父亲沉重的咳嗽声。一只野兽的影子,从门缝溜进来,投在卧室墙上,黑色的影糅合月光,将我吞没。心底那个声音又响了,催促我去看。我溜下床,赤着脚,蹑手蹑脚摸到虚掩的门边。只见那影子从父亲门缝钻出,大笑着,将手中的战利品塞进嘴里。天啊,我多希望这是一场梦!这当真是一场梦吗?我必须弄清真相。我能弄清吗?
父亲死了。村里为他举办了葬礼。
那个严厉的父亲死了,我再见不到他满载猎物归来的身影。
“这下,枪归你了。你说,林子里到底有什么?”阿利的大脸又杵到我面前。我盯着父亲的遗嘱,咬着干涩的嘴唇,一言不发。阿利的手探进我怀里,他的手很脏,玷污了我的内衬。他什么也没找到,带着愠色钻进内屋搜寻。葬礼上,邻里都来了。王大婶正和赵大爷、李大婶争论父亲后院那块地的归属,满地瓜子皮。张大爷从内屋踱出,手里提着一篮鸡蛋,摇着蒲扇,乐呵呵地溜出我家。身后跟着眼圈通红、躬腰相送的母亲。
是的,那杆枪归我了。此刻它正躺在我的床头柜里。通体银亮,一尘不染,光鲜夺目。可我知道,枪管里填满了血。它质感冰冷坚实,表面涂层光滑。枪不大,扳机刚好容下一指;枪又很大,大到我看不清枪口瞄准的远方。
我迫切想知道林子里发生的一切。未吃早饭,便溜到村头。阿勒痛苦地蜷缩在破庙角落。他看见我,脸上没了往日的笑意。
“你也是来打我的吗?”
胸口像压着巨石。心底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它清晰无比,催促我进入林子。
那片迷雾就在眼前,指尖已能触到那湿冷的质感。巨树参天,我确信自己能爬上去,我是村里最会爬树的孩子。我举起枪,透过准星观察。我听见鱼儿的翻腾声,却在空中——那是长翅膀的鱼,通体无鳞,鳃盖开合,在空中游弋,翅膀布满鳞片,在雾中闪烁微光。我举枪瞄准。旋即,我又看见身形庞大的异兽,天啊,是三头鹿,生着三对俊美的犄角,皮毛光滑如缎,每个头颅望向一个方向。侧旁传来吱喳声,原来树枝上倒吊着一只只无翼的鸟,用爪子紧紧抓住枝干。准星里又出现了九尾猫,蜷在树洞中,竖瞳戒备地闪烁。我的手指不自觉搭上扳机。脸颊因充血而滚烫,牙齿打颤,汗毛倒竖。天啊,我能在这些异兽的注视下狩猎吗?别想了,你一定能。我能收获颇丰吗?我可是村里最好的猎手。我能扣动扳机吗?心底的嗡鸣越来越响,耳鸣声尖锐起来,视野天旋地转,像醉了酒。我忽然觉得身上开始长毛,牙齿和指甲变得尖锐。我激动得想跳舞,肢体不由自主地摆动。
这时,我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你也是来打我的吗?”
啊,是那只会说人话的狐狸。它就那样凝视着我,原来它受伤了。现在,只需扣动扳机,我就能捕获一只会说话的狐狸。
我听清了,我终于听清了——心底是嘹亮的枪声,震耳欲聋。我不想听,我不要听!
胸膛剧烈起伏。
枪响了。我分不清是心底的轰鸣,还是手中的怒吼。我想到了阿勒,他此刻一定在占卜吧,他早算到我会来此狩猎。我听见悠扬的笛声,盖过了枪声。
我用尽力气抬高手臂,让子弹偏离——它击中了破庙常年漏雨的檐角。
我大口喘息,手掌震得发麻。我抓起枪身,一下,又一下,砸向坚硬的石头,直到确信它再也射不出夺命的子弹。
回过神来,内心一片沉寂。我却再也找不到那片林子。我仍站在村口的破庙前,眼前是蜷缩成一团的阿勒,脚边躺着他那支旧长笛。
清晨,雾散了。笼罩村庄多年的阴霾被阳光撕开,温暖而熨帖。人们沐浴在久违的日光下,或许不知发生了什么,却都舒展着腰身,打着哈欠,第一次感到清冽的空气润泽了疲惫的肺腑。
我知道,林子一定存在过。
人心中的枪,总有一天会响。
我将村里的青年召集起来。阿利不愿靠近,只在远处观望,两颗白眼珠死死盯着这边。我挺起胸膛,目光扫过众人,用嘹亮的声音宣告——
“这杆枪,是把哑枪!”
—— The End ——
苏培栋 高中生。喜欢读书和写作。
©原创作品 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