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摘 要
皇权交接关乎王朝治乱兴衰,是历代统治者无法回避的政治议题。宗法观念赋予皇权政治以家族底色,使得皇权交接与世袭统治的概念混融,形成独特的皇权政治文化,成为皇权的统治根基之一。皇帝与储君的关系是皇权政治体制下最为矛盾的内容。储君继承皇权的重要前提是皇帝离世,因而帝储之间难免相疑,成为皇权交接的重要难点。东宫体制变迁映射着储君权力变迁,汉朝至晋朝是东宫武装力量的上升期,南北朝至唐初是巅峰期,盛唐至宋前期是衰退期,此后则是消亡期。历代皇权交接充满变数,最受统治阶级推崇的大宗传承,占比不足半数。异姓革命、强臣禅代、皇室政变、权臣擅立等情况不绝于史,皇亲继承的执行情况与皇权政治走向基本一致。皇权交接是帝制中国政治生态演化、人文环境变迁、思想文化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
02
作者简介
李杰文,河南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博士后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5年第9期
目 录
一、中国古代皇权的基本指向与皇权交接的基本内涵
二、观念层面:宗法观念影响下的皇位传承
三、制度层面:以东宫武装力量的历史变迁为中心
四、历史实践:历代皇位交接的量化分析
余 论
皇权政治极具复杂性,皇权交接过程中充斥着博弈和角力,政治影响层累叠加。从家族世袭层面上看,旧皇的皇权难以完全交予新皇,权力和权威在历次转递中呈现总体减弱趋势;从政体发展层面上看,旧王朝的皇权被移接至新王朝,皇权在移替过程中进行权力重塑和权威重构。皇权权力交接事关统治权益的重新分配,影响接续皇帝对于最高支配力的掌控;皇权权威转移则事关统治秩序的再次确认,影响接续皇帝对于最终裁决权的掌控。作为维系政治体系稳定与延续的关键,皇权交接是洞察皇权政治规则的最佳切入点。皇权平稳交接有助于维护政治运行的实效和权力结构的完整,直接关系到中央权力的有效性和王朝统治的延续性;而交接过程中的派系斗争和权力真空则会削弱中央权威,引发政局动荡,一定程度上威胁着王朝存续。作为君臣必须面对的头等大事,皇权交接是派系政治和权力斗争的重要“引擎”。它不仅是皇帝向储君移交权力的过程,更是各方政治势力争夺资源和话语权的重要契机。作为王朝法统传续的必要程序,皇权交接也是考察政治文化与治理理念的“钥匙”。皇权的合法性不仅依赖于血统延续、继承程序、军事力量,还需要与时代政治文化和道德秩序相契合。两千余年的皇权政治史上,历代统治者对于皇权交接都极其重视。有鉴于此,本文从观念、制度和历史实践三个层面考察中国古代皇权交接的发展历程,以通史眼光观照历代皇权政治兴衰的内在关联,以期增进对古代皇权的理解和把握。
一、中国古代皇权的基本指向
与皇权交接的基本内涵
皇权是政治史研究中的高频词汇,皇权问题是史学重点研究对象。学界围绕皇权形成的研究成果甚丰,但对皇权的具体内涵尚无统一认知。吴晗将皇权理解为治权,作为治理国家的权力,这种皇权自然无处不在。李振宏将秦朝至清朝理解为“皇权专制社会”,在此语境下,皇权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既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又伴随帝制中国之始终。何晓明将皇权视为帝制时期“中国国家政治权力的特殊表现形式,是国家出现以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体现,是最高政治权力的个性化表达”,本质上还是一种治权。王瑞来对皇权的定义是,“皇权是皇帝制度的权力与皇帝本人的权力的混合物”。在此语境下,皇权包含皇帝权力和帝制政体两个层面,二者互为表里。卫广来对皇权的定义是,“皇权是秦汉时代形成的代表政治统一的最高国家主权”。在此语境下,皇权代表王朝推进政治统一的力量,皇权强弱体现在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上。胡恒将皇权置于基层社会治理维度加以考察,“传统中国社会的权力体系是金字塔式的,塔顶是皇帝,谓之’皇权’,又或有’国权’’王权’之称”,在此语境下,皇权包含皇帝权力和王朝力量两个层面,二者共同存在于“皇权专制社会”之下。
综观各家所述,皇权有三种基本指向:一是个体层面的皇权,即某位皇帝个人的权力。这种语境下的皇权最为具体,皇帝在政治场域中的各种作为都能展现皇权,这是政治制度史研究考察的重点。二是家族层面的皇权,即某一姓王朝的政治向心力和政治特质。央地关系变化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族王朝的盛衰。王朝统治力量的主导者不一定总是皇帝,皇权在不同政治角色间流转,形成军功贵族政治、门阀政治、宦官政治、士大夫政治等特殊现象,本质上都是派系政治。三是社会层面的皇权,即体系化的皇权专制政治体制。皇权处于全社会的政治核心、经济核心和文化核心,即使有时皇帝只在名义上拥有皇权,各类社会角色仍然惯性地辐辏于皇帝周围。
本文所考察的皇权,兼指皇帝制度下皇帝个人权力和王朝统治力量。王朝建立阶段,皇权往往是“卡理斯玛”(Charisma)型政治领袖个人魅力和皇权至上政治模式的混合物,皇帝的个人权力基本能与王朝力量对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后续皇帝继承“卡理斯玛”的血统,却不一定继承人格上的领袖特质,往往通过规章制度彰显皇帝个人权威和王朝统治能力。人治背景下,规章制度容易沦为一纸空文或谋权工具,从而滋生派系政治,各个派系围绕皇权开展权力斗争。由于家族和王朝之间的界限模糊,这里所讲的皇权,内涵并不固定,有时指皇帝个人权力,有时指王朝统治力量,有时兼指二者,具体指向要视政治形势而定。王瑞来对皇权的私权力属性和公权力属性界限不明的情况作过解释,“皇权的这种不明确性,其实是一种出于有意或无意的政治设计”,派系政治的突出表现是各方争夺以军权、财权、行政权为基础而衍生出的各类权力,这些权力均是皇权的外在表现。
皇权的核心内容在于对所有事务的裁决权和对所有人员的支配力。掌握至高裁决权自然需要树立至公至正形象,故皇帝号为天子,以示公允。不过,仅靠天命难以切实维护统治秩序,“权”的正当性要得到普遍承认,还需要“力”的加持。裁决权是皇权柔性的一面,支配力是皇权刚性的一面,裁决权和支配力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裁决权而无支配力,那皇帝便容易沦为政治象征物,裁决权终将遭到窃取;只有支配力而无裁决权,那皇帝便容易被斥为独夫民贼,支配力终将走向瓦解。因而,历朝皆培养和任用文官以保障皇权裁决的相对公允,培养和任用武将以保障皇权支配的贯彻落实。在“笔”和“刀”的协作下,皇权的裁决结果具备至善属性,皇权的支配力量具备至尊属性。可以说,谁能在实质上把控皇权,谁就能在皇权社会中无往不利,这便是历代参政者前赴后继谋取皇权的根本原因。
皇权政治的排他性决定了皇权交接总是伴随着权力斗争,从而备受瞩目。而且,皇权交接经常会与皇位交接混为一谈。一般情况下,皇权交接以皇位交接为界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皇帝选定和培养储君,同时避免被储君分权。皇帝寿命有限,为保证家族王朝的稳定延续,必须要选定权力的接替者。储君作为未来的皇帝,不可避免地会分割现任皇帝的权力,即使储君本人无心分权,从属于储君的政治参与者也会跃跃欲试。这是横亘在帝储之间的天然矛盾,往往引发父子相疑,致使皇权交接表现出残酷性。第二个阶段,新帝收拢先帝下放的皇权,重新分配政治资源。储君登上皇位后,政治身份正式转换为皇帝,政治利益的实现路径从分割皇权转变为集中皇权。新帝必须收拢权力以确保对王朝的实质统治,同时满足依附者得到合理报偿的政治诉求,否则他便只是某一派系攫取权力的工具。把控皇权是皇帝主导政局走向的必要前提,但是要使既得利益者甘心让渡权力,通常要经过权力斗争,因而皇权交接表现出凶险性。
特殊情况下,皇位交接与皇权交接以平行状态分别进行。太上皇、女主、权臣的存在皆能表明皇位交接与皇权交接不同步。太上皇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退位前便被架空,如唐高祖;一类是退位后仍掌实权,如清高宗。女主临朝情况较为复杂,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继任皇帝年幼,需要女主担当皇权过渡的重任,如宋朝刘娥、辽朝萧绰;二是女主恋栈不去,皇帝虚居皇位而不能控御皇权,如唐朝武则天、清朝慈禧;三是派系争斗激烈,由太后摄政应对皇位空悬局面,如辽朝述律平。最直观体现皇权和皇位分离之彻底的,是东魏权臣高澄的嚣张态度,他质问皇帝:“陛下何意反邪!”权臣擅权时,皇帝个人权力不振的现象不绝于史,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权相兜揽对政务的裁决权架空皇帝,如南宋右丞相史弥远矫诏废立,宋理宗“渊默十年无为”,而史弥远“擅权用事,专任憸壬”。二是军将借助对军权的支配力轻视皇帝,如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扬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三是权宦通过阻塞皇帝与外朝的沟通渠道来窃夺皇权,如晚唐宦官杨复恭出任枢密使、左神策护军中尉、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大权在握,甚至将唐昭宗视为“门生天子”。
总的来说,皇权交接从来都不只是皇帝和储君二人之事,它总是裹挟着各方矛盾,承载着各方期冀。各方的政治诉求不同,派系政治便难以避免。王瑞来认为,“派系政治不仅是士大夫政治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如果从派系政治的角度考察包括皇权在内的许多政治现象,几乎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我以为从派系政治的角度入手,是研究中国政治史的一个关键”。诚如所言,皇权交接过程中派系政治斗争的特性就尤为突出。皇位交接与皇权交接关系密切,皇位交接是皇权交接的重要程序,却又并非必要程序。皇权交接的过程有长有短,因时而殊、因人而异。有的皇帝在继位前便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对皇权的收拢,有的皇帝继位数年后才完成对皇权的收拢,有的皇帝终生未能收拢皇权。而皇位交接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短期内走完流程,既是政治形式,又往往成为派系矛盾集中爆发的契机,抑或派系斗争的结果展示。
二、观念层面:
宗法观念影响下的皇位传承
皇权政治绕不开“宗法”。自先秦至晚清,宗法观念深刻地影响着皇位传承,宗法关系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皇权交接的合法性。嫡庶、长幼、亲疏、贤愚等经典议题,均与“宗法”密切相关。
夏商周三代确立了王权在家族内部传承的政治规则。夏代王位传递主要有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叔终侄继三种形式。商代“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周代“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三代宗法观念渐趋增强,初步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度。
秦汉时期,宗法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秦国遵循嫡长子继承原则。秦始皇未立储君,根据陈胜所言“吾闻(秦)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推测秦朝仍然遵循嫡长子继承原则。汉高帝册立嫡长子刘盈为皇太子,晚年意欲易储,“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汉元帝亦有易储考虑,侍中史丹以死相争,进言“皇太子以適长立,积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臣子”。东汉经学家何休对继承顺位有明确解释:“適,谓適夫人之子,尊无与敌,故以齿。子,谓左右媵及侄娣之子,位有贵贱,又防其同时而生,故以贵也。”嫡长子继承原则已然成为宗法观念的重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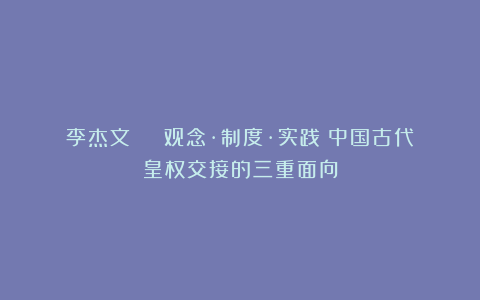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立嫡、立长、立贤各有利弊,于是,一些人开始反思嫡长子继承制是否足以适应现实需要。魏武帝意欲不唯嫡长,结合才干选拔继承人,引发朝臣反对,尚书仆射毛玠密谏:“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魏明帝传位幼子加速了曹魏覆亡,陈寿论曰:“古者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与。后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继,则宜取旁亲明德,若汉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准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系私爱,抚养婴孩,传以大器,托付不专,必参枝族,终于曹爽诛夷,齐王替位。”幼帝无法应对艰难时世,故陈寿对于嫡、长、贤三种继承人的选立标准有所反思。晋武帝发觉皇太子的才智不堪承接皇权,杨皇后进言:“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痴愚的晋惠帝以嫡长子身份继位,又引起晋人反思。晋成帝崩逝后,中书监庾冰与中书令何充各执一词,庾冰鉴于皇长子司马丕幼弱,提议拥立长君,何充宣称:“父子相传,先王旧典,忽妄改易,惧非长计。”最终以司马丕年幼“未堪艰难”为由,扶立晋成帝同母弟琅琊王司马岳。后燕成武帝段皇后鉴于太子柔弱,建议废嫡立贤。北魏实行长子继承制,司徒长孙嵩认为“立长则顺,以德则人服”。君臣出于现实关切,反思嫡长子继承原则的普适性,然而越嫡建储又使得同室操戈问题愈演愈烈,反衬出嫡长子继承原则的优势。
隋唐至五代时期,嫡庶之分严格,父子相继优先于兄弟相及,然而嫡子继承难以落实。隋文帝鉴于前代皇权交接纷争不断,与独孤后“誓无异生之子”,五子皆为嫡出,相当重视嫡庶之分。唐太宗主张“设无太子,则立嫡孙;若无嫡孙,即立诸子”。唐代对嫡庶继承顺位作了具体规定:“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无庶子,立嫡孙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孙。曾、玄以下准此。”按照优先等级排序,即嫡长子、嫡长孙、其他嫡子、庶子、其他嫡孙、庶孙。嫡次子以下诸子的继承顺位很低,五等爵位承袭时,嫡庶兄弟均无继承权,“袭爵嫡子,无子孙,而身亡者除国,更不及兄弟”。唐隆元年(710),李隆基政变夺权,唐睿宗嫡长子李成器以“时平则先嫡长,国难则归有功”为辞推让储位。唐玄宗以下诸帝(除唐德宗外)均无嫡子。唐德宗意欲废子立侄,宰相李泌劝其若必废子,不如立孙。唐宣宗晚年属意第四子夔王李滋,久不能决,崩逝后,左神策护军中尉王宗实矫立皇长子郓王李温。五代乱世,成年君主更能应对乱局。马楚、南唐奉行兄弟相继,马殷“遗命诸子,兄弟相继;置剑于祠堂,曰:’违吾命者戮之!’”李璟即位时“于父柩前设盟约,兄弟相继”。不过,即便亲子年幼,中原政权的皇帝仍然倾向于传子。后唐庄宗欲立年幼的李继岌,令其与侍中郭崇韬共同伐蜀,增加军功。后晋高祖临终前将幼子托付给宰相冯道,冯道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为由,改立皇侄齐王石重贵。后周世宗临终前,传位于年幼的梁王柴宗训。若皇帝不立皇后,则没有名义上的嫡子,嫡庶界限模糊,由掌握政治实权者控制对嫡长子继承原则的解释权。
宋辽夏金时期,皇位传承更加规范,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嫡子一般就是长子。宋代皇位传承合乎宗法观念。宋太宗按照长幼次序培养皇子,宋真宗传位独子,宋英宗、宋徽宗、宋孝宗、宋光宗均传位于嫡长子,宋神宗、宋度宗传位长子,宋仁宗、宋哲宗、宋高宗、宋宁宗、宋理宗没有亲子,择选旁宗入继。宋朝士大夫认为立嫡以长、立子以贵是“古今之正义也”。辽初宗法观念薄弱,辽太祖诸弟相继为乱。到辽太宗—辽世宗权力过渡时期,将嫡长身份作为宣传资源,辽世宗编造遗诏:“永康王,大圣皇帝之嫡孙,人皇王之长子,太后钟爱,群情允归,可于中京即皇帝位。”契丹王朝逐步接受嫡长子继承原则,辽景宗略过横帐皇族传位于子,辽道宗略过同母弟传位于长孙。西夏秉持嫡长子继承原则,夏景宗、夏毅宗、夏惠宗、夏崇宗、夏仁宗均册立嫡长子为太子,夏神宗无嫡立长,夏献宗无子传侄。金初尚有氏族部落遗风,“兄弟相传,周而复始”。最高权力按照嫡出兄弟的长幼次序横向交接,然后再纵向传承给下一代的嫡长子,唐长孺将之概括为“嫡子继承,兄弟相及”。金熙宗以金太祖嫡孙身份嗣位,得子后册立皇太子,开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金世宗完善嫡长子继承制度,嫡长子薨后立嫡长孙。金章宗希望遗腹子接续皇位,遗诏:“载惟礼经有嫡立嫡、无嫡立庶,今朕之内人见有娠者两位,已诏皇帝,如其中有男当立为储贰,如皆是男子,择可立者立之。”皇位竞逐者借助嫡长子身份谋取政治合法性,进一步增加了嫡长子继承原则在皇权交接中的分量。
元朝皇族内讧不断,皇位继承纷繁复杂,嫡长子继承制执行不力。元世祖为巩固自身合法性,自诩:“太祖嫡孙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贤以长,止予一人……实可为天下主。”镇远王牙忽都认为“世祖皇帝之嫡孙在,神器所当属”。元武宗自诩“次序居长,神器所归”。平章政事三宝奴认为“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闻有子而立弟者”。元文宗认为妥欢帖睦尔是“明宗之长子,礼当立也”。不过元朝皇室很少遵守嫡长子继承制,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相继的现象皆有。张岱玉道破了元朝皇族对待嫡长子继承制的态度:“随着中原的嫡长子继承制观念在蒙古统治者中间的传播,嫡长子继承制与幼子守产的观念成为汗位争夺者的双选工具,哪个有利于自己,就标榜哪一个观念。”嫡长子继承制只是被元朝皇族作为政治工具,并没有升格为观念认同。
明朝皇室以嫡子为正统,宗法观念深入人心。明太祖规定:“国家建储,礼从长嫡,天下之本在焉。”“惟帝王之子,居嫡长者,必正储位。”《皇明祖训》中具体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若奸臣弃嫡立庶,庶者必当守分勿动,遣信报嫡之当立者,务以嫡临君位,朝廷即斩奸臣。”明代历任皇帝加以遵循,上行下效,“凡公侯伯家,最尊嫡长”。明朝统治者以书面形式确立嫡长子继承制的合法性,也承继了此种继承方式的弊端。明亡后,王夫之反思嫡子继承之利弊:“立子以適长,此嗣有天下,太子诸王皆生长深宫,天显之序,不可以宠嬖乱也。初有天下,而创制自己,以贤以功,为天下而得人,作君师以佑下民,不可以守法之例例之矣。”历代统治者遇到的皇权交接难题再次回归。
清前期,旗主接受父死子继高于兄终弟及的观念。清中期,皇位传承由宗法观念主导转变为择贤而立,出现秘密立储形式。清太宗崩逝,郑亲王济尔哈朗认为“皇子即帝位,更复何言”,三等甲喇章京索尼认为“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清圣祖二次废储后开启了立贤模式。此后清帝秘密立储,皇帝无子时,“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清朝统治者实行秘密立储制度之后,皇位不一定由嫡长子继承,但宗法观念始终没有消散。
综上所述,宗法观念与皇权政治黏合得相当紧密,使得皇权交接成为历朝历代的普遍性难题。嫡长子继承制纵贯整个中国历史,每逢衰世,便有人反思其适用性。然而,各类政治角色生存于皇权体制下,无法跳脱自身立场,始终找不到替代方案。虽然历代统治者都试图求解,但从整个皇权政治的层面来看,他们所采取的政治举措均无法触及问题的根本,只可谓小修小补。
三、制度层面:
以东宫武装力量的历史变迁为中心
储君权力主要来源于皇权,权力强弱主要体现在东宫建制上。学界对于东宫制度的研究成果丰硕,各个主要朝代均有专论,故笔者仅措意于帝储权力分配视域下的东宫武装力量变迁,勾勒出皇权交接制度层面的变迁脉络。
三代时期,东宫制度已经完全形成,王位继承人有权监国抚军,“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以师、保、傅作为官属,“太子师、保、二傅,殷周已有。逮乎列国,秦(国)亦有之”。秦朝未设储君,缺乏配套东宫制度。汉朝在先秦师、保、傅的基础上增设东宫官属,配备太子宾客、太子詹事、太子门大夫、太子庶子、太子洗马、太子舍人、太子率更令、太子家令、太子仓令、太子仆、太子中盾、太子食官令、太子厩长、太子中庶子、太子卫率。后世东宫职官体系大体照此设置,因时增损。
东宫武装力量是储君权力的有力保障。汉朝未设专门的东宫武官,仅以太子卫率一人掌管门禁。曹魏东宫属官废阙,“唯置卫率令典兵,二傅并摄众事”,太子卫率开始成为东宫武装力量的核心成员。西晋增加太子卫率规模,东宫武装力量成形,“晋初曰中卫率,泰始分为左右,各领一军。惠帝时,愍怀太子在东宫,加置前后二率。成都王颖为太弟,又置中卫,是为五率”。刘宋东宫武装力量增强,主要武官有太子屯骑校尉、太子步兵校尉、太子翊军校尉各七人,太子冗从仆射七人,太子旅贲中郎将十人、太子左右积弩将军各十人、殿中将军十人、殿中员外将军二十人。南朝皆因循之。北魏亦设太子卫率统领东宫禁军,以太子步兵校尉、太子屯骑校尉、太子翊军校尉、太子常从虎贲督宿卫侍从太子。隋朝东宫沿设太子左右卫率,储君麾下可谓兵多将广,“左率领果毅、统远、立忠、建宁、陵锋、夷寇、祚德等七营,右率领崇荣、永吉、崇和、细射等四营。二率各置殿中将军十人,员外将军十人,正员司马四人。又有员外司马督官。其屯骑、步兵、翊军三校尉各一人,谓之三校。旅贲中郎将、冗从仆射各一人,谓之二将。左、右积弩将军各一人。门大夫一人,视谒者仆射”。左右卫率之外,还增设左右宗卫、左右虞候、左右内率、左右监门。东宫武装力量强盛,隋文帝开始猜疑储君,认为:“太子毓德东宫,左右何须强武?”唐前期沿袭隋朝东宫建制,“置詹事以统众务,则尤朝廷之尚书省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领众局,则犹中书、门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设官,有各率其属之意。崇文馆犹朝廷之馆阁,赞善大夫犹朝廷之谏议大夫,其官职一视朝廷而为之降杀”。武德时期,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争致名臣以自助”,东宫官员配置更加完备。玄武门之变后,太子李世民的东宫班底最为强大。
经历数朝发展,唐初东宫武装力量处于巅峰,帝储关系相对恶化。盛唐时期,皇帝着力打压东宫力量。自盛唐开始,东宫体制向非实体化发展,东宫武装力量急剧下降。唐玄宗为防范皇子夺权,营建“十王宅”限制子孙政治活动,东宫失去武装力量。武惠妃诈诱太子李瑛入宫除贼时,李瑛只能带着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和驸马薛锈披甲入宫。此后,东宫不再是“小朝廷”,“自唐世至于五代,东宫之职,王府之属,或总领佗务,或授左降分司致仕官,不专为宫府之任。若建置储嫡,诸王出阁,则宫府之职,多以佗官兼领及检校之。天宝后,武臣及藩镇牙校、幕府僚佐,亦多检校东宫之职,以为散官”,独立武装力量随之丧失。宋朝继续减省东宫属官,“诸司庶局颇令兼摄”。朱熹称:“今之东宫官属极苟简。左右春坊,旧制皆用贤德者为之,今遂用武弁之小有才者,其次惟有讲读数员而已。如赞善大夫诸官,又但为阶官,非实有职业。”太子诸率长官由宗室皇子充任,“中兴后不置,惟以监门率府副率为环卫阶官”。辽朝不设东宫,有皇太子惕隐司“掌皇太子宫帐之事”。金朝海陵王“初定东宫官署”,东宫护卫定员三十人。
元朝东宫武装力量再度增强。皇帝数次为东宫增置兵员,至元十六年(1279),“世祖以新取到侍卫亲军一万户,属之东宫,立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至大元年(1308),“命以中卫兵万人立(左)卫率府,属之东宫”,选入左卫率府的士兵俱是汉军精锐。延祐五年(1318),“以詹事秃满迭儿所管速怯那儿万户府,及迤东、女直两万户府,右翼屯田万户府兵,合为右卫率府,隶皇太子位下”。明朝“东宫官名多袭古”,东宫官员均为兼任,明太祖明确提出抚军监国是储君的天职,洪武十年(1377)六月,“命群臣自今大小政事皆先启皇太子处分,然后奏闻”。不过,明朝东宫不设卫率,储君没有独立武装力量,明世宗晚年“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太子朱载垕虽然忧惧,却无能为力。清前期储君没有独立武装力量,康熙朝太子胤礽两次居储长达几十年,最终却被清圣祖轻易废黜。清中期确立秘密立储制度后,东宫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综上所述,东宫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储君与皇帝的关系,东宫武装力量的损益经常引发政治变动。汉代确立东宫体制的基本模型,后续王朝加以沿袭。南北朝至唐初,东宫武装日益完备,由皇帝权力的衍生品发展为对抗性力量。盛唐以降统治者引前车之鉴,大力削弱东宫力量,储权遭到大幅削弱,以致矫枉过正,使得储君从皇权场域中消失。宋前期统治者重新设立储君,不为东宫配备武装力量,阶段性完成了皇帝对储君的制约。清中期皇帝秘密立储后,东宫制度失去生存土壤。东宫体制经历漫长的历史变迁,总体上看,汉朝至晋朝是东宫武装力量的上升期,南北朝至唐初是巅峰期,盛唐至宋前期是衰退期,此后则是消亡期。
四、历史实践:
历代皇位交接的量化分析
陈寅恪指出,“皇位继承之无固定性及新旧君主接续之交,辄有政变发生,遂为唐代政治史之一大问题也”。不止唐代,此论放之皇权政治史而皆准,只是政变程度各有不同。据浦薛凤统计,“几乎每一次继承即包含一次危机”。据谭平统计,“在中国从秦至清二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有2/5的皇帝是依靠嫡长子继位制登上皇位的”。以皇太子或嫡长子身份继位的皇帝不足半数,说明皇权交接充满变数。
皇帝与储君之间的猜疑和斗争,几乎贯穿皇权政治之始终。秦始皇确立皇帝制度后,不立储君。汉高帝鉴于“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即位初便定储位,储君制度随之确立。明人于慎行指出“今人主临御日,讳言储贰,自古然矣”。汉武帝疑忌太子,酿成巫蛊之祸。隋文帝猜疑太子杨勇,将东宫宿卫“有健儿者,咸屏去之”。唐玄宗怒于太子披甲入宫而一日杀三子。唐宣宗不愿立储,声称“若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后唐明宗亦不立储,抱怨“群臣请立太子,朕当归老太原旧第耳”。宋太宗立储后,埋怨“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金元皇太子更是“无一享国者”。明世宗不愿储君掌权,“朕疾未全平,遂欲储贰临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将提议太子临朝者黜落为民。清圣祖废储后,宣布“诸皇子中如有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宥”。皇帝对于储贰多加猜忌的原因之一是储贰弑君确有其事。宋文帝太子刘邵开弑君弑父先河,时人谓“穷弑极逆,开辟未闻”。隋文帝太子杨广的弑父嫌疑颇重,“中外颇有异论”。夏景宗太子李宁令哥弑父,“国主曩霄(李元昊)为子宁令哥所弑”。皇子弑君亦不乏其事,如清河王拓跋绍弑北魏道武帝,郢王朱友珪弑后梁太祖。
有鉴于此,笔者统计历代皇位交接情况,将皇权获取方式分为四大类:A创业开国,B皇亲继承,C皇亲自立,D臣僚选立。每一类又根据具体情况分为若干小类:A1非皇族出身的创业皇帝,A2非皇族出身的权臣政变自立;B1大行皇帝或太后指定的直系继承人即位——大宗传承,B2大行皇帝或太后指定的旁系继承人即位——小宗入继,B3皇帝指定的继承人即位——内禅;C1皇亲政变夺权,C2皇亲趁乱自立;D1臣僚议立的皇帝,D2权臣谋立的傀儡皇帝。详见下表:
表1 皇权获取方式统计表(前221—1912)
中国历史上朝代、皇帝众多,不乏闰朝、伪帝,本表只统计主要朝代的235位皇帝,具体说明如下:第一,只统计帝制时期,先秦时期不在统计之列。第二,王朝创始者不一定称帝,由于不涉及皇位传承,不能称为皇权交接。以下两种情况不作统计:一是权臣家族的权力递嬗,如魏武帝、晋宣帝、晋景帝、晋文帝、北齐神武帝、北齐文襄帝、北周文帝、后唐太祖;二是氏族部落、军事联盟的权力递嬗,如北魏、辽朝、金朝、西夏、蒙古、清朝等王朝的建国前史。第三,新朝、玄汉、桓楚、侯汉、西梁、武周、北辽、南明等闰朝,“十六国”、“十国”、大理等割据政权,刘劭、刘子勋、萧正德、萧纪、杨侗、杨浩等不被史家承认的伪帝,不纳入统计范围。第四,两次即位的皇帝,晋安帝、唐中宗、唐睿宗、元文宗、明英宗只统计第一次;身兼多种情况的皇帝,按照即位情况统计,如唐太宗实是政变夺权,计入C1;唐肃宗实是趁乱自立,计入C2;后周太祖将后周世宗立为嗣子,计入B1;宋高宗以宋孝宗为嗣子,内禅传位,计入B3;元明宗受元文宗邀请而即位,计入B3。第五,原本是权臣傀儡,却在即位后剪除权臣的皇帝,如宋文帝、北周武帝,按照即位时情况计入D2。第六,虽曰继承,实同创业的皇帝计入A1,有秦始皇、吴大帝、北魏道武帝、辽太祖、后唐庄宗、金太祖、元世祖、清太宗。第七,即位原因存疑的皇帝,姑且按照正史记载统计,如宋太宗等。第八,被废的皇帝被降级为王、公、侯,考虑到他们曾经实际在位,纳入统计范围。
统计所得数据是:A类:A1计15次,A2计10次;B类:B1计94次,B2计33次,B3计13次;C类:C1计22次,C2计7次;D类:D1计11次,D2计30次。皇亲继承(B类)是最常规的皇权获取方式,在历代皇权获取方式中占比达到59.57%。其中,大宗传承(B1)是皇权交接的最常见样态,在历代皇权获取方式中占比达到40%。不过,其他皇权获取方式不容忽视,无论是排除大宗传承后60%的占比,还是A类、C类、D类所占40.43%的比重,都表示皇权交接事务存在很大变数。接下来,再看历朝历代皇亲继承的执行情况(图1)。
图1 皇亲继承执行率趋势图(前221—1912)
秦汉时期,皇亲继承(B类)执行率为66.67%,皇权交接期间的政治变幻为后世王朝提供了参照。魏晋南北朝时期,执行率大幅下降,位于皇帝制度确立以来的最低点,若将“十六国”政权纳入统计范畴,执行率将会更低。隋唐五代至宋辽夏金时期,执行率相对稳定,从60.53%缓升至63.83%。这是因为该时段政权外部的威胁相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幅降低,皇权交接的矛盾与纠葛大多源自内部。若聚焦于唐宋时期,执行率达到64.52%,唐朝和宋朝分别达到80.95%和72.22%。不过,唐朝大宗传承(B1)仅占B类的58.82%,旁宗入继(B2)占29.41%,内禅(B3)占11.77%;宋朝大宗传承的占比更低,为38.46%,旁宗入继和内禅各占30.77%。元明清时期皇亲继承的执行率最高,尤其是明清两朝,分别达到87.5%和81.82%,这与皇权专制政体走向顶峰的历史大势基本吻合。
综合以上数据来看,皇帝与储君之间的矛盾几乎绵延于整个皇权政治史,秩序建构与权力斗争是皇权交接衍生出的一组矛盾。需要指出的是,以上量化统计结果只应作为一种参考,事实上,关于皇权交接的议题大多疑雾重重,仅靠数据无法阐述其详,政治参与者及历史记录者的讳言或缘饰等,都成为统计数据的“水分”。量化统计的意义在于为研究者分析皇权交接之际的具体政治情况提供宏观视角,便于在整体观照与个案探寻之间找出平衡点,为得到更加可靠的结论提供帮助。
余 论
“家天下”统治模式确立后,宗法观念主导着权力交接,嫡长子继承原则成为后世权力传承的经典参照。皇帝制度确立后,宗法观念一以贯之。在秦汉至晚清的时代变迁中,嫡长子继承原则或受推崇、或遭质疑,对于皇位传承的主导作用渐次增强。帝储关系是皇权交接的重要议题,储君掌握的武装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帝储关系。汉代建立了健全的东宫体系,魏晋时期东宫武装力量逐渐加强,储君具备与皇帝争锋的能力,唐初储君军事实力达到顶峰。唐玄宗大力打压东宫力量,盛唐之后,储君无力与皇帝抗礼。元朝东宫武装得以重振,明朝东宫复失武装,清中期开始秘密立储,东宫不复存焉,储君对皇帝的威胁解除。综合历代政治情况来看,两汉时期初步建立了皇权交接的基本秩序,魏晋南北朝时期交接秩序混乱,属于低谷期,唐宋时期恢复了交接秩序,步入缓升期,明清时期皇权交接更加有序,储君发动政变的风险大幅降低。
历任统治者接管政治权力和接续统治权威的努力,使得皇权政治的稳定性和皇帝权力的合法性得到延续,无论是政权内部的权力博弈,还是政权之间的正统争夺,都在不同程度上夯实了皇权政治体制的框架。皇权交接的完成既标志着一个阶段派系之争的暂时解决,又为新一阶段的派系之争埋下伏笔。各方政治势力的互动不仅决定着具体事件的走向,还对皇权政治的发展轨迹施加影响。皇权政治表现出一种周期性变动的特征,帝制政治思想与正统话语体系在一轮又一轮的皇权交接中不断得到重塑和强化,为后世王朝提供政治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讲,皇权交接是帝制中国政治生态演化、人文环境变迁、思想文化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