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town Central Plains
给在外打拼的家乡游子一个寄放心灵归宿的地方
乡土文学
作者 | 刘尚钞
原创 | 乡土中原(ID:gh_06d145e3125e)
小刘庄有两个生产队,分别是十八队和十九队,东墁十八队,西墁十九队。
在生产队的年代,每个生产队都要有一个集中设置的牛屋院,生产队里的牛和驴都要集中喂养。生产队的很多活动,都在牛屋院里进行。
牛屋院的主角是牛,老家叫ou,不叫niu。公牛叫牤ou,母牛叫虱ou。牛是生产队最贵重的生产资料,犁地耙地、耩地打场,几乎所有农活都离不开它。
小刘庄东墁的牛屋院就建在村子的东北角。牛屋院的西边是个大坑,南边是道沟,东南方向也是不规则的大坑。雨水丰沛的季节,牛屋院四周,一大半被水环绕,就像是一个半岛。
牛屋院的西南角,是一个简易便桥,勉强可以通过架子车。通过这个桥,牛屋院与村子相连。顺着水沟再往东,有两个漫水桥,枯水季节直接通行,有水的时候就趟水而过。
两个漫水桥,说是桥,其实就是地势比沟底高比周围低的硬路面,坑满沟满的丰水年代,在这里用干草作围挡,再糊上泥巴,可以逮鱼逮虾,水沟里可以扎蛤蟆。
(二)
牛屋院的整体布局是这样的。
牛屋是东西走向的一长排草房,大约有一二十间,坐北朝南,在整个院子的最北端,房后就是庄稼地了。最西侧,坐西朝东也有三间牛屋,房后是条水沟连着的大水坑。也就是说,整个牛屋呈“L”型,除了根基有几块砖外,清一色的土坯房,房顶早的时候缮的是黄背草,后来用的是麦秸。
牛屋的窗户是空的,除了通风,最主要的用途是牛把儿把牛铺里的牛粪从窗户里用铁锨甩到屋外。春夏秋三季都是敞开着的,冬天的时候用麦秸织的稿荐或包谷杆堵起来挡风。
牛屋的前面,是一个大粪坑,东西向长方形的,牛粪就倒在这里面,粪坑用于积庄稼地里的农家肥,围绕在粪坑周围,地上栽有很多木撅,用于拴牛,一个撅对应一头牛。粪坑的南边,是一个大末子堆,主要用途是给牛铺的地上撒干末子,相当于人的床铺褥子。
末子堆的西边,有一个大碾盘。直径可达两米的大碾盘,上面有一个可以绕中心轴转动的大石滚。由于碾盘很厚很重,人力根本就抬不动,就是破坏起来也不太容易。所以一直等到牛屋院消失,大碾盘始终都在。大概它是整个牛屋院里保存时间最长的老物件,二零零几年我离开家乡时记得它还在。
末子堆的东边,是一片空场地,我小的时候,曾经看到村子里的男劳力在这里磕砖坯,兄弟几个一齐干,用专用的木模子,一次磕出四块砖坯,用料是软硬合适的黄焦泥。最后能磕出上万块的砖坯,晾干以后送到村子东南地的窑上,烧出的青砖盖房子用,比土坯结实多了。
(三)
牛屋院的东南角,据村子里的老人讲,解放前的时候有一座小庙,后来被毁了。过去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庙,区别就是大小和知名度有差异。有庙就有神,村民们对庙都是很敬畏的,即使毁了,也没人敢在庙上盖房子。
庙址的北边,是一个高高耸立的大烟炕,方方正正的,足有两层楼房那么高,面积至少有四间堂屋那么大。不种烟叶以后,烟炕就废弃了,不过毕竟可以遮风避雨,里面放有砖坯、农具、柴禾等杂物。小时候,那里是我们理想的捉迷藏场所。
北侧长排牛屋再往东连在一起的,是保管屋,存放粮食等生产生活资料,相当于仓库,大集体时代家家户户分粮食就是在这里进行。保管屋里的地面是铺砖的,墙上用的砖也多,比牛屋的房子盖得气派多了。保管是村里的实权派人物,管吃管喝,饿死谁也饿死不了保管。保管保管,兜装满没人管。保管大多肥肥胖胖的,十八队也不例外。
保管屋再往东,是八十年代初建造的三间砖瓦房,比土坯草顶的牛屋高级多了,相当于现代建筑。这房子是牛屋院的东北角,也是整个村子的东北角。在这个屋内,安装有打面机器,有了它就不用驴拉磨磨面了,效率高多了。负责打面的人,叫“小党喜”,光棍汉,个子不高微胖,很壮实。打面的时候,弥漫满屋的粉尘,把他的睫毛、头发全都染白了。
生产队里的牲口,牛和驴最多。这是有原因的。
牛和马有很大不同,牛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卧着的,主人不赶它不起来,不过卧着可不是闲着,它要倒沫,就是把没有嚼碎的草料反刍出来,再细嚼慢咽一遍,整个过程能持续一两个小时。牛倒沫的时候,不要打扰它。一旦它不倒沫了,那就是生病了。不过牛很结实,很少生病。
马呢,大多数时候都是站着的,四条腿轮换着休息就可以了。马卧下可不是好现象,十有八九是生病了。
驴呢,和牛马都不一样,既可以站又可以卧,白天的时候四条腿轮换站着休息,到了晚上在驴棚里就蜷卧着休息,相当于进入深睡眠状态。但它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打滚儿,打滚儿是它的专属运动。
马爱动牛爱静,驴最爱闹腾,打起滚来不管不顾地乱扑腾。驴叫起来声音嘶长又难听,骂人说话声音大又难听,就称之为“老叫驴”。驴的名声一直不好,“一个槽里拴不住两头老叫驴”,关于驴的俗语几乎全是贬义的。像“脸拉里像头驴”“耳朵里塞驴毛”“驴屎蛋外面光”“懒驴上磨屎尿多”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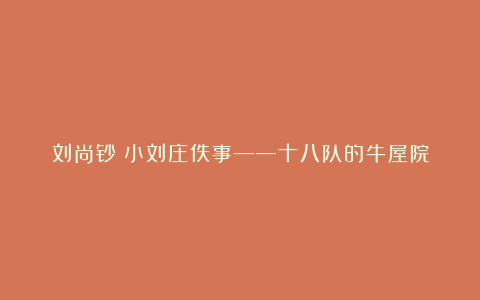
骡子是马和驴的杂交品种,兼具马和驴的优点,但它不会生育,骂没用的男人就骂他是“骡子球,没使处”。在农村有“铁骡子铜驴纸糊马”的说法,是说马的身子骨不结实,容易生病,不好养活。因此,生产队里牛和驴最多,马和骡都较少。牛耕地驴拉磨,各有所长,都离不开。
牛屋院的牛有很多,大约有一二十头。
大多数的时候,它们躺在大粪坑的周围地上,安静地倒沫。每头牛的脖子里都挂有一个铃铛,脖子动铃铛响。有时候为了防止它乱吃东西,会给它戴上牛笼嘴,树叶树苗庄稼棵儿,一不小心它就要偷吃一口。尤其是嫰绿的榆树枝条,简直是它的最爱。
夏天的时候,为了驱赶围绕在它身边的蚊蝇,即使卧着尾巴也能不停甩动,前半身尾巴够不着的地方,就用牛头去驱赶,这时就会响起一阵急促的牛铃铛声。有一种牛虻十分讨厌,它有时也会叮人,由于个头大,比蚊子叮人厉害多了,被叮了很疼很疼。
大中午的时候,吃饱草料的牛卧在地上倒沫,东卧一个,西卧一个,晶莹的白沫从牛嘴里耷拉下来,能拉丝,牛铃铛各不相同,铃铛声也不同。每头牛的品相脾气各不相同,卧姿也各不相同。太阳暖暖地照着,风儿轻轻地吹着,铃铛清脆地响着,这个时候的牛把儿,一般是坐在离牛不远的地上打盹。整个牛屋院,一派祥和安宁。
生产队里有一头明星牛,名叫“卧底花”,是个大牤牛。它的名字源于牛肚子上有几朵白色的花朵,整体上是南阳大黄牛,肚子上点缀的白毛,使它看起来有点像东北大奶牛,但几朵白花只仅限于肚子上那一片区域,卧下来的时候看着更醒目。
“卧底花”膀大腰圆,力大无穷,青壮年时期爱抵架,它可以同时单挑两头大牤牛。吃的多干活也利索,从不偷懒。别的牛犁地都是两头牛搁犋,并排干活,“卧底花”可以单干。
生产队里的牛有很多,只有“卧底花”有自己的名字,有自己的专属农具。平时都是杨表爷在喂养它,它的牛屋在“L”型的头上,坐西朝东的三间牛屋。生产队解散的时候,“卧底花”分给了杨表爷一家。杨表爷曾用“卧底花”给我们家悄悄耕过地,对杨表爷来说是举手之劳,对我们家来说,可是解决了大问题。这头明星牛是小刘庄也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
杨表爷一家是小刘庄的外来户,很早的时候他家的长辈在舅家门里住了下来,我们那里的说法是“老姑娘回门”。“卧底花”的年代,正是杨表爷一家在小刘庄过得最富足的时候。杨表爷和表奶对我们兄弟们照顾颇多,感恩他们。随着农耕经济的没落,杨表爷一家也无可奈何地走上了下坡路,令人惋惜。
牛屋院里,除了牛是主角,牛把儿也是当仁不让的重要角色。
牛听不懂人语,但它可以听懂牛把儿的话。“哒哒”是让它向左转,“咧咧”是让它向右转,“喔…喔”是让它慢一点,“喔”拖长音,语气再重一点是让它停住。牛把儿手持牛鞭在牛屁股后面甩着,可以指挥着牛们完成各项农业生产。好的牛把儿和牛之间,就像好的司机和汽车之间,可以配合默契,达到人车合一的美好境界。
牛把儿住在牛屋院里,和自己养的牛朝夕相处。牛吃的是碎麦秸,泼上料水用拌草棍搅拌均匀,叫拌槽。拌槽时手要稳要快,否则牛就把表面上的牛料都吃了,剩下的麦秸它就不爱吃了。牛料一般是黑豌豆、黄豆、玉米、麸子,棉花籽榨过油打出来的花籽饼,也是好牛料,牛很爱吃。大的牛槽可以同时容纳两头牛并排吃草。
牛把儿一般也是农活好把式,老家叫“庄稼筋儿”,牛把儿和牛干大项农活,其他人都是打下手。牛屋院里,除了西侧杨表爷的牛屋,北侧一排牛屋住着的牛把儿,自西向东第一个是“三哥”,三哥是光棍汉,虽然是同辈,但他的岁数比我的父亲都大。
再往东,是“印伯儿”,生产队解散分成小组的时候,我们家和印伯儿家是一个组,牛和大项农具都是共用的,有活儿大家一块儿干。“印伯儿”也是个光棍汉,一辈子未娶。
再往东的几个牛把儿,分别是元合“六爷”、元功“三爷”、“仓哥”、永祥“老六爷”。应该还有几个牛把儿,具体是谁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仓哥”、永祥“老六爷”都是光棍汉,永祥“老六爷”走路时腿一瘸一拐的,腿不好使却没耽搁干了一辈子农活。小刘庄的光棍何其多,一个字,穷啊!
元功“三爷”的后事更是令人唏嘘。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老家农村偷牛偷羊成风,团伙作案,疯狂程度简直就是明抢,元功“三爷”的两只大奶子羊不幸被贼偷走,一气之下,性格刚烈的他,竟然服农药自尽,这事我也是后来听别人说的。
时至今日,当年牛屋院的那些牛把儿们,无一例外全部都去天国报到了。生在小刘庄,又是那个年代,吃一辈子苦那是必然的。他们养过的牛,也已在生命的轮回里走过好几遭了。随牛把儿和牛们而去的,还有一个时代。
我小时候学会说话可真是不容易。
牛屋院的末子堆又高又大,是小孩子爬山冲锋、打滑梯的理想场地。西侧由于牛把儿经常从这里挖取土末子垫牛铺,被挖成了一个“悬崖”,笔陡笔陡的,差不多有一丈高。
有一天我和小伙伴们从末子堆上往下蹦,是张着嘴往下蹦的,结果蹦下来,牙齿重重地咬在了舌头上。用当时的话说,就剩“一系溜儿”了,舌头被咬掉,我就成哑巴了。吃一堑长一智,原来从高处往下蹦的时候,一定要闭着嘴,可不能张着嘴。张着嘴容易咬着舌头。
一个阴雨绵绵的上午,幼小的我去牛屋院玩,来到了三哥的牛屋。三哥是个结巴壳儿,说话结结巴巴的。他非常热心地教我学习结巴壳,老师用心教,学生用心学,在师徒二人的共同努力下,没用多长时间我就熟练掌握了说话结巴的方法和技巧。三哥很满意,没想到我学得这么快。临走的时候,他笑的很灿烂,也很阴险。
中午回到家,母亲一听到我的结巴壳,怒不可遏,一巴掌拍过来,就把我一上午辛勤学来的结巴技术打到了九霄云外。母亲教育我们向来简单粗暴,效果也是最好。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去三哥的牛屋玩了。母亲打我们,可不是吓唬吓唬,那是真打啊。小刘庄东墁,尚字辈的结巴壳有好几个,差一点就多了我一个。
现在的豫南农村,已经看不到耕牛遍地的场景了。
过去,二十多天才能熬过去的麦天,现在用收割机两三天就结束了,牛和牛把儿都已失去了用武之地。传承了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小农经济再也难以为继了。听说今年的豫南农村,先旱后涝,秋庄稼还没来得及收就烂在地里长了芽,损失惨重,令人惋惜。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鲜明特色。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一粒尘埃,渺小得微不足道。除了顺应时代,我们别无选择。
小刘庄过去很穷,是周围所有村庄最后一个通电的。刚通电的时候因为电压低,灯泡影影绰绰的就像萤火虫,连电视机都打不开。
直到九十年代末,由于在村子边上新建了一个变电站,电压才稳定下来,小刘庄才开始正式进入电器时代。而在九十年代之前的漫长岁月里,都是靠点油灯熬过来的。可想而知,小刘庄的先人们,吃了多少的苦,遭了多少的罪。
有时我也会想:如果时代没有改变,我没走出小刘庄,我会做些什么呢?答案是我很可能也会成为小刘庄的一个牛把儿,就像我未曾见过面的光棍汉二爷一样,喂一辈子牛,种一辈子地,手持牛鞭把田耕,在“哒哒咧咧”的吆喝声中度过这一生。什么航天,什么雷达,什么导弹,此生都会离我很远很远。
岁月模糊了记忆,改变了容颜。但故乡一直屹立在我的心中,从未走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