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徽宗赵佶的《文会图》中,一幅宋代文人宴饮的热闹图景徐徐展开:案几之上,酒器错落排布,一侧有童子屏息守候在红泥火炉旁,炉上矮胖的注壶正接受明火烘烤;另一侧,一套温润的白瓷器具格外引人注目 —— 瘦高的注壶稳稳嵌在敞口温碗中,碗内热水氤氲,正以柔和的温度滋养着壶中的佳酿。
宋徽宗赵佶《文会图》中的火炉热酒和温碗温酒
这幅传世名画,不仅定格了宋代两种主流温酒方式,更让我们得以窥见 “注壶温碗” 这套酒具所承载的精致生活美学。
而 1992 年河北定州宋墓出土、现藏于定州市文管所的宋代定窑白釉注壶温碗,便是这幅画中 “雅致温酒” 场景最生动的实物注脚。
这套定窑酒具由注壶与温碗配套而成,胎质细腻洁白,釉色莹润如象牙,尽显宋代定窑 “白如玉、薄如纸” 的工艺精髓。
温碗高 14 厘米、口径 17.5 厘米,口沿作六曲花口,呈典型的 “芒口” 样式,深腹搭配高圈足,胎厚仅 0.2-0.3 厘米,轻薄却不失端庄。
外壁以精湛的剔花工艺刻绘缠枝牡丹纹,花瓣舒展、枝蔓缠绕,近足处还饰有一周层次分明的莲瓣纹,线条流畅如行云流水;
与之配套的注壶虽口部残缺,残高仍达 21.5 厘米,整体呈灵动的葫芦形,龙首状的壶流张口欲吐,对侧的环形柄由三股泥条并列粘结而成,柄与壶腹上侧间还巧妙设一圆柱支撑,既加固了结构,又增添了造型的层次感。
壶身纹饰与温碗呼应,颈部上下各饰一周菊瓣纹,下腹满刻肥硕饱满的缠枝牡丹,近足处的重叠仰莲纹与温碗纹饰形成完美闭环,整套器具宛如一件浑然天成的艺术杰作。
为何宋代文人会偏爱这样一套酒具?这便要从它 “隔水温热” 的核心功能说起。相较于火炉直接加热注壶的便捷,温碗隔水加热的方式更显细腻 —— 先将热水注入温碗,再将盛酒的注壶放入碗中,热水的温度会缓慢渗透至壶内,让酒液在约 100℃的温和环境中逐渐升温,既避免了明火直接加热导致的酒液焦糊,又能长久保持酒香醇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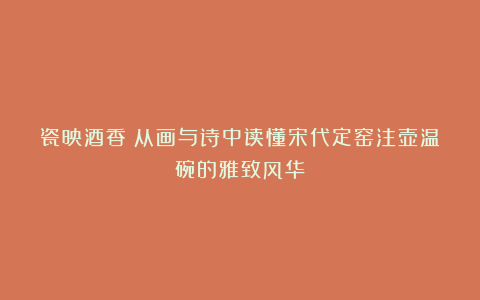
这种温酒方式,恰与宋代文人追求 “雅致生活” 的理念不谋而合,无论是《文会图》中众贤齐聚的宴饮盛会,还是独处时的浅酌慢品,注壶温碗都能胜任。
正如宋末元初画家钱选在《题雪霁望弁山图》中所写:“独坐火炉煨酒吃,细听扑簌打窗声。” 诗句虽描绘的是火炉煨酒的场景,却道出了宋代文人对 “煨酒” 的偏爱。
当窗外雪花簌簌飘落,文人将定州这套定窑注壶温碗置于案头,往温碗中添入滚烫的热水,看着白瓷碗壁渐渐蒙上一层薄雾,壶中酒液在温水滋养下缓缓升温,酒香随着水汽悄然弥漫。
此时无需宴饮的热闹,仅一人、一壶、一碗,便能在酒香与雪声的交织中,品味独处的悠然。这套注壶温碗轻薄的胎体、瘦高的壶型,正是为适配温碗的弧形内壁而生,它不像火炉加热的注壶那般厚重矮胖,却以精巧的设计,将 “温酒” 从单纯的实用行为,升华为一种充满诗意的生活仪式。
从《文会图》中觥筹交错的宴饮盛景,到钱选诗中静谧闲适的独坐煨酒;从红泥火炉的市井烟火气,到注壶温碗的文人雅致风,定州文管所藏的这套定窑白釉注壶温碗,早已超越了 “酒具” 的实用属性。
它是宋代制瓷工匠智慧的结晶 —— 细腻的胎土、莹润的釉色、精湛的剔花工艺,代表着定窑白瓷的巅峰水准;更是宋代文化的鲜活载体,见证着古人对生活美学的极致追求。
如今,当我们凝视这套跨越千年的白瓷酒具,仿佛仍能看见宋代文人围坐案前,以热水温润佳酿的场景,听见酒香中流淌的诗意与风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