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祐元年九月初一,1086年10月11日。
一场矛盾的哀悼在开封府(今河南省开封市)上演.
百姓罢市哭送、高太后携哲宗亲祭,赠谥“文正”的司马光.
却在死后数年被削爵毁碑。
甚至沦为“元祐党人”之首。
他是编著《资治通鉴》的史学巨匠。
却因全盘废除王安石新法、归还宋军攻占的西夏土地,陷入“守旧误国”的争议。
从“火线复出”主持元祐更化,到积劳病逝仅八个月.
这位四朝老臣的一生。
既是北宋党争的缩影。
也是历史人物功过难断的典型。
其跌宕命运与复杂争议。
至今仍引人探究历史深处的权衡与遗憾。
元祐元年秋的巨星陨落——北宋名相的最后落幕
北宋元祐元年九月初一,1086年10月11日。
开封府(今河南省开封市)的秋风卷着落叶,穿过喧嚣的街巷。
最终停在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的府邸前。
这一天,这位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的老臣。
在主持朝政仅八个月后,因积劳成疾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八岁。
史载司马光晚年“心悸气素,步履需人扶”,即便如此,他仍以“工谋于国则拙于身”的执念,坚守在朝堂一线。
司马光彩像(清殿藏本),取自《历代圣贤名人像》,台北故宫藏
此前数月,他还带病上疏,直言“免役法、青苗法不除,吾死不瞑目”。
这份对国事的赤诚,早已刻进他的骨血。
噩耗传入宫中,垂帘听政的高太后闻讯,当场落泪,随即携年幼的宋哲宗亲赴司马府祭奠。
朝廷特赐一品礼服为其入殓,赏银、绢七千两(匹)以助丧仪。
追赠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赐谥号“文正”。
要知道,“文正”之谥在北宋乃文臣最高荣誉,自开国至元祐年间,获此殊荣者寥寥无几,足见其生前地位与贡献。
哲宗更亲笔为其墓碑题字“忠清粹德”。
又命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全程护送灵柩。
归葬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运城市夏县水头镇)司马光祖茔。
消息传到民间,开封百姓自发罢市,涌到街头凭吊。
有人捧着刚买的布匹,有人提着尚未归家的食盒。
密密麻麻的人群堵满了通往司马府的道路。
街巷间的哭泣声盖过了车水马龙的喧嚣。
更有甚者,为凑钱参加祭奠,不惜变卖衣物。
待灵柩启程前往夏县时,送葬队伍绵延数里。
百姓跟在后面,如丧至亲般悲恸。
有人边走边哭道:“司马相公走了,往后谁还替咱百姓说话啊!”
即便远在岭南封州(今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的父老,听闻消息后也纷纷设坛祭拜。
京城及全国各地的百姓,争相绘制司马光画像,供奉于家中正堂,每日饮食前必先祭祀,以表敬重。
司马光的离世,为何能牵动举国民心?
回溯此前一年,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病逝,十岁的哲宗继位。
北宋因变法引发的党争已持续十余年,民生凋敝,朝堂动荡。
正是高太后力排众议,召退居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十五年的司马光“火线复出”,让他以门下侍郎之职收拾残局。
谁曾想,这位以《资治通鉴》名传天下的史学家,刚在相位上为“元祐更化”铺垫好根基,便匆匆离世。
他的逝去,不仅是北宋朝堂的重大损失。
更像一根支撑民心的梁柱轰然倒塌。
难怪时人叹曰:“温公一去,天下无完人矣。”
而这份身后哀荣,也为司马光跌宕起伏的一生,画上了一道悲壮却厚重的句号。
从涑水神童到政坛砥柱——司马光的半生耕耘
司马光的故事,要从北宋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1019年11月17日)讲起。
这一天,他出生在光州光山(今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县衙官舍。
父亲司马池时任光山县令,便以“光”为名。
这名字也成了他一生与这片土地的羁绊。
六岁时,司马池开始教他读书。
七岁那年,他已能完整背诵《左氏春秋》。
还能给家人逐句讲解书中要义。
《宋史·司马光传》载其“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
这般早慧,在当时实属罕见。
更让人惊叹的是,他还在童年留下“破瓮救友”的典故。
“司马光砸缸”雕塑
小伙伴不慎坠入大水瓮,其他孩童吓得哭喊着跑去找大人。
唯有司马光急中生智,捡起地上石块砸破瓮身。
水流尽后,同伴得以脱险。
这就是著名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
此事很快传遍京洛,时人还绘成《小儿击瓮图》广为流传,成为后世蒙童启蒙的经典案例。
2004年国家邮政局发行的《司马光砸缸》特种邮票
十五岁前,司马光的生活轨迹跟着父亲的仕途变动而延伸。
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等地为官,始终把他带在身边。
用《邵氏闻见前录》的说法,是“每出游或与同僚论议,必携以行”。
这段“走南闯北”的经历,让他见识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
访古探奇时还常赋诗题壁。
既丰富了社会阅历。
也埋下了对民生疾苦的体察之心。
他读书的劲头更是“离谱”。
《宋史》称其“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即便在赶路的马车上,也会捧着书卷研读。
这般嗜学,为他后来的学术与政治生涯打下了坚实根基。
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二十岁的司马光赴京参加会试。
一举高中进士甲科,顺利踏入仕途。
最初被授为华州(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判官。
当时司马池任同州(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知州。
两地距离不远,他常抽空探望父母。
也在同州结识了同科进士石昌言,两人成了忘年之交。
不过,他的官场生涯并非一路顺遂,很快便遭遇“丁忧”考验。
康定元年(1040年),他为侍奉在苏州(今江苏省苏州市)的父亲,求得改任签书苏州判官事。
可没过多久,母亲离世,他按制离职回乡服丧。
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父亲司马池又在晋州(今山西省临汾市)病逝。
一年之内“二亲继丧”,《司马文正公集》中记载他当时“叹息平生念此心先乱”。
却仍在居丧期间发奋著述,写下《十哲论》《四豪论》等文。
这些文章后来多成为《资治通鉴》中“臣光曰”的雏形。
服丧期满后,司马光在父亲好友庞籍的举荐下,先游幕延州(今陕西省延安市),后任武成军判官。
庆历五年(1045年)春,黄河泛滥,武成军治所滑州(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受灾严重。
他亲自督役河上,冒雨指挥抢险。
这份亲力亲为的作风,在他后来的为官生涯中始终未变。
皇祐三年(1051年),他任同知太常礼院时。
还因敢说真话留下美名。
宦官麦允言死后,朝廷拟用卤簿仪仗
他坚决反对,上疏称“近习之臣用此礼,不合名分”。
大臣夏竦获谥“文正”。
他又直言“此谥至美,非竦所当得”。
即便得罪权贵也不妥协。
到了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的人生迎来重要转折。
他将耗时数年编撰的《通志》八卷呈献宋英宗,这部书记述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前207年)的历史,详析历代治乱兴衰。
英宗阅后大为赞赏,当即命他在崇文院设局续修《历代君臣事迹》。
还允许他自主挑选协修人员。
谁也没想到,这个决定后来催生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资治通鉴》。
而司马光的人生,也自此与这部史书紧紧绑在一起,开启了“宦海沉浮与修史并行”的新阶段。
元祐更化的燃眉之任——老臣最后的鞠躬尽瘁
北宋元丰八年三月七日(1085年4月1日),宋神宗赵顼病逝。
十岁的太子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
朝堂瞬间陷入动荡,变法派与保守派的角力愈发激烈。
垂帘听政的高太后深知,唯有请回那位“退居洛阳十五年,天下皆期之为相”的司马光,才能稳住局面。
这一年,司马光已六十六岁,《司马文正公集》中记载他当时“体羸多病,目昏齿落”。
却在接到诏令后,毫不犹豫地结束了“宅在家”修史的生活。
明仇英《独乐园图》(局部)中的司马光(着白衣者)
从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赶赴开封府(今河南省开封市),开启了人生最后一段“火线复出”的征程。
初回朝堂,司马光便以门下侍郎(副宰相)之职上疏《乞开言路札子》,恳请高太后“广开言路,许群臣直言新法利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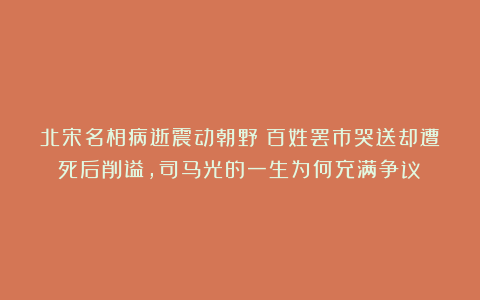
这份奏疏很快得到批准,朝堂上下压抑已久的声音终于得以释放。
紧接着,他又上《乞去新法病民伤国者疏》,直指青苗法、免役法等新政的弊端,称其“名为爱民,实则病民;名为益国,实则伤国”,字里行间满是对民生疾苦的关切。
当时,新法已推行十余年。
各地官吏为求政绩,强行摊派青苗钱、加重役税,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的惨状屡见不鲜。
司马光的奏疏如同一剂对症的药方,让高太后更加坚定了“更化”的决心。
可改革之路远比想象中艰难。
变法派残余势力仍在朝中盘踞,他们指责司马光“以母改子,违背先帝遗志”。
甚至暗中阻挠新政废除。
司马光却毫不退让,他一面联合吕公著、范纯仁等老臣。
召回因反对变法被贬的苏轼、苏辙、刘挚等人,构建起稳定的执政核心。
一面亲自主持新法的废除工作,先罢保甲法,解除百姓“昼夜训练,不得务农”的负担。
再废方田均税法、市易法,让民间商业与土地买卖回归常态。
那时的司马光,身体已近极限。
《宋史》载其“心悸气素,行步需人扶掖”,甚至在上朝时多次因体力不支险些跌倒。
高太后心疼他,特准其“乘肩舆入省,三日一上朝”。
可他仍坚持亲理政务,常常在书房批阅奏章到深夜,桌上的烛火映着他佝偻的身影,成了宫廷中一道令人动容的风景。
最让人揪心的,是他对免役法的态度。
免役法虽缓解了官府劳役短缺的问题。
却让百姓缴纳的“免役钱”日益繁重。
司马光深知此弊不除,民生难安,可废除过程中遭遇的阻力也最大。
一次朝堂议事,变法派大臣章惇当庭与他争辩,言辞激烈。
司马光却始终平静应对,一条条列举免役法的弊端,直到章惇“理屈词穷,默然退下”。
事后,他对身边人说:“吾非必欲尽废新法,但求为民去害耳。”
元丰八年(1085年)年底,司马光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相。
可他的身体也彻底垮了。
元祐元年四月(1086年5月),王安石病逝的消息传来。
重病中的司马光仍特意致信吕公著。
叮嘱道:“介甫(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朝廷当优加厚礼,以慰其家。”
这份不计前嫌的胸襟,让时人无不敬佩。
到了元祐元年七月(1086年8月),《资治通鉴》的最后校定工作完成。
司马光捧着这部耗尽十九年心血的著作,眼中满是欣慰。
可他也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他开始抓紧处理未竟的政务,甚至在病榻上口述奏疏,让养子司马康记录。
内容全是关于如何安抚百姓、稳定边疆的建议。
有人劝他保重身体,他却摇头道:“吾受两宫厚恩,若不能为天下尽最后一份力,死不瞑目。”
这份“工谋于国则拙于身”的执念,最终伴随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元祐元年九月初一(1086年10月11日),当免役法、青苗法等新法终于尽数废除。
北宋的民生与朝堂逐渐回归正轨时,司马光却没能看到这一切的成果,在开封府的府邸中溘然长逝。
他的离去,如同为“元祐更化”按下了暂停键。
也让北宋失去了一位能平衡各方势力、稳定大局的名相。。
而这场他倾注最后心血的改革,最终也在他死后逐渐偏离方向,为日后的“绍圣绍述”埋下了隐患。
千年史魂与宦海沉浮——司马光的身后荣辱与精神传承
元祐元年九月初一(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病逝后,北宋朝堂为他举办了隆重葬礼。
可谁也没想到,这位“权倾天下而朝不忌”的名相,身后名竟会经历如此剧烈的起伏。
其执政生涯中的争议之举,更成为后世评价他的重要分歧点。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拜相。
这位变法派核心人物一上台,便将矛头对准元祐旧臣,直言“先帝法度,为司马光、苏辙坏尽”。
同年七月,宋哲宗下诏削除司马光的太师封号与“文正”谥号。
派人毁掉哲宗亲题的“忠清粹德”碑。
绍圣四年(1097年),司马光再遭贬谪,被追贬为清海军节度副使。
甚至加贬朱崖军司户参军,其子孙也被限制入朝为官。
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时期,蔡京将司马光列为“元祐党人”之首,刻元祐党人碑于全国各州郡。
司马光(标红部分)在元祐党籍碑中名列首位
明令“禁元祐学术”,连收藏司马光著作的人都可能获罪。
一时间,这位曾受万民敬仰的老臣,成了朝堂上人人避之不及的“罪人”。
这般冰火两重天的待遇,背后除了党争恩怨,更源于司马光执政期间的争议决策。
在不少时人与后世看来,他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对。
存在“为了反对而反对”之嫌。
未能客观审视新法中合理部分。
反而以“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执念全盘否定,导致北宋经变法积累的国力与改革成果付诸东流。
宋廷面临的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尤其在边事上,王安石主政期间,宋军曾攻占西夏不少土地。
这些土地既是西北边防的重要屏障。
也是对西夏军事威慑的战略支点。
可司马光上台后,却以“恐西夏不安,致边患再起”为由,主张将元丰四、五两年(1081-1082年)间宋军攻占的军寨尽数归还西夏。
此举在当时便遭安焘、孙路等大臣竭力反对,认为“弃地与夏,是弃祖宗将士血战之功,损国家边防之固”。
即便在后世,也有学者批评这一决策短视,甚至直言以现代视角审视,这般主动放弃已收复的领土,近乎“卖国”之举。
司马光虽在与王安石的党争中“斗赢”,最终推动废除新法、归还西夏土地。
却也因此让自己的名声蒙上阴影,成为后世争议的焦点。
有人赞他“为民去害”。
也有人斥他“守旧误国”。
正如《宋史》编纂者在评述中所留的余地:“熙宁新法病民,海内骚动,光退居洛阳,天下引领望其为相;及其起而为政,毅然更张,然其弃地西夏之议,亦为后世所讥。”
直至靖康元年二月(1126年3月),宋钦宗即位后,面对金兵南下的危局。
才想起司马光当年“谨边防、安百姓”的主张。
下诏为其平反,恢复太师之职,重新赐谥“文正”。
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司马光得以配享哲宗庙廷,与北宋诸贤并列。
绍兴十八年(1148年),其画像被供奉于景灵宫,供后世帝王瞻仰。
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理宗图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司马光位列其中。
这份荣誉,是对他一生功绩的最终认可。
却未能完全消解关于他“弃地”“废法”的争议。
咸淳三年(1267年),朝廷追赠司马光从祀孔庙,称“先儒司马子”。
明嘉靖年间,从祀规格进一步提升。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司马光与历代四十位功臣一同从祀历代帝王庙。
至此,他的历史地位彻底稳固,成为跨越千年的“文臣标杆”。
但那些争议仍如影随形,成为解读他一生绕不开的话题。
如今,在司马光的故乡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运城市夏县水头镇),司马光墓(司马温公祠)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夏县司马光墓(司马温公祠)
仍保存着大量宋至清时期的碑刻。
其中宋哲宗的题碑、苏轼撰写的祭文石刻,皆是金石学中的珍品。
河南光州光山(今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留存着他的衣冠冢、司马府与涑水书院。
当地还成立了司马光教育基金会,以他的名字命名广场与道路,每年举办纪念活动。
浙江绍兴(今浙江省绍兴市)的司马温公祠。
虽经后世重修,却依旧承载着百姓对他的纪念之情。
而司马光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远不止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遗迹。
他耗时十九年编撰的《资治通鉴》,被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誉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
这部294卷的编年体通史,不仅保存了322种早已失传的史料,更开创了“通鉴学”。
影响了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到清代《续资治通鉴》的历代史学编纂。
他的个人品行,更成了后世君子的典范。
“诚信卖马”时,他坚持告知买主马匹“夏季有肺病”,不赚昧心钱。
“坚不纳妾”,与妻子张氏相濡以沫数十年,即便张氏未育,也从未想过纳妾。
身居高位时,他“食不常有肉,衣不穿纯帛”。
甚至卖掉洛阳三顷田安葬妻子。
这份“俭以养德”的坚守,在封建士大夫中极为罕见。
山西运城的司马光雕像
回望司马光的一生,他既是“工谋于国则拙于身”的贤臣。
也是“述往事、思来者”的史家。
却也因党争中的极端立场与边事上的保守决策,让自己的历史形象充满矛盾。
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并非全然守旧。
却也未能跳出“非此即彼”的党争思维。
他晚年“火线复出”主持元祐更化,初衷是“收拾残局”。
却因全盘废法、弃地西夏,反而加剧了北宋的统治危机。
正如近代学者蒙文通所言:“温公元祐时罢免或修改熙丰新法,未见其复行形势税簿,王居正亦未言元祐时废止主殴佃客至死减等之法,是荆公、温公虽有不同,而其本质则一也。且温公虽主节费,而元祐更化时于冗官、冗兵、冗费等弊政,仍无所触动。”
千年过去,北宋的党争早已落幕,变法的利弊也成了历史谈资。
但司马光的人生轨迹与争议决策,却始终提醒着后世。
历史人物的功过往往复杂多面。
评价时既需看到其品德与贡献。
也不能忽视其时代局限与决策失误。
而他“为了反对而反对”导致宋之问题未决、弃地西夏损及国权的争议,更成为后世审视党争危害、权衡改革与保守的重要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