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议之争”是北宋英宗时期一场关于皇室礼法的大论战。英宗以旁支入继大统,即位后欲尊崇生父濮王赵允让。以司马光、王珪为首的朝臣坚持“为人后者为之子”,主张英宗应称仁宗为皇考,生父为皇伯。欧阳修等官员则援引礼制,支持尊濮王为皇考。
双方相持不下,争论自治平二年(1065年)持续至三年,最终曹太后迫于压力,手诏同意英宗尊濮王为“皇考”。
英宗表面上获胜,实则激化了朝堂矛盾,消耗了统治精力,成为北宋中期政坛分裂的缩影。
以上文字,是我在网上搜索到的关于“濮议之争”的极简解读,不过一二百字而已。
但在罗胖子的《文明之旅1065》里,却是嘚啵嘚啵了一个小时、数万字之巨,其间自然是波澜起伏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再加上他明显夸张的表情、舞舞扎扎的动作,明明是一件两败俱伤的不好事儿,却依旧能把我看得忍俊不禁,到最后竟然“噗嗤”一笑:这不就是一场古代版的“我该管谁叫爹”的大型辩论赛吗?
只不过,这场辩论赛的赌注实在是太高了,关乎皇位、权力,还有满朝文武的仕途命运。
您想象一下这个场景:英宗皇帝赵曙坐在龙椅上,看着朝臣们争辩的面红耳赤唾沫横飞,一脸委屈地发问:诸位爱卿,你们争出结果了吗?我到底能不能管我亲爹叫一声爹?
就这么简单一个问题,竟然让北宋朝廷炸开了锅,分成两派吵了整整20个月!
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看似简单,实则牵扯极深。
英宗被过继给仁宗当儿子,继承了皇位,那么他该称生父濮王为“皇考”呢,还是“皇伯父”呢?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这问题简直就是无聊透顶:亲爹就是亲爹,这有什么好争论的?
前些年,村里有好多胎娃出生没几天,就因为各种原因,或是被抱养、或是被过继了,成了别人家的孩子,但多数跟亲生父母还是有联系的,回家之后依然是唤爸妈的。
但在古代礼法社会,这却是天大的原则问题。即便你亲爹真是你亲爹,也不是你想叫就能叫的。
以司马光为首的台谏官们坚持认为:新官家既然已经过继给了老官家,就只能有一个爹,至于亲爹濮王,只能叫“伯父”了。
而韩琦、欧阳修等几位相爷则觉得,皇帝也是人,也有骨肉亲情,管亲爹叫爹天经地义。这回,咱们几个老家伙,必须支持咱们这个小官家。
要理解这场争论,我们得先了解英宗皇帝的处境:他简直就是皇权制度下的“工具人”典范:三岁时被选进宫,不是为了当皇子,而是作为“招弟”的工具,希望他的存在能给仁宗招来亲生儿子。
果不其然,仁宗的亲生儿子一出生,赵招弟小朋友就被送回了濮王府;仁宗的儿子夭折,他又被接回了宫里。
如此反复了N次,他在宫中就像个临时演员,随时准备被替换。
更惨的是,当皇子的日子里,他吃不饱饭,没人敢和他说话,连家人送来的安慰信都不敢收。
这种环境下,他能对仁宗和曹太后产生多少真情实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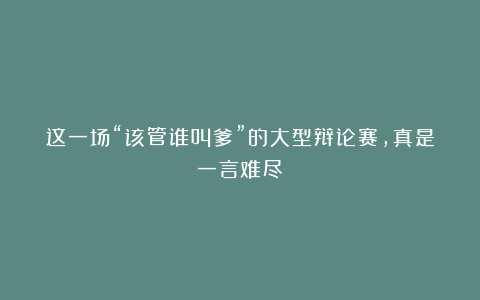
“濮议”之争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揭示了道德判断的复杂性。
司马光等人站在礼法角度,指责英宗“不孝”;而我们站在英宗的角度,却能理解他的委屈和恐惧。
双方都有自己的道理,也都有情感上的依归。
这让我想到现实生活中,我们总喜欢对别人的行为做简单的道德评判:某某不孝、某某忘恩负义。
现实往往比表面复杂得多,每个人匪夷所思的行为背后,都有其与众不同的情感逻辑和处境考量。
就像掌权后的英宗限制曹太后的吃穿用度,表面上看是大不孝,实际上可能源于对“假怀孕宫女”事件的恐惧。
他在担心:有朝一日,“母后”会用“父皇”那个“遗腹子”取代我吧?还是有个亲爹好啊,心里踏实。
最是无情帝王家,在残酷的皇权斗争中,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濮议”事件中,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同样是士大夫,为何宰相韩琦、欧阳修支持皇帝,而台谏官司马光等人却坚决反对?
说白了,就是“位置决定立场”。宰相作为行政首长,需要考虑与皇帝的合作关系;而台谏官的工作就是提意见,认死理、头铁是他们的职业要求。
回望这场千年前的争论,我看到的不仅是礼法与情感的冲突,更是人性的复杂与矛盾。
英宗坚持认亲爹,未必是因为对生父有多深的感情,更像是对那个强加给他的“养子”身份的最后反抗。就像一个被领养的孩子,长大后非要寻找亲生父母,不一定是因为养父母待他不好,而是想找回自己的根。
这场争论,最终以英宗皇帝的胜利告终,但代价惨重:所有反对他的台谏官,全都被赶出了京城。
表面上是英宗皇帝赢了,实际上他的声望遭受重创,还在史书上留下了不太光彩的一笔。如果这是笔买卖,实在太不划算。
罗胖子感慨:无论在什么时代,试图用权力解决情感和认同问题,往往适得其反。
“濮议”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千年之前,但它给我们的启示却历久弥新:在评判他人时,多一份理解,少一份武断;在处理复杂关系时,多一份灵活,少一份固执。
生活,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选择,而是充满灰色地带的复杂拼图。
叹息归叹息,我们还是以轻松的心情看待这段历史:
连皇帝都有“我该管谁叫爹”的烦恼,我们生活中的那点小纠结,又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