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在戊戌冬
余居白嶽一周年
终日云烟中 有庄生佐酒
赤子奉茶 写梅花一枝
録擔公诗
结伴去寻梅 梅花放不放
雪里有人家 酒帘高一丈
又一
雪中有路失南北 欲问青山不可得
不是梅花一点开 大块几乎暗无色
连山 学人
原文:
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如天之造生,地之造成,此其所以受也。然贵乎人能尊,得其受而不尊,自弃也;得其画而不化,自缚也。
“画受墨,墨受笔”,注意这个受,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个受不是画跟墨、墨跟笔的问题了,画,要画画,通过墨来受,墨是啥?墨是个实际物质,墨怎么能受呢?是有一个掌控墨的有天受的人受了画。懂了吧?墨绝对不是墨自己会画画,你想,我们借这个杰作看看,你看这上面是不是有墨?这个墨是它自己上去的吗?这后面有个大师,它一定是笔画上去的,笔后面一定有个手,手后面一定有个心,有心的人,才叫有一画的人。
如果没有这,这就不可能构成。反之,从这张画就能看出这个人的心,这个画如果是散乱的,这个人的心就是散乱的。这个人如果是媚俗的,这个人的心就是媚俗的。这个画如果是清洁的,这个人的心也是清洁的。所以古人看画先看气韵,气韵生动第一。这气韵是啥子?气就是那个天受的部分,所以人之生也气之聚也,万物皆气之流变,所以一切物象,它的格调是它的气息决定的。
气息正的人,我们感受到清旷。气息不正,你看所有妖魔鬼怪的东西,它都气息不正,它即便长得丑,他气息正,你都会觉得他有温柔敦厚感,他有堂正感。反之长的特别漂亮,只要气不正,你就觉得他妖孽,你会感觉到这个人身上有妖孽感。你如果是一个生命通透的人,你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你会即便不搭一句话,一眼看你下意识就会有感受了,虽然你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这个人给你一种不祥的感受,看着他就觉得不祥。后来一聊,发现他果然是个恶人。
所以注意,这个受字不再是横向的我给你,你给我,受这个字是纵向的关系,看起来是横向的画和墨的关系,墨和笔的关系,所以石涛他前面先要界定什么是“受”,然后才用这个词。他上来就说受,就会变成我受给你,你受给我,好像你们的水平是我受的似的,不是这样的。你们以后真的名满天下成大师了,你也不要说是我教的,我哪教的上呢?当然,我要死了,你到我坟上去烧一把纸,我也不知道,那是你的事情。这是两不相关的。
我还记得很多年前,牛群在蒙城搞的那个聋哑学校,约我去给他们带几个学生。我在负责聋哑学校之前,我是先有半年给他们带了一个班,算是帮忙,义务带了一个聋哑人班。在《目击道存》那个书里面,我稍微有提及,从八个年级二百多个学生,我选了二十个学生,然后组成了一个特别的美术班,名字叫大音堂,我起的,因为他们听不到,耳朵听不到,但是我不认为他听不到,他只是听不到噪音,能听到真音,就是大音希声的意思。
然后怎么教?牛群很关心这个问题,他说你不会手语怎么教呢?我说没关系,他很热心,从北京聋校还请了两个聋哑老师专门教我手语,我一开始也认为要学手语,到那两个聋哑老师来了要教我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不需要学手语,后来呢,就教了其他人。
我在拒绝学手语的时候,跟牛群有一个对话,牛群说你不学手语,怎么教他们呢?我那个时候读庄子,读了有半年了,所以实际上从我人生真正读庄子开始,一直到现在,我所有的作为都与庄子有关,都是后识庄子,然后启发了那个天受的东西,包括怎么做书院、怎么教聋哑人、怎么弄这个卮画,都是这样。
蜀人张大千
近世名手 长于摹写
余见其蔬果册 颇有性情习之
戊戌 连山于白嶽
我是因识了庄子,然后越来越有对人具足的那个东西的感受。然后第一个实验田就是聋哑人,我一下子敏锐地觉得这个是上天给我一个印证我学庄子一个感通的机会,因为庄子书中大量的有不言之教,不言之言,不言之人,言无言,正好碰见了一大堆不会说话的,这真是好,你没有想啥就来啥,不是你想啥来啥,我一开始从来没想到我要去教聋哑人呀,而是你没想啥它来啥。
来啥的时候,如果你是真的能接的住,你瞬间知道这是上天赐予你的机会。你如果只是说,哎呦,这是聋哑人,要教画画,然后再去问问人家聋哑老师是怎么教的。我干任何事情,都不问别人经验。但之前我不是这样的,我讲的是我更生之后。之前的我跟一般人一样,都是想干个什么事,一定要问问这个你怎么干的?
从那之后,我干任何事情,我都是一个人想一想这个事怎么干,我绝对不会跑去问别人经验。干完了以后,如果有人来采访,或者我要到哪儿去,可以跟人聊聊,但已经不是参考经验了,而是勘验了。就像四方来书院访学,对我们来说只是勘验。我们从来不需要去邯郸学步式去外在学别人经验。学画画也一样,那么之所以不学手语,是因为我突然发现这是一个天受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学手语呢?手语已经是后识了,你只要用天受的东西跟这些小孩交流不就可以了吗?所以我跟牛群说,根本不需要手语,如果会手语了,他看我的手,他眼睛的注意力在我手上了,如果不会手语,他注意在哪儿?他注意力在我整个的人身上,他们一定是两眼盯着我,根本不会离开的,因为不知道这个老师要干啥。然后呢,我要是带个翻译进来,那个翻译说这个老师不会手语,接下来他教你们画画,每个小朋友都开始懵。接下来开始想,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每个小朋友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像掉水里了等你来捞他,他就手伸给你,你一把就抓上了。
如果每个人都觉得,反正他也会手语,我只要看他手就行了,他手不动我就不看他,我手动的时候他才看我,我手不动他都不看我,所以,你要确保让每个小朋友随时都看着你,他就跟你交流了,那一切肢体语言都跟他发生交流,否则的话,他只盯着细节看,这叫小识,这个手是小识,我这个人才是大识。可重要?我当时其实就是这样想的,这不是我现在才这样解释啊,我当时很奇怪,我觉得我得要让他们关注我才可以。
关注我,他肯定不只是用眼关注,一个是他觉得这个人,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人他不会手语呀,那接下来咋教,他觉得这是个疑问,然后我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用最原始的方式,就是比划,他们也比划,我也比划,他们比划是有套路的,我比划是没有。他要全神贯注的看我比划,好,他懂了懂了懂了。他又不是个傻子,所以,我们都有这经验,你想想,你家养个狗、养个猫,你跟它熟了,你一个动作它就懂,你点个眼他就知道干啥。那些聋哑人之间跟我就变成这样的关系了。
所以直到现在,你们可以看到张磊跟我之间配合的默契,我只是现在照顾你们多了,他已经大了,那时候他小的时候,你知道,我要干啥他就像是人家手术室手术台里面训练极为有素的护士,医生一般在做手术的时候这样,递啥递啥他清楚的很,就是他的思维完全是跟着你做事的线路走的,到这个时候需要用刀,他直接就递你手里了,你只要一手伸就管了,你都不需要看他一眼他就递你手上了,张磊就有这本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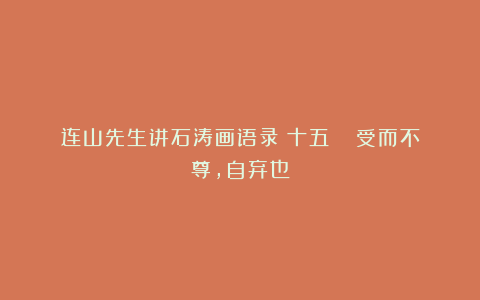
那些聋哑人就是这样厉害,他完全跟着老师的思维走,他是用心跟着你的,那还有什么需要麻烦的呢?所以我那一年教他们的时候特别不费事,上课基本我就坐在桌子上,要么自己看看书,要么看看他们,不会教的,从来没教过他们画一笔画,后来他们到我家去,我基本上我在我画室画画,我不准他们到我画室去,我画也不让他们看。他们画画,我一般早晨过去瞅一眼,看一眼,我就去画画了,我一天都不理他们,就看几秒钟,如果我一看,咦?这个画的笔法快要神经了,就找他聊聊,你的头脑可神经了?肯定又想这想那的了,他比如说想去打工,头脑就会混乱,想谈女朋友头脑也混乱,这个时候就跟他讲讲《弟子规》,我跟他们讲了两年《弟子规》,每天讲一条,《弟子规》让他们内心先有所收摄,他只要心神收摄了,他画就画得好了。
就这些东西,你调整的恰恰是他天受的部分,不是具体教哪一笔哪一笔怎么画。我现在反而跟你们要费那么大劲,之所以要费那么大劲,是因为你们擅长于用耳朵,当耳旁风,耳朵是用来扇风的,不能用心去感知我要跟你们交流什么,你想这不费劲吗?哎呀我每次跟你们上完我都快成哑巴了,这就叫报应。现在说的我都要成哑巴了。好了,我们继续。就是这个受字要注意,为什么特别强调,一定要注意,我们学画画,是为了要激活我们的天受,不是学墨法、画法、笔法。
余居徽州 始见枇杷模样
道旁多此果 随手采撷
戊戌 连山
“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画,画上面有墨,墨是由笔来写的,笔后面有个手,手后面有个人,人有心,这一路就到了,就走心了,所谓学画画是在这个地方的,然后发于这个。石涛这样讲,范宽也这样讲,范宽当年跟李成学画画,三年以后,范宽忽然慨然,很感慨,一下有触发,说“前人之法,未尝不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 (先生曰:与其师迹,不如师心,与其师心,不如师造化。)
画不就是迹嘛,痕迹,不如师人,这个痕迹是人,比如说他跟师父学画画,李成画一笔,他跟着画一笔,这就是师迹,他后来发现那有师迹不如师这个人,就看到李成这个人了嘛,看到师父这个人了。但只要是人,他还有杂质啊,只要有人形,你就看孔子他还有毛病啊,蘧伯玉也有毛病啊,那你怎么师的呢?你不好去勘验。有时候你以为是毛病,未必不是优点,你以为是优点,未必不是毛病,这个东西不好把着,他又推进,最起码看到人了嘛,这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一生看只是看画,只是看物,要么临摹画,要么出去写生看物,从来没有人。
学画画是学人,与其师人,不如师心。什么是心?这个时候就快到了天受的地方,但是范宽又推一步,与其师心,不如师造化,这不就是一化了吗?再推一步就到这儿了。所以你可以说石涛画语录是石涛的,也可以说历代都是这样,凡是大画家一定在这个地方相遇,不会有第二个画论,不会有两种不同的画论,只是它表述不一样而已。
所以“如天之造生”,这不就是师造化了吗?这是不二法门。你们要真实的学,一定也是这样,会越来越跟它相遇,它会呈现为你们在治学过程中越来越与日俱增的快乐感,你会觉得这个快乐不足为外人道,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兴奋期,这个兴奋期,会让你越来越有感通的能力,直到类似于火箭朝上,直到并轨才算能够正常运行了,原来那个刺激式的快乐感就会消失,然后常乐就会出现。所谓常乐,就是不会被外境干扰了,如“天之造生,地之造成”,这不就是生成了,对于地来说叫成,对天来说叫生。生者,“乐著大始”,礼能成物,所谓在地成物。乐象天,大始,生;礼象地,成,成物。这就是“地之造成”,这就叫受。
那么对于真正画画的人来说,只要一拿笔,他就像造物主一样,他就有开天辟地的能力了。你想,在方寸之间可以咫尺千里,人跟造物主是一样的。所以,真正画家的那种生命的饱满状态,来源于他跟宇宙同大的感受,他甚至于有宇宙的功能,有这个造化万物的功能,一支笔可以造化万物,这是画家之乐。这个画家的乐,并不来源于办了美展、卖了钱,而是他在这如混沌一样的纸上开天辟地。
要知道,梵高当年比较苦恼的就在这儿,就在这个临界点上,梵高跟他弟弟写信,说每天看到这个空白的画布,完全像看鸿蒙未开的天地,不知道怎么下这一笔。所以当你一笔起,鸿蒙就开。我在这个点上也是至少快乐了有两年,这两年我一笔也没画,就每天在那儿看白纸,就这一笔下来,裂天裂地的。但是这一笔怎么弄上去不把这一张纸给浪费了,又不好意思画,那个时候又穷,舍不得买纸,好不容易有个纸,坐那儿臆想。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快乐,尽管比如说我有时候回去,他们会帮我回忆原来我如何苦,我被他们回忆的我都觉得还怪苦呢,其实在你身临其境他们认为所谓苦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为什么呢?就像颜回为什么不觉得苦,因为他不关注这个,他的关注点不在饥饿上。当你的关注点在外在的时候,那你肯定就苦了,你即便比颜回富你都苦。所以原宪的关注点不在他的破房子上,他不认为他房子破,他也不认为下雨漏水他就会咋的,因为只要他无愧于屋漏,剩下的都无所谓。他的注意点不在周边环境舒适与否,他已经不再有任何想法追求身体所谓的舒适才让自己觉得乐,你只要还想追求,下意识有对身体的舒适的追求,这个乐就会损失掉。
所以达摩在那儿坐十年,他没觉得不乐,你试试,马上就不乐了。所以我们由于对内的关注散逸了,我们就会转移到对外的关注。对外的关注对世俗来说也是正常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我们每个人天生都下意识的追求舒适度的,所以冬天能有地暖,烤个火那就得劲,这也是正常的,这是身体基本的向度。但是人最重要是能驾驭你自己的身体,否则的话,你要是由着身体的追求,你要知道,你就进入无主的状态了,身体会越来越来,因为身体有欲望的象征,越来越带你走,越来越带你走,你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满足它。所以,人会被识见所不断的引诱着走,人就会没有天受了,这一段特别关键。
黄花长蕊 不知其名
取一枝入瓶 满室清光
余爱写墨 花开独坐
题以寄远也
戊戌四月 连山
“然贵乎人能尊,得其寿而不尊,自弃也。”人能够受,才是人的尊严所在,结果人受而不尊,就是自暴自弃,上天赋予你的本性你并没有真正使用它,就是不尊重它,你不尊重人的本性,你就是自弃,该你停你不能停,该你行你不能行。
“得其画而不化”,只是描像,而不能化的人就叫自缚,什么叫自缚?就是画奴。你看,今天去看美展,几乎都是画奴。今天全国美展就是工笔展,所谓工笔展就是画奴,并不是说工笔不对,看今天还有人能画工笔吗?
工笔是什么人能画的?如果他不是气局大,他画那很精细的东西,马上就局促,他就会被形局促,只是显摆你看我画的可像?工笔画,不是实际现实的处理,他完全有一种礼序在里面,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庄严感。他并不是今天写实式的具象,他用具象的方式不具象,这才是工笔的高境界。我们今天哪能画成这样呢,今天要么就是变形了,变形弄得人不像人,你看今天的画,完全变形,画的就莫名其妙。所以大象这是你的一个向度,因为你容易画细的,但是细就要细出庄严感,才有宏大气象。若细的没有庄严感,就叫纤细,那就麻烦了。
你要知道,这种庄严气象,就是所谓“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画家借着这个人的形象,赋予它难以名状的一个庄严感,在画面上我们就能看到。真人肯定不是这样长的,但是他真的是把一代高人的气象给画出来了,我们一看就觉得有洁净感,长得虽然不算俊,但是就觉得特别耐看。
所以,那些徒式临摹的人,就是以形自缚,就是奴隶。世间所有的事情不都是这样的吗?被钱奴役的人就只顾挣钱去了,挣的再多,他只是好像以自己挣的多为成就,买房子、买车子、买鞋子、买衣服都是这样,被反伤,完全是自缚。
自古画竹者高士如云
取其虚心高节 不改其操之德也
戊戌四月 雨后写一杆 连山
节录:连山先生讲《石涛画语录》第八课
听打:张小蒙
校对:明此
编辑: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