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盛夏,北京西郊的校门口,一块崭新的木牌悄悄挂起,上书“北京一零一中学”。看似平常的改名,却让周围几个跑来凑热闹的孩子不停嘀咕:“怎么不是第八中、第九中,偏偏是一零一?”对这所学校的掌舵人王一知来说,“一百是过去成绩,一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她当时的回答简洁有力,却暗藏心迹:教育,是她唯一愿意全情投入的战场。
追溯到1901年,湖南芷江的一声婴啼改变了一个封建大宅的命运。父亲杨凤笙重男轻女,母亲谭氏挨打后仍强撑门户,小女孩在夹缝中长大,14岁独自背着行李进了省立二女师。学费全免,可生活费分文没有,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没将她压垮,反倒炼出一股“认死理”的劲头。
1919年,五四的火焰从北平烧到长沙。街口退学潮水般的队伍里,王一知高举标语,嗓音嘶哑却毫不退缩。有人劝她“女孩子别太拼”,她抬头反问:“不拼的结果,就是继续当亡国奴吗?”一句话堵得对方说不出话来。也是从那一年起,她与“服从命运”四个字彻底决裂。
到上海平民女校读书时,课堂上是陈独秀、刘少奇、茅盾的讲授;课后,她把同窗丁玲拉进巷子,演练演讲稿。张太雷在一次工人夜校活动上注意到这个眼神坚毅的姑娘,两人并肩忙碌,爱情随之萌芽。1927年广州起义,他牺牲的噩耗传来,她抱着刚满月的儿子愣在屋檐下,眼泪一滴没流,却当夜把孩子托付邻居,重新走回地下电台。
抗战爆发后,王一知与龚饮冰伉俪重返上海。湘绣庄里灯火常亮,她在阁楼收发密电,纸条塞进绣花枕套。不久一道密码被日军捕获,她踩着黑夜挨家敲门转移线路,最危险时离宪兵队不过一条街。多年后她轻描淡写:“只是腿脚快点,并不神奇。”听者却心底一凉。
1948年西柏坡接见,毛主席看着这位昔日地下“老交通”笑道:“该到地上晒晒太阳了。”周总理补上一句:“北平妇女工作需要你。”气氛热烈,可她只是欠身致谢:“更想找个用得上自己的岗位。”那是一回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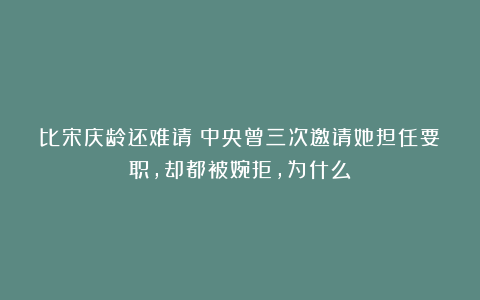
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邓颖超再次邀她进妇联。老朋友端茶时开玩笑:“是不是还得我们合唱一段才能把你留住?”王一知却已做了决定:新中国百废待兴,最短缺的不是干部而是人才;师范出身的她认准课堂比办公室更重要。第二次婉拒,就此尘埃落定。
第三次邀请发生在她任吴淞中学校长一年后。组织想调她进教育部,理由充分:党龄老,资历硬,基层经验也有。谈话室里,负责同志列出几条晋升路径,她听完只提一个要求:“让我留在学生堆里。”几分钟交谈,事情定局。有人摇头感慨:“比宋庆龄还难请。”此话虽带玩笑,却不无道理。
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她先后执掌吴淞中、华北中学、北师大二附中。办公室永远灯火通明,桌面摊着一叠叠教案。学生犯错,她先问动机,再抓方法,从不简单批评。中央领导子弟在一零一中学与工农子弟同桌,她强调的是“互帮互学”;工人家庭的孩子交不起伙食费,她拿出工资补贴,从不声张。
有意思的是,身边同事记得她对行政排场向来敏感。一次校庆活动,地方领导送来小轿车接送,她转身招呼学生:“活动完把司机师傅留下来吃食堂,两菜一汤就好。”主客皆愣,最终车子空驶,她跟着学生步行返校。教职工背地里议论:“王校长怕是天生和’排面’犯冲。”
王一知在校三十年,培养学生近万人。老兵、科学家、艺术家、外交官……不同领域的人后来提起名字,无一不先说一句“恩师严而慈”。1991年11月23日,病逝消息传开,北门口排起长队,旧时电台同伴、早年工友、白发苍苍的学子,自发站成静默的人墙。有人低声道:“她这一生,只为一件事——种人。”
中央为何三次挽留都留不住?答案其实早在她自己讲过的话里:“做官可一时风光,做教育能代代生根。”这一句,大概比任何官方任命都更能说明她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