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三国的星空》对《短歌行》的误读误用
——兼论《短歌行》非求贤之作
本文不评价《三国的星空》对曹操角色的设定,只讨论其对《短歌行》的引用。按一般教学进度,10月高一学生正要学习《短歌行》。无论您是否同意本文观点,都可以拿影片来或正或反地作课堂讨论的引子。
影片有两次引用《短歌行》的首四句: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第一次是曹操在酸枣出击董卓军大败,死里逃生后在阵亡将士的坟前念出这四句,以表达哀悼之情。
第二次是官渡之战前曹操赴袁绍宴请,袁绍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劝曹操享受诗酒年华,而放弃与自己争权,曹操回应:“’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那是感叹阵亡将士去世太早。”
影片为了塑造曹操的正面形象,把曹操历史上的一切言行都往忧国忧民、忠君爱兵上去靠。台词和情节可以编造,但《短歌行》这种写定的文本则如金石,可能遭磨灭但决不可移易。
孤立地看“譬如朝露”,确实可以泛化理解为人寿短暂。但上句“人生几何”是就常态的人寿而论的,不是指战死这种死于非命、未尽天年的情况。下句“去日苦多”,是说作者(曹操)苦(悲哀)于逝去的日子已多。战死将士的去日等于其人生的总长,如果去日已多,岂不是自认为活够了?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必须连贯起来理解:人生就如早晨的露水般短暂,逝去的日子已多,将来能对酒当歌的日子显然更少,这让人悲伤。
所以,影片如果单用“譬如朝露”哀悼阵亡将士,还算断章取义得有理,但现在让曹操说“’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那是感叹阵亡将士去世太早”,就完全不通了。
至于在阵亡将士的坟前念出四句诗,更是莫名其妙。坟前无歌无酒,阵亡将士生前亦无歌酒享乐,“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用不到他们身上。
影片也有用对《短歌行》的地方。袁曹酒会上,袁绍引用“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炫耀自己的财富权势,又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表示对曹操结好(臣服)自己的期待,曹操引用“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把与袁绍的友好关系诉诸过去(将未来悬置),都算不错。
影片始终未引《短歌行》全诗,但难免让人误会《短歌行》作于官渡之战前,甚至作于酸枣战败后。这种误会必须澄清。
《短歌行》的创作时间确实存在争议。《三国演义》说曹操在赤壁之战前的酒宴上即兴创作此诗,固然是小说家虚设的情境,但在时间线上大致不差。因为诗歌结尾“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壮语只能发自权倾天下者之口。官渡之战前曹操仅有兖州和徐州,是不足以自称“周公”的。
讨董时的曹操更不可能自称“周公”。曹操在建安十五年(210)作《述志令》(又名《让县自明本志令》),说自己早年“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受封“曹侯”是他破黄巾时的目标,讨董时大致亦然。
由“曹侯”而“周公”,是伴随权势扩大而带来的自我定位的变化。
定位的提升,带来的不一定总是兴奋,也可能是忧惧。“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卑未篡时。”(白居易《放言》)周公尽心辅佐年幼的周成王。但政敌在列国间散布流言,说周公欺侮幼主,图谋篡位。曹操也被时人指为王莽,周瑜就说过:“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军事上的占领并不等于人心上的收服。曹操需要一个名义来让自己的权势有一个立足点,以获得所作所为的合理性。
现存曹操《短歌行》有两首,其一即课本所收,结尾定位于“周公”。曹操“吐哺”是作出一种勤于王事的姿态,通过角色扮演代入历史人物,让天下人认可其地位。“天下归心”出自《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政治文章做在“灭国”“绝世”“逸民”上,读者是“天下之民”。同样的,“周公吐哺”是为求贤,曹操“吐哺”却是把求贤的文章做给天下人看,为了“天下归心”。
另一首《短歌行》评说三位史上的实质掌权者:
《短歌行(其二)》
周西伯昌,怀此圣德。
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修奉贡献,臣节不隆。
崇侯谗之,是以拘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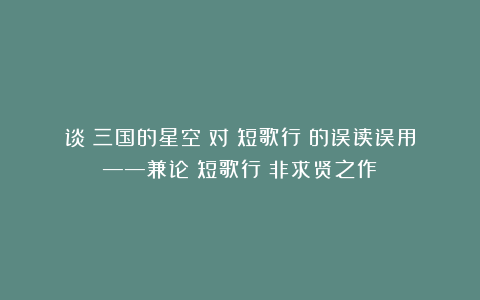
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征伐。
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
犹奉事殷,论叙其美。
齐桓之功,为霸之首。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一匡天下,不以兵车。
正而不谲,其德传称。
孔子所叹,并称夷吾,民受其恩。
赐与庙胙,命无下拜。
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
晋文亦霸,躬奉天王。
受赐圭瓒,秬鬯彤弓,
卢弓矢千,虎贲三百人。
威服诸侯,师之所尊。
八方闻之,名亚齐桓。
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其名纷葩。
“周西伯昌”三分天下有其二,仍守臣节;齐桓公九合诸侯,仍畏惧周天子之威;“晋文亦霸,躬奉天王”,但“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其名纷葩”。晋文公与诸侯在温(河阳)会盟,想率诸侯朝见周襄王,因为担心诸侯不服从,就派人把周襄王召到河阳来接受诸侯朝见,又因为以臣召君不合适,就假称周襄王是为巡狩而来的河阳。这种谲诈的行为是为尊重天子的权威,还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舆论哗然,后世议论纷纷。曹操所忧惧的正是这种“纷葩”。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曹操此时需要的不仅是“丞相”这种政治体系中的名分,还有“周公”“周西伯昌”和“齐桓”这样正面的、已有历史定论的、可供自己参照和他人类比的名义。这是政治统治的需要,也是自我安慰的必要。
但这个让自己安心的“名”(定位)仍是随主客观情势变动的。到曹操快死前的几个月,孙权劝曹操做皇帝,曹操的臣下也借机劝进,曹操却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周文王”即“周西伯昌”,但不等于“周西伯昌”。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历史的发展把曹操推到了不曾有先例的境地,不见轨道,只有虚空。他的人生难题不是如何踏尽阶梯,而是如何安稳停歇。从尊奉天子的“侯”“伯”,到开启新朝的“王”,曹操是否找到了可以安稳停歇的枝头——那个他所期待的历史定位?还是说,他用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创造了中国政治生态中的一个新定位点,叫“曹操”。
图书推荐
公众号ID:jlzxzwxp
钟楼语文
为学生立心,
为教师立命,
为语文继绝学,
为教育开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