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入围两部纪录长片《劳途归巢》《浪花儿》。影展第四日,《劳途归巢》进行全球首映。
《劳途归巢》记录了时代变迁下西南地区返乡青年的命运起伏,镜头对准返乡后在酒厂劳作的工人潘昭德,长达四年的拍摄捕捉到:特殊时期艰难工作,出走的妻子,生病的父亲,精神病院的母亲,两个年幼的女儿。纪录片平淡讲述着看似苦难的日常,以小见大般的呈现个体的磨难抉择,乡镇产业的崛起,家庭结构的变化等等。
平遥电影展结束后,凹凸镜DOC与《劳途归巢》导演郑旭松展开聊天,聊拍摄对象,聊制作团队,聊家乡……聚焦于那些未曾提及的点面,以此作为平遥展映期间映后和新闻发布会的补充。
以下为整理编辑的专访文字部分:
平遥纪录片新作《劳途归巢》:乡镇青年如何找到人生出口
撰文:FFAY
编辑:张先声
郑旭松:没有,比较坚定的是让他作为主线人物。当然之前有想过,因为他们车间是三个人成一个小组。小组的这种关系,其实也是我很感兴趣的。但是通过多条线叙述,首先肯定是有一定难度的。其次,我觉得作为影片来讲,尤其是纪录片,它的聚焦性其实也比较重要。所以,后面我们还是坚定的围绕到潘昭徳一个人物身上。另外一条线索是工厂的背景变化,比如说它受疫情的影响,或者是说工厂的一些人事变动,或者是类似于这些的一些关注。
凹凸镜DOC:那在整个纪录片制作过程中,您有干预干扰或者是有摆拍想要的内容吗?
凹凸镜DOC:我记得在新闻发布会上,有提到拍这个片子的背景是之前你与一家企业有过合作。企业那边对成片会有一些干预,或者是要求呈现一些企业那边想表达的东西吗?
凹凸镜DOC:企业品牌一出现,有些观众可能先入为主的想,这是不是一个带有一些企业宣传性质的片子?
凹凸镜DOC:相当于在剪辑上就取舍掉了。
郑旭松:对,从对影片的衔接,以及对影片的推动,整体分析后,2023年的这一部分的素材隐藏下来了。有时候我们觉得也需要克制一些,做一些留白。
凹凸镜DOC:整个片子时间跨度也挺长的,最后是如何确定停止拍摄的这个节点?
郑旭松:纪录片呢,我一直觉得它和绘画一样,没有所谓的节点,只要你愿意拍,你一直可以拍的。在很久前听说过一句话,“每个人的人生,只要你去记录,它都是一部电影”。所以这个时候我不会认为有这个节点。
那最后怎么开始去呈现的呢?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素材以构建出一部90分钟的三幕片,就尝试开始剪。剪辑呢,剪了大半年,快接近一年,最后看到2025年春节的镜头,实际上我们的剪辑都已经差不多做好了。我们听说今年白沙镇会有玩龙舟、打铁花的活动,我也感兴趣,就问潘老师要不要去看,他说可以带小孩去看。我也挺好奇的,我自己也想去看一看,这个也有小时候的符号记忆。然后我们就增加了这样子的场次。
事实上我们在2024年第二季度就开始在剪辑。
凹凸镜DOC:拍龙舟时,剪辑已经过半了,当时有没有想过给潘昭德看粗剪成片?
郑旭松:我们做首映的时候,我一直在给组委会那边说,我不希望我的主角能看到我的影片,这个涉及到纪录片伦理问题,第二个也会影响他。他父亲的去世,他老婆的离开,无疑这些在我思考上都是对他的二次伤害,把他已故的最亲的人,然后再次活生生的呈现在屏幕上,他的情绪是受到波动的。
所以直到现在,或未来很久的时间,我觉得都不是最适合他看影片的时间。一个是我站在导演的角度思考,第二个我站在他朋友的角度思考。那一天他要做映后,被志愿者提前一些带进去,其实他情绪已经受到了一些干扰的,也就意味着我判断是正确的,他确实在这个时间段是不适合看这个影片,所以我没有给他看。在这之前,他没有看过任何一个镜头。
凹凸镜DOC:他有自己主动提出过想看或者好奇吗?
郑旭松:他没有,可能他对记录电影也没有认知和概念,他提出过做好了可不可以给他留一个备份做纪念。我回答他可以的,一定会给。
我在这期间还给他们家拍了一些照片,我一直有想法把这些照片打印出来给到他,但是直到今天我都没有,时机不适合。因为我们不是做一个短视频的东西,我们不是做一个今天去博流量或者是快速放在网上求别人同情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它属于你拍摄以外私密情感的事情,你愿意和别人相处,你就这么去做就好了。所以这个点上我们现在是朋友,会经常有交流。但是回到影片的本质上来讲,我会有时候替他去做一些考虑,大概就是这样。因为上次他在首映的时候进去,然后他又出来了,因为他绷不住,情绪很崩溃。
凹凸镜DOC:要保护我们的拍摄对象。关于女性这方面,其实在整个成片里面,作为女性的呈现占比不多。
郑旭松:是的,占比不多也是从纪录片伦理的角度考虑的,比如说他妻子的出走,其实是他家庭内部最私密的,也是他在情感上比较有伤痛的一个伤口,这是在我的认知。如果我们追着去展示,第一潘昭徳可能不那么愿意,比如说我们脱离这个拍摄的这条线去拍他,其实我能感受到拍照者的内心也是惶恐的,他也很担心去拍到一些他过于私密的问题。
第二个我们都没有把镜头对向他的女儿,去拷问她或是追问她对家庭的感受,比如说你想不想你妈妈,你喜不喜欢妈妈?我们没有做这种问题性的干扰,我觉得这是有悖人伦的,这对小孩子的成长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和影响。我觉得纪录片它应该有底线的,它的底线在于故事的完整,而不是去摧毁别人生活的完整。
那他的妻子呢?我们确实建立过联系,也沟通过拍拍她在外面的生活,她拒绝了。拒绝过后,我也有一些思考。往往这种妻子在影片所谓的缺席,恰恰是一个在场。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潘昭徳是否和她打电话,女儿有没有在提及她的这种角度,也有去交代清楚他妻子的出走过后对这个家庭的变化和影响。至于她怎么出走,这个也是非常私密的问题,他们并没有离婚,只是说可能出于所谓的平等,自己过自己的,但是其实没有回来过,就包括我们后面没有拍了,还是没有回来过的。最后她拉着一个箱子离开,小女儿送了她一段。那是最后一个镜头,物理生活中也再也没出现过。
我觉得个人私密性不能去呈现社会性的朴实性,普遍性。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保持留白。她可能是多因素离开的,家庭的经济压力,也有可能是自己追求更自由的生活向往,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不合。因为我们手上确确实实在她回到家后,有一些素材可以去构建的出她到底怎么离开的。但是,我想这个片子还是平淡一点,我始终觉得她的缺席比在场更好,诉说再多,不如留白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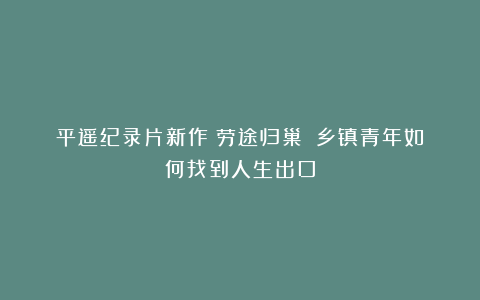
我把这种尊重还给生活的本质,不要去摧毁他们生活的原本样貌。这个部分就留给观众,他们可以去讨论,也可以去思考。如果我是一个相对不会思考这些的导演,他们现在可能是离婚状态。
凹凸镜DOC:那这样就相当于你干预了他们的生活。
郑旭松:其实这个都不需要太多干预,就是在他情绪最崩溃的时候,他会以朋友的身份来聊到他感情的问题,但凡在这个时候给一点比较偏激的意见,我应该是可以拍到他们离婚的镜头,这个毋庸置疑的,只是我没有这么去做。其实我拍他之前我们有两个预设,一个就是他父亲的去世,第二个预测就是离婚。父亲去世,我们有经历到,然后离婚没有经历到。
凹凸镜DOC:去世那段在观看时冲击蛮大的,对于纪录片来说,不可控的一个事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
郑旭松:对。其实我们全篇都在克制,包括他父亲的葬礼,我们都非常克制。克制的点我们有非常多,他父亲去世过后,当地叫上山,埋坟的镜头我们一个没用。最后他烧稻草,一把火结束了这个场景,我们还是想用克制的方式去表达。后面也有听到一些声音,私底下来跟我聊的,说有时候是不是给得太少了,我们能够感受到有一些素材,但是只愿意给那么多。我们在这个角度一直想的还是尽量的留白,我们拍了四年,四年的素材,剪90分钟的片子,肯定是有很多选择的。
凹凸镜DOC:我看剪辑师最后署名是鄢雨,是如何建立合作,您作为导演在整个剪辑过程中的参与度有多少?
郑旭松:大概介绍一下鄢雨的背景,有部纪录片叫《淹没》,他是《淹没》的导演之一。
我们之前就很熟,我在做这个影片的时候,有一次他来到我的工作室,我当时在剪这部影片,他提出很多建议,对于其中很多建议我也是很青涩和懵懂的。然后他说要不我来帮你弄吧。
我们熬了无数个夜,每天到早上五点钟左右,回去在家睡个觉,中午又去我工作室弄,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在一起工作的,他并不怎么听得懂江津话,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在一些抉择和讨论上要沟通好,大概的工作关系就是我把每一幕每一段要核心体现的东西表达,然后他来剪辑大概是这样子的一种配合关系。我会整理好素材,大家共同在操作。遇到障碍了,我们又会停下来讨论,再剪辑再讨论,再不断的去反思。他是正儿八经的做到一个后期导演或是剪辑指导的核心工作,他在给这个片子带来很大贡献的同时,也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多的建议和指导。
凹凸镜DOC:音乐方面,是发光曲线的薛大染,您是如何找到他进行合作的呢?
郑旭松:我和他也是多年的朋友,然后,我觉得他对艺术性的理解,对这种所谓社会反叛性的认知,还是在同一个频道。我告诉他,可能在哪几个节点上需要一点音乐,音乐方向是怎么样,音乐的整个计划一句话说的清楚,前面我的几个节点可能需要一些碎的不成曲子的一些音符出现,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可能会汇成一支曲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还是想减少音乐对故事的沉浸式,以及对故事本身的一种干扰。
往往在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坚决不能用音乐,当然用音乐肯定会把观众带到另外一个氛围层面,但我觉得这是音乐带走的,而不是故事本身带去的,所以我不那么认可。音乐它可以是独立的创作,但是音乐它绝对不是为了去煽情观众的一种手段。和薛大染聊得很好,所以他做好了直接发给我,我就用了,也没有修改。
凹凸镜DOC:摄影方面,我看除您之外,还有一位聂朝一老师,在拍摄过程中你们两位是如何分工拍摄的?
郑旭松:这里有一个误会,其实总共参与拍摄的有五个摄影老师。因为时间比较长,有时候是轮流在拍,可能这一段谁有时间正好就去拍。前期我拍得比较少,前期主要是给他们做一些场景分析,以及看他们拍到什么,做一些统筹上的这个工作分配以及思考。后期呢,在第三幕也就是2024年的镜头时,已经没有钱了,很穷了,不能再雇人了,那这个时候所有的镜头是我一个人拿着相机返回去拍的。所以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在拍,我们基本上最多两个机位在现场,平时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个机位。几个人相互轮流去做的。
凹凸镜DOC:在整个这个拍摄过程中,让你最难忘的或者印象最深的一段记忆是什么呢?
郑旭松:好多,我大概描述两个吧,一个是宏观的,一个相对比较微观的。微观的就是我反复在提到的一个点,潘昭徳父亲去世的时候第一个给我打的电话。我后面有时候也在内疚,内疚点是什么呢?他是正儿八经把我当成内心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好像每次去都带着拍摄的功能目的。这个是我很内疚的一部分,我没办法做到像他一样很真挚的对我。所以这是我很大的感受,我为什么不能做到平等,在这种情感的付出上,这是比较微观,来自于自己的。
另外一个感触呢,在于他工作和身份的变化。他在我们影片拍摄之前是一个农民身份,从自己的老家出去打工,学到了一些知识,然后再进厂,在广州一个灯具厂。回来依然在厂里面,在我看来是中国社会这种所谓的农业转型工业的一个社会性层面的社会结构变化。在影片中又发现当他工人还没有做好,还摇摇欲坠,在努力往前的时候,会发现社会经济又一次发生了变化,然后就把他推向了主播台。
那这个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呢?这个就不单单是潘昭徳的问题,是对于每个人都一样。我们在社会的洪流中被推着往前,即便我语无伦次,即便我不管怎么样,都得去做,可能是我们每个人没办法的选择。那这个的折射可能在我身上,在很多人身上,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可能形式不一样,可能内容不一样,但是最后的结局是一样的。
比如说可以反复的听到类似于这样的台词,“那就是干”,我觉得这就是农村人的底层逻辑。裁员的时候也说不出什么话给自己争取一些福利。还有潘昭徳的父亲也是在说我们每天起来要吃饭穿衣,我们农村人就只有干。最后会发现底层的逻辑很简单,就是我们得干得做,没有那么多思考,没有那么多所谓的正确性,最后会发现整个群体的群像讲究的就是我们要干的,我们没有任何思考,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其实蛮多细小的点都很感触我,包括裁员,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大家工作都很卖力,不单单是他们,还有别的没有出现在镜头里面的人,被裁掉的也有。最后我真的有一种感受就是工作上的骄子却成了职场的游子。真的有那一个阶段,不单单是一个厂的问题。身边很多人其实那时候都丢失工作,你身临其境的站在这些人之中,看着他们失去工作,真的就会有很强大的感受,就是刚才我说的,工作上很努力的人,却成为职场游走的人。
凹凸镜DOC:最后怎么定的这个片名《劳途归巢》,有考虑过其他片名吗?
郑旭松:这个片名是去年就敲定了的,敲定的还蛮早的。这个片名也有很多人给我提出意见,但是我比较坚定用这个。这个劳途,它不单单是路途,很多人认为劳途归巢是他在外面打工,然后今天回到自己的家,觉得是一种迁徙,这种物理上的迁徙。
我更多的理解是他所有的劳作其实是为了所谓的整个家。哪怕这个家是由父女三人构建起来的。这种劳途其实就是回归到这个家。在我看来,它不一定是物理性的,可能就是生活使命感的状态。
这整个思考也离不开英文名字, a long way home。它主要构建的是我主要想表达一个观点,回到家它只是起点,不是终点。虽然我们觉得可能家是温暖的港湾,但是它依然是你的起点而已,也可以理解成我们每个人回家的路是非常长远的,需要有很多路要去走,即便就是回到家过后,也是需要有很多路要走。
凹凸镜DOC:您在平遥映后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可能家乡不需要我们,但是我们一直需要家乡。”回乡拍摄这部纪录片期间,您觉得家乡最直观显著的变化是什么?还有就是您这次回到家乡,它对你带来了什么变化影响?
郑旭松:其实是拍这个片子过后,我的感受和变化。不单单是一次两次这种回到家乡物理性的认知,反而是在这里相当于工作了三、四年的感受。首先,因为我已经十几、二十年没有生活在农村,甚至更久一点,时常对老家的印象是怀念性的,可能有小时候的玩伴,或者是我们老街的这种感受,因为它在记忆中还蛮清晰的。所以这个时候对家乡的认知,真的就是乡愁,所谓的对家乡的怀念。
通过这个拍摄,我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我的家乡有了工业化的园区,以及出现了大面积的返乡潮,以及类似于潘昭德这样空心化的家庭。类似于这一系列的变化,我发现很多人认为家乡很老龄化,因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这几年,其实很多年轻人又回来了,其实在外面好像生活得也没那么如意。他们回到家,也在撑起家乡的发展。
如果我们把刚才那一个比喻成乡愁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家乡的疼痛。它依然出现了类似于刚才我说的这么多问题,但是还有一波年轻人,在自己的家乡奋斗。这种奋斗,不是我要改变我的家乡,它是为了个人在奋斗。无数个个人,叠加成了中国乡镇转型所面临的这种经济模式,或者是说他们精神归属的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精神归属,大部分回来说我可以照顾我的爸妈,我可以带孩子,那自己的家乡好像又能赚到一些收入。所以,在我看来是一种经济模式,以及社会结构,还有精神归属等一系列问题的这种体现。
这个时候,我对家乡的认知不再是很浪漫,与乡愁有关的,反而它是一种能够震惊到我,能够让我共鸣的,大家在承受这样的疼痛。在这个时候,我也看到了类似于潘昭德他们这样的人身上的韧劲。这种韧劲是什么呢?这它不是一种励志式,它真的就是我刚才提到过每天日复一日的奔波在摩托车上,回来给女儿做饭,陪女儿写作业。很简单的,他依然在很努力的构建这个家,哪怕这个家是父女三人相依为命构建的,哪怕是摇摇欲坠的,但是你有另外一种感受。即便它是三个人构建的,它的情感单元也是非常丰富坚固的,它没那么容易被摧毁。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们其实热爱的不一定是故乡,其实就只是自己的家。
在我看来,我的故乡有无数这样的人在构建,在往前,在努力。此时,我们才会有大面积的人认知到,今天中国的农村好像都发展得很不错,很经济化,其实是由一代一代的人在努力构建出来的结果。不然他们依然会回到传统农民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式的生活。乡村的建筑也绝对不会有今天这么漂亮。因为正是因为他们出去打工,看到了沿海一带的乡村是怎么修建的,然后自己赚了钱也想改变家人的生活,才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现象。
这么说可能有点大,我觉得这才是中国这种广袤乡村上用沉默用坚实最打动人的方式,再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自己家乡的人,他们才是根基。不是说所有的城市有多发达,当生活得不尽如人意的人也过得很好,这才是整个社会的变化。
现在我对家乡的理解没有那么多乡愁了,反而更多的是家乡在经历这一系列变革过后,还有一种韧劲儿,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我才觉得哪怕可能家乡不一定需要我们,但是我一直觉得家乡有一种伟大感。我知道可能这么说有点过,有点太过于庞大,我的认知是这种庞大的认知体系,一定是建立到最深入,最 local 的一个地方和一件事情上面。
凹凸镜DOC:您后续还有纪录片的拍摄计划吗?
郑旭松:我现在已经在拍,已经拍了蛮多的。这部纪录片也是在江津,也是在家乡,它和长江有关。它主要讲的是在禁渔期下的一些长江两岸人的身份命运的变化,也是游离在这种社会边缘性的人物。我还是比较热爱和习惯于去观察或是去记录可能光亮照不到的一些人和事物。
关于影片
生活在长江中上游的乡村青年潘昭德,热情而充满希望地投身于一家当地的酿酒厂劳作。兼顾家庭与工作,是他对目前生活的最大挑战。他每日往返于工厂与家之间,同时也不时去往精神病院和医院。年迈的父亲,失智的母亲,出走的妻子,年幼的一双女儿,构成了他需要努力面对的全部现实。
个人命运的裂隙与时代发展的阵痛交织在一起一个普通的乡村青年,又将如何面对自身的局限,将如何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关于导演
导演、影像创作者。创作艺术影像作品《Life is endless》《Where to GO》等。
近年导演的纪录短片《上山者》获2024年维也纳国际电影奖特别提及,《劳途归巢》入围第九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
凹凸镜DOC
ID:pjw-documentary
微博|豆瓣|知乎:@凹凸镜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