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的政事文
——兼论杜甫与唐代“古文运动”之关系
内容提要
政事文是指作家以官员身份对直接参与的日常具体政事提出见解、解决方案的创作,包括公文文体以及涉及公共事务处理的其他散文文体。杜甫现存的 9 篇政事文,反映了杜甫以官员身份对具体政务的建议和思考,这些建议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高明且实用。杜甫因疏救房琯而开罪于君,失去参与高层政治、建立重大事功的机会,但此事不足以表明杜甫缺乏行政能力。无论在朝、在野,杜甫始终积极入世,勇担社会责任,不仅以一个诗人身份观察现实,抒发感慨,而且以一个官员身份和视角实实在在处理政事或提出真知灼见,显示他具有突出的政治见识和行政才能。杜甫的政事文,源自独特的实际参政经验及其儒学信仰,与其“诗史”创作同声相应,表现出自觉革除骈俪、以古为新的特点。追溯“古文运动”之“前史”,杜甫的创造及其贡献不可忽略。
「《中国文学研究》2025年第2期」
何谓政事文?检索知网,尚未发现学者使用这一概念,但有两篇论文使用了“政事诗”的概念:“政事诗主要指那些指陈朝廷政策,评论国家时局形势,表现诗人关怀国计民生,社稷命运的诗歌。”[1](P197)“政事诗是集中反映朝廷统治、政治制度,评论国家时局,表现文人关怀民生、社稷的诗歌。”[2](P126)两个定义差不多,不过,显然都是广义的定义,本文不取:中国古代的文学家追求入世,而且大多是一身二任——既是官员,也是文学家,其文学创作反映了他们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经验和感受,反映了他们对朝廷政局的关注、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古代的文学创作很少不在这个定义指称的范围之内。有的文章虽然也包含作家参与具体政事活动的内容,但对作家而言,重在即事抒情,而不是讨论事务本身,这并非本文所说的“政事”之文、“政事”之诗。所以,“政事”概念需要辨析。《世说新语》列“政事”一目,所指是王朝、政府的行政事务,包括帝王的公务活动,也包括一般官员处理的基层事务。唐代处理王朝日程行政事务的机构被称为“政事堂”,开始设置在三省之一的门下省,后移到中书省,是宰相议事决策的机构。其实,“政事”有大小,中国古代“政治”就是“布政治事”之“事”,偏指与王朝高层决策有关的活动,而本文所使用的“政事”概念与此稍有不同,指的是“政治”事务之外的一般行政事务、公共事务。刘勰就注意到这种区分,并关注由此造成的文体之差异:“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所谓“政事文”显然不是“王言”,也不是呈给帝王的有关程序性内容的章表等各类“上书”,大致是指一般行政机关、政府官员处理日常公共事务的公务文体,如谱、籍、簿、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共 24 种。因此,本文所谓“政事文”也不同于“政论文”,即刘勰所提到的“论说”,“论”“说”这两种文体侧重于论辩析理,著名者如李斯《谏逐客书》、贾谊《过秦论》《论积贮疏》以及桓谭《新论》、仲长统《昌言》、曹丕《典论》等,“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文心雕龙·论说》),这两种文体都是臣属就重大决策越级向帝王提建议,而不是日常处理的公文。因此,本文所谓“政事”,所指不是在朝堂内所论之政治大事,而是一般行政事务;所谓“政事文”,是指作家以官员角色,对亲身参与的日常具体政事,提出见解、解决方案的创作,包括公文以及涉及公共事务处理的文章①。这些涉及公共事务处理的文章,在现代的古代文学研究者眼里,基本上被视作“实用文体”的散文,少被关注,但是,从尊重中国文学自身传统的独特性以及认识作家生活、思想、创作的多样性、丰富性而言,值得关注。
在杜甫传世的全部创作中,数量最多的是诗歌,此外,还留下近 30 篇文,除了辞赋及其相关上表(9篇)和祭祀性质的祭文、墓志(6 篇)属于韵文,剩下的都是散文,而在这些散文中,除了《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阁画太一天尊图文》《画马赞》《秋述》《杂述》4 篇文之外②,其余的皆是与其参与的公务活动有关的作品,达 9 篇之多③,这些散文内容实用,文字古雅甚至晦涩——与南朝以来“文”“笔”皆趋向骈俪不同。很有意思的是,杜甫没有留下如王勃《滕王阁序》、王维《山中与裴迪书》、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这一类抒情写意、文字流丽优美的散文。杜甫自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他创作的诗、文数量肯定很大,遗憾的是在杜甫去世之后很多作品已自然散佚,今天能看到的确如韩愈所谓“太山一毫芒”(《调张籍》)而已,而我们今天能读到的杜甫作品,虽是后代刻意保存的结果,当然也经过了杜甫生前不断的选择、删汰——杜甫生前曾对自己创作的文字进行遴选、加工、编辑,可以说,现存的文章都是杜甫所认可的。宋代就出现了“千家注杜”的文化盛景,杜甫研究今天更加兴盛,但奇怪的是,古今学者对杜甫的散文关注却极其有限,甚至还存在严重误解,对其实用性公文研究更少④。杜甫这类散文有什么独特内容?写作上有何特点?杜甫为什么创作这些散文?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一
杜甫参政活动、行政能力及其政事文之内容
政事文的创作来自创作者直接的参政经验。杜甫出生于政治世家,从小立志参与政治,这既是个人生活所需,也是实现人生理想之必需。天宝五载(746),杜甫离开洛阳,西入长安求仕,“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当初杜甫也没想到这一去会经历十年的艰难。后来,他不得不反复进献大赋,才得到唐玄宗垂注和赏识,天宝十四载(755)十月才得到“河西尉”的官职,杜甫以这一官职“凄凉折腰”而未接受,最后被授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之职,从此步入仕途,开启其政事活动,并留下相关作品。
杜甫就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就赶上安史之乱爆发,玄宗奔蜀,太子李亨乘机自立为帝,至德二载(757)五月十六日,杜甫冒险从沦陷中的长安投奔到肃宗驻跸地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述怀》)。为了褒奖杜甫“辛苦贼中来”(《喜达行在所三首》)的忠诚,肃宗直接授予其左拾遗的职位。安史之乱让杜甫从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到左拾遗,无疑是一次机会难得的升迁。杜甫大为感动,准备努力工作,认真履职尽言官之责,以报答唐肃宗的信任,却意外地卷入房琯案。五月十日,唐肃宗罢免了房琯的宰相之职,而初上任的杜甫不识其中缘由,因“过于尽职”,抗疏救之,触怒肃宗,结果被肃宗诏“三司推问”。此事被后代学者认为“是公生平一大节”(张溍《读书堂杜工部文集注解》卷二《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后评),是杜甫“生平最大之事”(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五)。杜甫没有看到房琯案背后的二帝之争⑤,仅仅出于言官职责以及对房琯的了解,主动疏救房琯,差点被杀,幸亏得到韦陟和张镐的搭救,唐肃宗最后才赦免杜甫。杜甫于六月一日上《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其文云:
右,臣甫智识浅昧,向所论事,涉近激讦,违忤圣旨,既下有司,具已举劾,甘从自弃,就戮为幸。今日巳时,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镐奉宣口敕,宜放推问。知臣愚戆,舍臣万死,曲成恩造,再赐骸骨。臣甫诚顽诚蔽,死罪死罪。臣以陷身贼庭,愤惋成疾,实从间道,获谒龙颜。猾逆未除,愁痛难过,猥厕衮职,愿少裨补。窃见房琯以宰相子,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必位至公辅,康济元元。陛下果委以枢密,众望甚允。观琯之深念主忧,义形于色,况画一保大,素所蓄积者已。而琯性失于简,酷嗜鼓琴。董庭兰今之琴工,游琯门下有日,贫病之老,依倚为非,琯之爱惜人情,一至于玷污。臣不自度量,叹其功名未垂,而志气挫衄,觊望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何思虑始竟,阙于再三。陛下贷以仁慈,怜其恳到,不书狂狷之过,复解网罗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劝勉来者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岂小臣独蒙全躯、就列待罪而已?无任先惧后喜之至,谨诣阁门进状奉谢以闻。谨进。
这篇公文既再次表达了对唐肃宗的忠诚,对唐肃宗不杀之恩的感谢,也再次为自己疏救房琯申辩。他认真辨析房琯的为人,也承认房琯信任董庭兰的过失。此文表现了杜甫从政的态度:他不因唐肃宗赦免死罪而简单地感恩戴德,即使面对最高统治者,他不虚与委蛇,始终不卑不亢,坚持自己的立场,充分表现了认真、忠诚、正直的人格与处世态度。杜甫曾在《进雕赋表》中明确宣示要“正色立朝”,这就是他对诺言的践行。
杜甫六月初一上《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六月十二日联合其他三位言官,上《为遗补荐岑参状》,举荐戍边归来的岑参,可见杜甫不颓丧,不懈怠,认真履职如旧,没有受到疏救房琯案的影响。杜甫失去唐肃宗的信任,终于在两个月后的八月初,被“墨制放还鄜州省家”[3](P67)。杜甫到家之后创作了长篇大作《北征》感慨万千,情绪激烈,尽情抒发家国情怀:“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诗校注》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六月,杜甫被视作忠诚于唐玄宗的房琯一党而贬出京城,任华州司功参军,这是一个负责文教事务的岗位,包括官员考课、祭祀礼乐、学校教育等,琐务甚多。杜甫到华州后创作的《早秋苦热堆案相仍》曰“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反映出心情之烦躁,当然主要因天气,也因事务确实繁多,更有杜甫被贬导致心情不好这个原因。尽管环境如此恶劣,心情如此烦闷,但两篇公文足以证明杜甫工作仍十分严肃认真。七月间,杜甫为华州刺史郭使君撰写《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以进献给朝廷,本状是杜甫为华州刺史代写,目的是为皇上提供剿灭安史乱军的军事谋略。“残寇”指在相州苟延残喘的安庆绪及其叛军,当时安庆绪退保相州(邺城),企图东山再起,而唐军渐成合围之势。至德二载(757)初,安禄山被安庆绪所杀,安史叛军内讧起,至十月唐军先后收复长安、洛阳,李唐军队形成一鼓作气即可消灭安史叛军的大好形势,当时安庆绪退守相州(邺城),而身在范阳的史思明既害怕被安庆绪所杀,又怕唐军进攻,十二月宣布归顺李唐。文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战场态势,首先提出史思明的投降是迫不得已,杜甫提醒要警惕史思明有可能随时反水,再和相州的安庆绪勾结,因此,要吸取至德二载(757)收复两京时叛军诈降的教训,主张一举歼灭残寇(首先攻击的还是安庆绪部),不给其任何喘息之机。安庆绪在相州,后勤补给仰赖卫州(在相州南)、魏州(在相州东南),因此,唐军应先从东南部的郓城渡过黄河(唐时黄河河道在今日黄河河道偏北),攻击卫、魏,如果安庆绪救魏,则唐之郭子仪率领的朔方军从西北方向进攻相州;如果安庆绪回救相州,则唐军在东南方向继续进攻,几个方向的唐军“相与出掎角,逐便扑灭”——最终彻底消灭安庆绪残部。此文还附上形势图加以解释说明。杜甫熟悉河北之地敌我军力分布态势,考虑到后勤等要素,建议各方军力配合联动,说明杜甫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与韬略。事实上,在九月至次年三月,天下兵马副元帅、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等 9 位节度使,率各部唐军围攻相州邺城安庆绪部,这个策略正与杜甫的建议相同⑥。然而,唐军与复叛的史思明部实际作战时,九路兵马被狂风惊散溃败一溃千里:郭子仪军溃退至河阳桥,李光弼整军返回太原,其余节度使各回本镇,史思明重新占领洛阳,失败的原因与最高层的军事指挥制度设计有关。这篇图状充分说明,即使遭遇贬谪,杜甫依然密切关注着朝廷的平叛大局。张溍说:“遣帅分兵,掎角互进,算无遗策,谁谓公不长于经济?”(《读书堂杜工部文集注解》卷二)仇兆鳌赞誉说:“杜公借箸前筹,洞悉情势,此等文字,真可坐而言、起而行者,初非书生谈兵迂阔也。与韩昌黎论淮西事宜,俱推经国有用之文。”(《杜诗详注》卷二十五)仇兆鳌很多评论比较迂腐,但这句话可谓知言!
乾元元年(758)十二月,华州举行进士考试的初选,作为司功参军的杜甫负责为举子们出题,他共拟五道策问题目,即《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这五道策问立足于战乱未平的现实,分别从赋税、驿马供应、水路运输、军队给养、货币改革等方面提出问题。杜甫提出的这些考试题目,既联系经典遗教,更紧密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既有原则,也能联系实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体现了他“贵切时务”的思想倾向,可见他并非食古不化的书生。
乾元二年(759)立秋后,杜甫经过深思熟虑,果断辞去华州司功参军之职,漂泊西南,历经艰难于岁末到达成都,于次年营建了草堂,暂时安顿下来。但杜甫并不以隐士自居,依然关心天下,与地方官往来频繁。上元二年(761)八月十四日,杜甫来到成都附近的唐兴县,县令王潜“修厥政事,始自鳏寡茕独,而和其封内,非侮循循,不畏险肤,而行而一”,深受百姓爱戴,同时,还不扰民、不烦公,竭个人之财力,修缮客馆,杜甫因此撰《唐兴县客馆记》予以表彰。此文反映杜甫对建筑工程之熟悉,同时,此文是唐代流行的建筑记体文,却采用对话体,巧妙地借他人之口赞美王潜之政绩与美德,反映出杜甫对儒家“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理念的坚定信仰。
上元三年(762)四月,唐肃宗崩,唐代宗继位,改元宝应(762)。成都自上年十月到本年二月干旱。杜甫好友严挺之之子严武时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与杜甫过从甚密。杜甫见蜀中春旱严重,撰写《说旱》一文,主动向严武提出应疏决冤狱、减轻侍丁赋敛等改革弊政的建议,希望感天动地,天降甘霖,以纾解百姓干旱之苦。杜甫此文中对天灾的认识与观念,乃是继承了汉代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说,表明杜甫具备当时流行的天象信仰知识,同时反映杜甫继承儒家民本思想,具有对民生疾苦的一贯关切。干旱是自然灾害,古代遭遇天灾时,地方官员往往通过调整政策甚至通过斋戒仪式,企图避灾减灾。杜甫虽然已不是政府官员,却打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惯例,可见他内心仍然以官员自居,实在有“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唐元竑指出:“《说旱》劝郑公清理狱囚及勿役两川侍丁之老者,真仁人之言。”(《杜诗攟》卷四)
杜甫在蜀期间,当地政治形势并不稳定,关中和蜀都受到吐蕃进攻之影响。在安史之乱期间,唐廷顾此失彼,把本来长期驻守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和北庭的军队大批征调内援,结果“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资治通鉴》卷 223“广德元年”),至宝应、广德间,吐蕃大举进攻,不仅占领了陇右、河西许多州县,并于广德元年(763),南则攻克唐川西维、松、保诸州,北则攻入大震关,次年秋攻入长安,代宗仓皇逃往陕州。宝应元年(762)春,杜甫送严武回朝任职到达绵州,这时成都少尹徐知道发动叛乱,最后高适从彭州发兵,才平定叛乱,但高适也没有逐出吐蕃军队。杜甫因此浪迹蜀北诸地,广德元年(763)十月,杜甫在阆州撰写《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⑦。此文是杜甫代阆州王刺史向朝廷所上表章。阆州作为成都东部重镇,又地处梁州与成都之间要冲,地理位置颇为重要。然此表并未局限于阆州一隅,而是着眼于蜀地全局,针对两川当时之政治军事形势,提出一系列治理建议。杜甫为剑南道治政提出“宗王出镇”“合并两川”的主张,“宗王出镇”的思路与房琯、刘秩的政治主张一脉相承,因格于玄、肃二宗中枢政局的权力争夺和代宗对地方势力、宗王势力的防范而遭弃用,甚为可惜。“合并两川”的思想,则与广德二年(764)正月代宗诏令内容基本吻合,表现出杜甫对时局的深刻体察与谋断,可见出杜甫策议之切中时弊⑧。杜甫离开成都浪迹绵州、梓州、阆州等地,实际上对巴蜀山川地理、历史文化、风俗民情乃至当代政治展开了详细的考察。
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再镇蜀,派人通知杜甫从阆州回成都,并邀其入幕府作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东西两川说》就是杜甫在严武幕府中履职尽责的具体工作文字。此文隐约承前《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合并两川”之思路,论唐蕃关系之大局。当时吐蕃已攻陷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对成都产生巨大威胁,人心惶惶。身为节度参谋,杜甫向严武提出建议:为安定巴蜀局势,必须加强西山防务。杜甫认为,羌兵作为当时西部唐蕃交界地区备边守险的主力,急需统一指挥权,而对叛降无常的僚人,则应采取招抚之策为上,避免叛乱。此外,还要安抚流冗百姓,抑制豪族兼并,稳定后方。杜甫的分析缜密,对策具体可用,表明他对蜀中形势的深刻洞察及对民生问题的忧虑与关切。明代学者唐元竑指出:“《东西两川说》欲分诸羌部落各自统领,不使羌王得专制其命。此论最妙。汉晁贾之策亲王也,尚曰众建诸侯而小其国,况蛮夷乎!至于蛮夷畏汉法治之,诚宜宽大,勿轻扰之。赋敛宜薄,非宽富人,宽富人乃以宽贫人也。观其处分,井井谭兵羌,利弊亦甚悉,岂得谓非良吏才乎。昔人谓右军具经世略,惜为书法所掩。唯公亦然。今人但知其能诗耳。”(《杜诗捃》卷四)张溍曰:“公意在诸羌分党各属,而统以汉将,其末归于散兼并,择委任,可谓驭边之妙策。”“洞中机宜之文,即少陵之经济可知,谁云迂阔少实用?”(《读书堂杜工部文集注解》卷一)“因系向老友严武分析两川局势,申述治蜀方略,故不假润饰,将所见倾泻而出,如促膝相谈,随意流注,不屑经营结构、锻炼文字,时或有转接突兀之处,行文风格迥异于奉献表奏之作。”[4](P6478)
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去世,杜甫离开成都。经嘉州(乐山)、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云安(云阳),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到达夔州(奉节),直到大历三年(786)离开夔州,杜甫在夔州前后生活了三个年头,得到地方官员的照顾,夔州都督柏茂琳是照顾杜甫的官员之一。《为夔府柏都督谢上表》也是公文,属于代笔之作,此文当作于大历元年(766),为杜甫代柏茂琳草拟之谢恩表。柏都督,即柏茂琳,蜀郡人,是代宗时期巴蜀地区甚有影响之军政强人。累迁邛州兵马使,永泰元年(765)闰十月,西山都知兵马使崔旰杀剑南节度使郭英乂,柏茂琳率邛州兵讨之。永泰二年(766)八月,加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使持节邛州诸军事兼邛州刺史、御史中丞、剑南防御使及邛南招讨使,封上柱国、巨鹿县开国子。寻废邛南节度使,使持节都督夔州诸军事兼夔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夔、忠、万、归、涪等州都防御使。常衮《授柏贞节夔忠等州防御使制》称其“雅有器干,深于戎律,蕴三略以经武,秉一心而事君。蜀之西疆,久典戎务,惠和驭众,义勇安边。克励公忠,尤彰名节,令闻休绩,良深嘉重”。大历中,终同州刺史,卒赠户部尚书,谥肃。此文以柏茂琳口吻表达对唐代宗提拔的感谢,但是,文中所述施政方略:“伏扬陛下之圣德,爱惜陛下之百姓,先之以简易,闲之以乐业,均之以赋敛,终之以敦劝,然后毕禁将士之暴,弘洽主客之宜,示以刑典难犯之科,宽以困穷计无所出。哀今之人,庶古之道,内救惸独,外攘师寇。上报君父,曲尽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补失坠之目。灰粉骸骨,以备守官。”概括而言,即忠君爱民、宽政薄赋之意。虽为柏茂琳谢恩而发,也寄予了杜甫对柏茂琳的殷切期望,实则也是杜甫对治理一地政策的理解。此文与《唐兴县客馆记》颇为呼应。杜甫其实并未担任过地方官,但是他对地方官应该作为的理解确实符合儒家治国之思路。
以上九文,从文体看,有上表、状、策问、记、说,文体形式多样,其中也有上呈给皇帝的公文,但不是重大政治安排。这些公文内容却大体一致,都是杜甫对具体政务的思考或建议,有在朝堂履职的文字,也有在州县工作的记录,还有作为幕僚工作的思考,也有给地方官员的代笔,杜甫所关注、擘画的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民政乃至建筑等,可见杜甫知识领域之宽广,不仅谙熟儒学、礼仪以及官府办事制度、公文制度,还谙熟各地历史、地理、风俗,甚至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也很了解,善于从大局看问题,以儒家思想为原则以古鉴今,因此杜甫提出的建议不仅高明,而且针对性很强,实用性突出。
吴怀东著《杜甫与唐代文学论稿》
有人认为杜甫缺少行政能力,原因之一是他没有做过朝廷高官。按照唐制度,五品以上才是高官,杜甫一生先后担任的官职有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左拾遗、华州司功参军、严武幕府节度参谋,此外,严武推荐他担任检校工部员外郎(六品),赐绯鱼袋;代宗朝曾召补他为京兆功曹参军,但杜甫“不至”(《新唐书》杜甫传)。杜甫实际担任过的官职确实都不高,只是僚属——没有主政一方、一个重要部门的经历,也没有做到五品以上的高官——缺少“王佐”的经历,不是如张九龄、李泌那样深受帝王信任、参与了决定时代命运重大决策的政治家,而且在职的时间也不长,更没有创造出丰功伟绩。可是,我们从杜甫的政事文看到,无论在职还是不在职,杜甫始终以一个官员的身份思考问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云“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按唐制,杜甫一直享有官员的身份,不承担普通百姓承担的租庸调等义务),提出的建议合理而深刻。原因之二,在杜甫为政经历中,实际担任的最高级别的官职是左拾遗,这个职务级别不高但地位不低——直接在朝廷、在皇帝身边工作,可是他就任左拾遗不到半个月,就发生了房琯案——因为疏救房琯而遭到唐肃宗的打压,导致其晋升的仕途从此中断。对肃宗惩处房琯以及杜甫疏救房琯的是非曲直,学术界已有基本一致的认识,后代有学者认为这是杜甫缺少行政才能的表现,但我们并不认可此说。就杜甫在此事中的表现而言,于公于私、于情于法都没问题,并无可议之处:首先,参与“三司推问”的韦陟就说“(杜)甫言虽狂,不失谏臣体”(《新唐书·韦陟传》),宰相张镐也说“(杜)甫若抵罪,绝言者路”(《新唐书·杜甫传》)。其次,杜甫疏救的建议还是被采纳了,唐肃宗并未立即因董庭兰之事而立马处分房琯,至于唐肃宗后来降职处理房琯,是因为唐肃宗要通过打压房琯等玄宗旧臣,以实现打压唐玄宗的根本政治目的。论杜甫此次参政活动失败的根源,不是杜甫的态度和能力问题,而在于唐玄宗、唐肃宗父子相争这种背景和专制制度。杜甫参政的目标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可是,封建帝王哪是什么尧舜?这种特定的背景和制度才是理想主义者杜甫无法实现政治理想的根源⑨。杜甫坚信崇高的政治理想,正是这种代表人类良知的理想主义精神才确保人类社会走向良善,极为珍贵,杜甫具备封建官员忠君爱民的“官德”和实际行政能力。
杜甫自述“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他忠于君王,同情民生疾苦,关注时事,关注现实,这种思想与态度在唐代诗人中特别突出,深得后代学者一致赞誉。其实,杜甫还是行动家、实践家,只要有机会,就会为民请命⑩,他善于针对具体问题,切切实实提出深刻的思考和正确的建议,可见他不仅有“官德”,还有“官才”。宋人彭汝砺感叹杜甫“未及明君用”(《次皇甫子仁老杜诗韵》)。黄彻论云:“老杜《送严武》云:’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寄裴道州苏侍御》云:’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此公素所蓄积而未及施设者,故乐以告人耳。”(《䂬溪诗话》)两宋之际学者赵次公认为杜甫“负王佐之才”:“李、杜号诗人之雄,而白之诗多在于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负王佐之才,有意当世,而肮脏不偶,胸中所蕴,一切写之以诗。”(《草堂记略》)张戒说:“子美以为可以佐王者。……夫佐王治邦国者,非斯人而谁可乎?”(《岁寒堂诗话》卷下)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陆游就感叹说:“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读杜诗》)“少陵区区于仕进者,不胜爱君忧国之心,思少出所学佐天子,兴贞观、开元之治。”(《东屯高斋论》)刘克庄云:“二公(指李白、杜甫)皆唐佐命,勋在帝室,然皆不能攀致李、杜。”(《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八十五)明代学者唐元竑、张溍讨论杜甫政事文时,反复赞叹杜甫乃“良吏才”“长于经济”,显然,这和盛唐诗人普遍擅长写诗议论、不重视实干迥然不同。明末学者王嗣奭有感于世人对杜甫政治才能的轻视,极力为其辩解:“杜少陵自许稷契,人未必信。今读其诗,当奔走流离,衣食且不给,而于国家理乱安危之故,用人行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军机之胜负,地势之险要,夷虏之向背,无不见之于诗。陈之详确,出之恳挚,非平日留心世务,何以有此?”(《管天笔记外编》)清代蒋士铨曰:“先生不仅是诗人,薄宦沉沦稷契身。”(《南池杜少陵祠堂》)潘德舆认为杜甫见识超卓:“老杜’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岁时高议排君门,各使苍生有环堵’,’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为蓄积之厚,自比稷、契不为过。彻之识议,过人远矣。”(《养一斋诗话》卷十)因杜甫“疏救房琯”而遭到唐肃宗的打击、疏远从此失去晋升高层的机会,无法建立更大的功业,就因此说杜甫缺少行政能力,这显然是严重的误解。《新唐书·杜甫传》讥评杜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晚清施山《戏题杜集》说杜甫“词章万古此江河,契稷其如褊躁何。高论可怜无切用,人间名士散材多”,这类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当代学者冯至说:“杜甫一生关怀国运,蒿目民艰,可是他实际的政治生活却非常短促,虽然如此,他那’穷年忧黎元’的热诚并没有丝毫退减过。他也说过’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这不过是一时的解嘲,实际上他那忧国忧民的泪是一直流到他死亡的前夕。”[5](P160)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就指出:“如果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他们(指杜甫和陆游)的共同之处:两人虽然都是诗人,但都不愿意仅仅做一个诗人。然而,由于命运的捉弄,不,应该说由于命运的强迫,两人除了走诗人之路以外,竟别无他途。”[6](P122)洪业说得最明确:“杜甫不但是一个伟大诗人,而且是个富于经世济民之学的学者。”《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东西两川说》“即此数篇,已足见杜甫不是一个徒作高论,不合实际之人”,“杜甫论事常有先见之明;他设策以实用为要;他参谋有收效之功”⑪。
二
杜甫诗、文共生与政治革新、文化复古思潮
杜甫为什么要创作并刻意保存这些政事文?这些政事文与他的诗歌有何关联?在我们看来,杜甫政事文的创作,与他的参政经历有关,更与其思想信仰有关,并与时代思潮存在密切共振。
“学而优则仕”,唐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其实就有考核士子处理政事以及撰写相关公文的能力。既然参加行政工作,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就是必备的能力。唐代士子重要的入仕途径,是参加礼部主持的科举考试,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法、明算诸科,其中盛唐以来最受重视的就是进士科,唐朝初期的进士科考试为“时务策”五条,到了唐高宗调露二年(680),则加试帖经、杂文,形成杂文、帖经、策问三场考试制。此“杂文”泛指诗、赋、箴、铭、表、赞之类,其中既有纯文学的诗、赋,也有传统被视为与“文”相对之“笔”体的公文。杂文之外,还有策问,指考官就当前国家的时务提出问题,考生以书面的形式作答。通过科举考试只是获得“出身”,要步入仕途还必须参加并通过吏部考试才能正式做官,即所谓“释褐”,而吏部考试的内容就是身、言、书、判,其中书、判尤为重要,特别是判,判就是对日常政务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形成判决公文。《新唐书·杜审言传》记载:“(杜审言)恃才高,以傲世见疾。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集判,出谓人曰:’味道必死。’人惊问故,答曰:’彼见吾判,且羞死。’”可见,判文是很被看重的。
不过,从总体来说,有唐一代的文化风气(特别是盛唐时代)是,尽管也看重文人的实际行政能力,但更推崇文学才华;重视抒发感情、表达理想的诗歌创作,而不太重视应用性的公文写作⑫。尽管他们关心政治,积极参与政务活动,并且肯定也创作了不少政事文,但是,一般作家并不看重这类世俗文字。实际上,从魏晋以来,文人以从事具体事务为俗,追求高雅,热爱山水自然,以隐居为时尚,陶渊明就是这样的典范,谢灵运的山水诗集中体现了这种思想倾向。“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梁书·谢举何敬容传论》)山水、田园两种题材在唐代合流,充分表现了盛唐人追求高洁人格、澹泊自守的情怀,王维的散文名作《山中与裴迪书》充分体现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格调:“近腊月下,景气和畅,故山殊可过。足下方温经,猥不敢相烦,辄便往山中,憩感配寺,与山僧饭讫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此时独坐,僮仆静默,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也。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鲦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雊,斯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无忽。因驮黄檗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维白。”永明体代表作家谢朓“既怀欢禄情,复协沧洲趣”(《出新林浦向板桥》)思想,在大历时期获得更多共鸣,到了中唐更发展出姚合这样的“吏隐”典范,他在武功县主簿任上创作了《武功县中作三十首》,第一首第一联即为“县去帝城远,为官与隐齐”,其三云:“微官如马足,只是在泥尘。到处贫随我,终年老趁人。簿书销眼力,杯酒耗心神。早作归休计,深居养此身。簿书多不会,薄俸亦难销。醉卧慵开眼,闲行懒系腰。”其十四云:“作吏荒城里,穷愁欲不胜。病多唯识药,年老渐亲僧。”其二十云:“宦名浑不计,酒熟且开封。晴月销灯色,寒天挫笔锋。”杜甫《送裴二虬作尉永嘉》自述“隐吏逢梅福,看山忆谢公”,《东津送韦讽摄阆州录事》自述“闻说江山好,怜君吏隐兼。……他时如按县,不得慢陶潜”,表明他对“吏隐”的认可。杜甫确实崇尚人格自由⑬,喜欢山水自然,但是,他终生却是儒家虔诚的信徒。
杜甫明确说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晚清著名学者刘熙载就说:“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艺概》卷二)杜甫这种自觉而强烈的儒家思想信仰在盛唐诗人中极其突出。杜甫的政事文表明,他非常熟悉行政事务,这是他关心现实、关注政治人生立场的必然结果。换言之,杜甫的行政能力以及政事文写作本质上来自儒家思想信仰,杜甫是儒家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儒家培养了杜甫的入世精神,培养了杜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杜甫儒学信仰的形成,既有家族传统的作用,他自述出自“奉儒守官”(《进雕赋表》)的家庭,也有地域影响——他自小生活的洛阳就是政治中心,耳闻目染,对他的思想产生巨大影响,更与所处时代有关,杜甫儒家信仰其实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运动、政治思潮的反映。
陈寅恪著作《金明馆丛稿初编》
众所周知,唐玄宗晚年淆乱的政局已引发贾至、元结等一批敏感文人的深刻反思,而安史之乱的爆发,更激起了“尊王攘夷”儒家思想的自觉追怀,这种思潮也是政治思潮,并在中唐形成韩愈、柳宗元所发动的兴儒思想运动和古文运动。陈寅恪早就指出:“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起。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详见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7](P329)邓小军指出:“由韩愈(768—824)所倡导的中唐古文暨儒学复兴运动,包涵两大中心思想。第一,是尊王攘夷,即维护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祖国统一,反对以胡化为本质的藩镇割据。这是政治层面。第二,是复兴儒学,攘斥佛教。这是文化层面。复兴儒学,乃是尊王攘夷及攘斥佛教的根本。儒学复兴运动的宗旨,是要使多难的中华民族以中国文化为自本自根,挺立起来,重新安身立命于天地之间。而早在韩愈之前,杜甫(712—770)就已孤明先发,以诗歌文化为表现形式,首唱尊王攘夷,尤其是首唱复兴儒学。杜甫与杜诗,乃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先行者与先声。”⑭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思想,但是,魏晋南北朝的分裂以及李唐建国,儒家思想始终面对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的竞争,从对士人思想的影响来看,后两者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儒家思想。葛晓音先生研究指出:“盛唐作为一段长达五十年的历史时期,不但在政治上呈现出由开元到天宝逐渐变化的态势,在文人的组合上也存在着阶段性的差异。如果将盛唐文人按年龄分层排辈,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活跃在天宝诗坛上的诗人如李白、高适、元结、杜甫等,谈论诗歌和政治时,多以’复元古’和’念淳古’相标榜;天宝年间开始崭露头角的一些文人如李华、萧颖士、独孤及、贾至、颜真卿等,也都带有较浓厚的复古色彩。学术界一般认为元结、李华、萧颖士、独孤及等人是中唐复古思潮的先驱,因而视之为与盛唐文学的基调不甚合拍的别派。其实,他们只是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天宝文人区别于开元文人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已。也可以说,这种复古色彩是生长于开元、活跃于天宝至大历间的一批文人的共同特征。”[8](P30)所论极为精到,毋庸赘言。
众所周知,杜甫的诗歌具有鲜明的现实性,不仅和其他诗人一样即事抒情,而且,或记录所涉事,或者围绕诗歌所涉事展开议论分析,具有深刻的见识,杜甫代表性的诗歌大多能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体。被后代学者赞誉为杜甫长安十年生活的总结、代表着杜甫最“清醒的现实主义”[9](P145)的长篇五古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生动描写,“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对安史之乱爆发时唐玄宗君臣贪图享乐生活的真实揭露,杜甫在自述“忧端齐终南, 洞不可掇”时安史之乱爆发,时间的巧合生动地证实了杜甫政治预见的深刻、准确!杜甫最杰出的代表作“三吏”“三别”被宋代以来的评论家誉为“诗史”,其继承了汉乐府传统,充分体现了杜甫忧国忧民的儒家仁者情怀。杜甫的一些涉及基层政事的诗歌创作,其实也是杜甫这种儒家仁者情怀的体现。上元二年(761),杜甫在蜀州创作一组独特的诗歌,反映了一个地方官建桥的过程。《陪李七司马皂江上观造竹桥,即日成,往来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题短作,简李公二首》(其一):“伐竹为桥结构同,褰裳不涉往来通。天寒白鹤归华表,日落青龙见水中。顾我老非题柱客,知君才是济川功。合欢却笑千年事,驱石何时到海东。”《观作桥成,月夜舟中有述,还呈李司马》:“把烛桥成夜,回舟客坐时。天高云去尽,江迥月来迟。衰谢多扶病,招邀屡有期。异方乘此兴,乐罢不无悲?”《李司马桥成,高使君自成都回》:“向来江上手纷纷,三日成功事出群。已传童子骑青竹,总拟桥东待使君。”杜甫大费周章地描述建桥过程,并表扬李司马。这类诗艺术性不强,而且有逢迎敷衍格调不高的嫌疑,因此后代评论家对此评价不高,如王士禛就批评《陪李七司马皂江上观造竹桥,即日成,往来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题短作,简李公二首》“诗近俗套”(杨伦《杜诗镜铨》卷八引)。其实,评论者并未注意到杜甫是真诚地感动于地方官爱民的具体作为。创作于宝应元年(762)的《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也是杜甫从村民立场出发,感念严武政绩之作。因此,不能从一般抒情性角度苛求杜甫这类诗歌,更不能将杜甫爱国爱民的情怀庸俗化地误解为吹捧地方官。正因为杜甫不是抽象地爱国爱民,而是从实际出发,真正为国家平叛出谋划策,也为百姓解倒悬之苦,他才创作“三吏”“三别”以及涉及基层政事的诗歌,如宋代周紫芝所说“少陵有句皆忧国”(《乱后并得陶杜二集》)。杜甫诗歌所体现的整体思想倾向是儒家思想,而这种思想也是当时思想发展趋势的反映。
杜甫不仅是诗人,也是散文家;不仅是文学家,也是实干的官员、行动家、实践家。儒学信仰构成了杜甫的政事文写作与其备受后代赞誉的诗歌创作共同的思想基础⑮,也是沟通杜甫文学活动和积极参与处理行政事务共同的思想基础。
三
杜甫“文自古奥”与中唐古文运动
众所周知,“初盛唐诗、文革新”步调并不一致⑯,诗歌革新运动的完成是以“吴中四士”为代表的地方诗人进入京城并产生影响为标志[10](P318),而散文创作则依然沿袭六朝以来的骈文传统,直到中唐韩愈、柳宗元自觉提倡“古文”才逐渐完成。呼唤儒家思想,倡导尊王攘夷,这种文化思潮、政治思潮正是中唐“古文运动”的本质,思想的复古与文字的复古互为表里。对杜甫散文以古为新(包括思想与文风)的创新特色、生成原因以及文学影响,应该从唐代古文运动视角进行审视。
杜甫的散文,从宋代以来评价不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古”——内容实际朴实,文字也不华丽。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五引严有翼《艺苑雌黄》记录苏轼之评论:“曾子固文章妙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杜子美长于歌诗,而无韵者几不可读。”苏轼对杜甫诗歌以及思想评价极高,其“一饭未尝忘君”论影响甚大,却批评杜文。他们从文体以及作家创作偏善的角度解读这种现象,苏轼曾记录秦观的观点云:“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诗冠古今,而无韵者殆不可读;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苏轼题跋》,《苏轼集》附)。南宋学者陈善提出:“文中要自有诗,诗中要自有文”,而“世之议者,遂谓子美无韵语(指杜甫散文),殆不堪读”,恰恰是不懂得“诗文相生法”(《扪虱新话》上集卷一)。尽管宋代学者蔡绦已指出:“杜少陵文自古奥。……或言(杜甫)无韵者不可读,是大不然。”(《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引《西清诗话》),认为杜甫“文自古奥”,但是,并没有说明原因与意义。
实际上,从南朝以来,很多文人不仅不以介入实际社会生活为文学最高境界,反而追求文字的华丽,甚至连公文写作也追求骈俪。杜甫以儒家思想为指南,积极参与实际社会行政事务,并将政事文作为自己写作的重要追求,从散文创作角度看其政事文是以古为新,与流行的骈俪文风分道扬镳。杜甫散文不仅在思想观念上表现出对儒家思想与价值观念的崇奉和坚守(积极参政、仁者情怀等),而且文字表达上也追求复古。批评杜文的学者,没有看到杜文内容与其儒家思想信仰的关联,没有注意到杜甫刻意复古的散文创作追求,而按照抒情文的标准审视杜文,必然导致对杜文评价不高。明代学者张溍揭示了杜甫散文从思想到语言、从遣词用字到文体要素都追求复西汉之古雅、古涩的特点⑰,其评《唐兴县客馆记》曰“以质见姿,似拙似滞,而有古致”,评《东西两川说》曰“文之纡古,似断似续,酷肖西京”(《读书堂杜工部文集注解》卷一)。在张溍看来,杜甫其他诸文具有共同的尚古之气,评《秋述》曰“古拙曲折,似西京以上文”,评《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曰“庄重周悉,虽有骈辞,无伤于体。汉铭多用对句,正复相同”,赞美《祭外祖祖母文》“古茂之章”,赞美《祭远祖当阳君文》“朴而雅”(《读书堂杜工部文集注解》卷二);仇兆鳌也认为《祭远祖当阳君文》“似乎散行无韵,及细玩之,知篇中凡七转韵,盖古韵参错,乍看故未觉耳。苏子瞻祭屈原文,亦系暗藏古韵”(《杜诗详注》卷二十五)。杜甫所写大赋、所撰祭文有古意,更是文学史常识。何焯亦明确指出,杜文“有志于复古”(《义门读书记》)。因此,张溍提出了重要判断“少陵之文,本自过人,反以诗掩!”(《读书堂杜工部文集注解》卷二),确有一定的合理性⑱。仇兆鳌继承此说,评论《唐兴县客馆记》云:“韩文多文从字顺,而作诗务为险奇;杜诗皆熔经铸史,而散文时有艰涩。岂专长者不能兼胜耶?皆当分别观之。”(《杜诗详注》卷二十五)仇兆鳌确实发现杜文复古的特点,却未注意到这出自杜甫对复古的自觉追求,且以作家创作所擅文体不同以解释杜文与诗歌之不同,此说实未达一间。
(清)仇兆鳌编撰《杜诗详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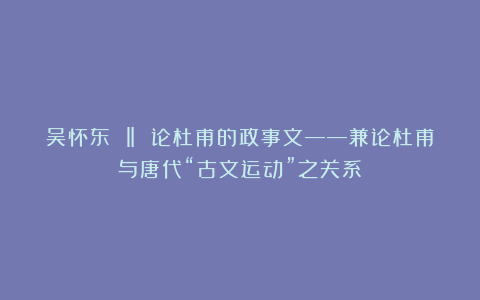
中唐以来,一般学者追溯中唐古文运动“前史”,杜甫并未进入其视野。白居易甚至说“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显然是对自己与元稹创作新变的自我表彰。独孤及的视野则相对开阔:“帝唐以文德旉祐于下,民被王风,俗稍丕变。至则天太后时,陈子昂以雅易郑,学者浸而向方。天宝中,公(指李华)与兰陵萧茂挺、长乐贾幼几勃焉复起,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其弟子梁肃则说:“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已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补阙李君前集序》)他们追述唐“古文运动”前期的发展过程,都强调陈子昂的开拓之功,却不约而同忽略了杜甫的贡献。后来《新唐书》借用梁肃“三变”之说,加以发展,描述唐代古文发展,成为后代主流的文学史常识。刘开扬先生早就指出:“子美、太白与独孤至之均继之(指陈子昂)而起,其后为梁肃与韩、柳,遂使波澜壮阔,为唐文之巨观。今述子美之杂著,乃知确亦古文革新运动之拥护者与躬行者。”[11](P141)熊礼汇先生认为:“从天宝散文复古以求创新的特点,来看杜文的词求古雅、语多简省、造句不避拗折、运思惯于跳跃,其自为其词、决不蹈袭的创新精神。”[12](P23)杜甫散文创作(包括本文讨论的公文——应用性散文)的思想、内容以及艺术特征,都体现了“古文”的特点,遗憾的是,杜甫诗歌在中唐得到了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主流诗人一致的高度评价,一改其生前被忽视的窘境,但杜甫散文的成就与特点却未得到散文学界的充分认知。
四
余 论
杜甫在开元时代培养的理想主义精神,与长安十年的求仕经历以及安史之乱爆发后艰难的生活碰撞⑲,激发了杜甫非凡的创新、创造力,杜甫的思想、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都发生了重大转型。杜甫信仰儒家思想,积极入世,勇于担当,他不仅以一个诗人身份观察现实,抒发感慨(唐代大多数诗人如此),而且以一个官员身份,实实在在为政:忧国忧民不仅是他的信仰,而且落实在日常事务处理实践之中,表现出一定的行政才能。奇怪的是,自从宋代以来,主流的学者们,高度肯定杜甫的诗歌才华,更肯定杜甫“一饭未尝忘君”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价值立场和思想感情,却忽略杜甫对现实政治的积极参与,否认杜甫的行政才能,这未免遗憾。中国古代文学家,从屈原开始,大多是一身二任——既是文学家,也是官员,其中不少是杰出的政治家,即如唐代就有陈子昂、张九龄、高适、李绅、元稹、白居易等,参政的经历激发了他们创作的激情,但参与的行政事务很少成为他们代表性诗文的内容,而杜甫却不仅关心政治,还具备实际行政才能——杜甫的儒家信仰、道德风范与政治见识、行政能力较好地统一,并且,用诗、文创作记录自己参与或关心的政治、行政事务以及思考,这样的作家在古代其实并不多见⑳。
总之,杜甫的政事文,既来自他独特的实际参政经验,也源自他的儒学信仰——和他的“诗史”同声相应,并表现出反映现实、关注政治、自觉革除骈俪、以古为新的倾向或特点,与天宝时期兴起的文儒思想运动和古文思潮同声共振,因此,今天追溯、研究唐代“古文运动”“前史”,当然不应再继续忽略杜甫的创造及其贡献。
注释
①与“政事文”有一定关联的概念是政论文。按照流行的理解,政论文是“从政治角度阐述和评论当前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议论文”,阐述的对象是“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主要讨论其政治问题,这和本文所谓“政事文”不同。
②《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阁画太一天尊图文》甚至具有一定的“小说”性质,参见拙文《杜甫与“小说”——〈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阁画太一天尊图文〉文体性质考论》,《杜甫研究学刊》2022 年第 1 期,第 17—34 页。
③其实,杜甫的赋与国家典礼有关,也属于实用文体,带有公文性质。
④仇兆鳌就感慨说:“杜文传世无几,旧刻既少疏笺,又多舛字,令读者不能终篇。”(《杜诗详注》卷二十五,中华书局 1999年版,第 2234 页)这一方面表明杜文之古雅甚至艰涩,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古今学者并未着力解读杜文。关于杜甫这些散文的创作时间和具体过程,学者们并无统一意见,本文主要参考萧涤非主编、张忠纲终审统稿《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的观点。
⑤房琯案的过程、政治背景与以及杜甫“疏救房琯”的是非曲直,清代学者钱谦益论之最详,当今史学界已有深入研究,此处不赘。
⑥在短暂的担任左拾遗时期,面对安史之乱造成的巨大社会危机,杜甫提出了不少具体的合理建议,如提到平叛的策略,诗云:“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望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北征》)仇注引朱鹤龄注云:“当时李泌之议,欲令建宁并塞北出,与光弼犄角,以取范阳,所见正与公同。”(《杜诗详注》卷五)杜甫提出的战略构想与李泌的思路相同(详参吴相洲《略说杜甫的“小臣议论”》,《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4 期,第 82—86 页)。杜甫后来在《壮游》诗中说“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还遗憾地追忆自己身为谏官积极履职,提建议、出谋略的这段经历。杜甫任左拾遗时身在朝廷掌握当时的政治军事信息较多,对平叛的军事问题思考较多且十分深入,所以,在华州司功参军任上提出的方案沿袭他之前的思考,仍然强调各路唐军互为犄角、动态合围的战略战术。
⑦此文写作时间是采信林继中《杜文系年》之论定,其文载《漳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3 期,第 50—53 页。
⑧参见王伟《宗王出镇:安史乱后杜甫平叛思想的文化意义——以〈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为中心》(《中国文学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40—48 页)之详论。
⑨参见拙文《论杜甫参政实践及其文学影响》,《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24 年第 1 期,第 74—81 页。
⑩关于杜甫对百姓的态度,参见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代前言”第二部分之详细论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10 页)。
⑪《再说杜甫》,收入洪业著、曾祥波译《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附录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66 页)。按,杜甫的诗歌看起来都是抒情,其实包含他的现实关怀和政治判断,他晚年在夔州的《释闷》诗云:“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陈寅恪曾结合杜甫陷贼时创作的《哀江头》诗句解释论曰:“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其被困长安时所作之诗,如《哀江头》《哀王孙》诸篇,古今称其文词之美,忠义之忱,或取与王右丞’凝碧池头’之句连类为说。殊不知摩诘艺术禅学,固有过于少陵之处,然少陵推理之明,料事之确,则远非右丞所能几及。由此言之,古今治杜诗者虽众,而于少陵之为人,似犹知之未尽。”(《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64 页)陈寅恪所论为杜诗,其实杜文更直接表现了杜甫的政治参与意识与政治见识。
⑫ 参见汪篯《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二》,收入《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⑬ 参见拙文《陶杜异同论》,《文学评论丛刊》2002 年第 1 辑。
⑭ 见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2 页。陈弱水《思想史中的杜甫》(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九本第一分册,1998 年)对杜甫与儒家思想的关联,有更详细的辨析。
⑮ 按,许总《杜甫以诗为文论》(收入其《杜诗学引论》,南京出版社 1989 年版)认为杜甫文受到诗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形象性、抒情性、“刻意锻炼的语言”诸方面。本文认为,杜诗、杜文的相通,主要的不在这些技术层面,而是内在精神的相通,即共同体现着儒家的入世精神和复古的政治、文学思想。
⑯ 傅璇琮总主编、蒋寅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第 402 页下注本人拙见,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⑰ 参见拙文《杜甫〈杂述〉〈秋述〉文体形态及其源流考论》(《中国文学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48—57 页)、《杜甫〈天狗赋〉“献赋”性质考论》(《文学遗产》2023 年第 6 期,第 24—36 页)。
⑱ 每个作家都非全才,对不同文体各有所擅。宋代以来,学者对此讨论甚多,详论可参见张巍《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跨文体成就比较》(《光明日报》2022 年 7 月 25 日)。孙微还提出,杜甫生前赋名超过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力(《名岂文章著:论杜甫生前诗名为赋名所掩》,《文史哲》2017 年第 2 期,第 45—54 页)。当然,还存在不同文体互相影响现象,晚唐司空图就认为杜甫《祭太尉房公文》、李白《佛寺碑赞》“宏拔清厉,乃其歌诗也;张曲江五言沉郁,亦其文笔也”(《题柳柳州集后》),唐代文体间的相互借鉴、学习是实现文学革新、发展的重要条件,详论参见余恕诚、吴怀东《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中华书局 2012 年版)。
⑲ 拙文《论李杜交谊及其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2 期,第 146—160 页)从李、杜交往的角度讨论了盛唐精神对杜甫的孕育作用。
⑳ 关于杜甫的官员角色心态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学创作特色,本人另有文详论,在此不赘。
参考文献
[1]兰翠 . 论唐代政事诗及诗人群体性格[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2]马林刚 . 儒家诗教传统下的政事诗[J]. 求索,2013(3).
[3]闻一多 . 唐诗杂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萧涤非主编,张忠纲终审统稿 . 杜甫全集校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5]冯至 . 人间要好诗[M]//杜甫传附录一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6]小川环树“. 吾道长悠悠”:杜甫的自觉[M]//风与云:中国诗文论集 . 周先民,译 . 北京:中华书局,2005.
[7]陈寅恪 . 论韩愈[M]//金明馆丛稿初编 . 北京:三联书店,2001.
[8]葛晓音 . 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J]. 文学遗产,1998(6).
[9]程千帆 . 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读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J]. 中国社会科学,1984(5).
[10]宇文所安 . 初唐诗[M]. 贾晋华,译 . 北京:三联书店,2004.
[11]刘开扬 . 柿叶楼存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2]熊礼汇 . 杜甫散文创作倾向论:兼论杜甫以诗为文说[J]. 杜甫研究学刊,2002(2).
作者简介
Intrdcution
吴怀东,文学博士,现为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三曹”与魏晋文学、杜甫与唐代文学以及清代散文,出版过《诗史运动与作家创造——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杜甫与唐代文学研究论稿》等著作,发表过《杜甫〈杂述》〈秋述》文体形态及其源流考论》《“文取指达”说的千古误解及其思想背景》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