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人类,致病菌始终威胁人类的健康,人类也一直在和致病菌做着斗争。磺胺类药物发明于上世纪30年代,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发现的合成抗菌药,用于临床已近90年之久。
01
—
染料化学里的意外之光:磺胺的诞生前夜
磺胺类药物的故事,并非始于实验室里的刻意追寻,而是源于 19 世纪一场关于合成染料的化学革命。1856 年,英国一位 18 岁的化学家威廉・珀金,正为合成治疗疟疾的关键药物奎宁而努力。彼时的奎宁依赖从南美金鸡纳树树皮中提取,产量稀少且价格昂贵,珀金希望通过化学合成的方式突破这一限制。然而,实验并未按预期进行,他意外得到了一种紫色粉末 —— 这种粉末溶于酒精后,能染出鲜艳的紫色,这便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合成染料 “苯胺紫”。
苯胺紫的出现,不仅让珀金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合成染料工厂,更开启了合成染料的黄金时代。而谁也没想到,几十年后,这种用于染色的化学物质,会与 “治病救人” 产生深刻联结。1882 年,德国病原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在研究结核病时,发现苯胺类染料能与细菌的核酸结合,让原本透明的细菌在显微镜下清晰可见 —— 这就是著名的 “细菌染色法”。在反复实验中,科赫又偶然观察到一个奇特现象:某些苯胺染料不仅能给细菌 “上色”,还能抑制细菌的生长。这一发现像一束微弱却关键的光,照亮了 “染料或许能成为药物” 的全新路径,也为后来磺胺类药物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而将这束光转化为 “救命火种” 的,是德国科学家格哈德・多马克。1895 年,多马克出生在德国勃兰登一个贫困的小镇,父亲是当地的小学教师,母亲则操持家务补贴家用。由于家境清贫,家里根本无力承担孩子的学费,多马克直到 14 岁才踏入小学课堂 —— 比同龄孩子晚了整整 8 年。但贫穷并未磨灭他对知识的渴望,相反,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刻苦。白天在课堂上认真听讲,晚上就借着微弱的灯光自学,最终以远超常人的努力考入了德国著名的基尔大学医学院。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刚进入医学院不久的多马克被迫中断学业,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军医。在战地医院里,他目睹了太多令人心碎的场景:士兵们在战场上被子弹、炮弹击伤后,医生们虽能成功完成手术,取出弹片、缝合伤口,但几天后,伤口却会开始红肿、化脓,细菌感染引发的败血症迅速席卷全身,患者往往在痛苦中死去。有一次,多马克接诊了一名腿部中弹的年轻士兵,手术非常成功,士兵还笑着和他约定 “战争结束后一起回家”,可仅仅 3 天,败血症就夺走了这个年轻的生命。看着士兵逐渐冰冷的身体,多马克在日记本上写下:“我们能修复伤口,却挡不住看不见的细菌。必须找到一种能在人体内杀死它们的药物。”
格哈德·多马克(Gerhard Johannes Paul Domagk,1895年10月30日-1964年4月24日),德国生物化学家、病理学家与细菌学家。
战争结束后,多马克重返基尔大学医学院,带着战地的遗憾与决心继续深造。凭借扎实的医学基础和对细菌感染的深入思考,他顺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27 年,国际制药巨头拜耳公司向他伸出橄榄枝,邀请他出任公司病理学和细菌学实验室主任 —— 拜耳公司当时已因研发出阿司匹林而享誉全球,拥有顶尖的实验设备和研发资源,这为多马克的研究提供了绝佳的平台。
当时,科学界研究药物抗菌性的方法还十分粗放:大多数研究者只是将药物加入试管或培养基中,观察是否能抑制细菌生长,若结果为 “阴性”(无抑菌效果),就会直接放弃该药物。但多马克深知,体外实验与体内环境有着天壤之别 —— 试管里无效的药物,在活体内或许能发挥作用。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思路:将染料合成与动物实验结合,用从患者身上分离出的真实致病菌,在小白鼠身上建立疾病模型,再测试药物的体内抗菌效果。
从 1927 年到 1932 年,整整 5 年时间里,多马克带领团队日复一日地泡在实验室里。他们合成了一种又一种偶氮化合物(一类含偶氮基的染料),前后共合成了 1000 多种;每合成一种,就先进行体外实验,再给感染致病菌的小白鼠注射。无数个夜晚,实验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多马克的白大褂上沾满了染料的痕迹,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实验数据 —— 但大多数结果都是 “体外阴性,体内无效”。有一次,团队连续测试了 30 多种化合物,都没有任何突破,年轻的助手忍不住抱怨:“也许我们的思路根本就是错的。” 多马克却只是拿起下一瓶染料,平静地说:“再试一次,万一成功了呢?”
1932 年圣诞节前的一个夜晚,实验室里只剩下多马克一人。他拿起一瓶刚合成好的红色染料,标签上写着 “4-(2,4 – 二氨基苯基) 偶氮苯磺酰胺”,团队给它起了个商品名 “百浪多息”。按照惯例,他先将染料加入装有链球菌的培养基中,静置一段时间后观察 —— 培养基里的细菌依旧活跃,体外实验结果还是 “阴性”。疲惫的多马克揉了揉眼睛,想起了战地里那些因感染死去的士兵,又想起了家里等待他回家过节的家人。他本可以像往常一样,将这瓶染料归入 “无效” 类别,但心底的执念让他停住了手。
“再给小白鼠试一次吧。” 多马克自言自语道。他从培养箱里取出几只感染了链球菌的小白鼠 —— 这些小白鼠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感染症状,精神萎靡、毛发杂乱,有的甚至已经无法站立。他小心地给每只小白鼠注射了百浪多息,然后将它们放回笼子,默默等待。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在实验室里守着笼子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实验室时,多马克惊喜地发现:原本奄奄一息的小白鼠,竟然开始活动了!它们不仅能站起来,还主动去舔食笼子里的食物。他赶紧对小白鼠进行检测,发现其体内的链球菌数量大幅减少 —— 百浪多息在小白鼠体内发挥了抗菌作用!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合成抗菌药,就这样在一个寒冷的圣诞前夜,在 “不放弃” 的坚持中诞生了。
02
—
从女儿的病床到总统之子:百浪多息的 “破圈” 之路
百浪多息在小白鼠身上的成功,让多马克看到了希望,但他深知,动物实验的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人体疗效,还需要进一步验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于是,他带领团队开始研究百浪多息的毒性:给小白鼠、兔子等不同动物注射不同剂量的药物,观察它们是否出现呕吐、抽搐、器官损伤等不良反应。经过数月的实验,结果显示:百浪多息对实验动物的毒性极低,即使是较高剂量,也不会对器官造成明显伤害。这让多马克更加坚定了将其用于人体治疗的想法,但他还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 直到 1933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降临到他的家庭。
那年春天,多马克 6 岁的女儿玛丽在院子里玩耍时,不小心被玫瑰花的刺刺破了手指。起初,一家人都没太在意,只是用清水冲洗了一下伤口。可没过两天,玛丽的手指开始红肿、疼痛,体温也迅速升高到 39.5℃,脸颊烧得通红,还伴有寒战、呕吐等症状。多马克赶紧给女儿做了检查,在显微镜下,他清晰地看到了玛丽伤口渗出液和血液中的链球菌 —— 和他在实验室里研究的致病菌一模一样,而且感染已经扩散,随时可能发展成败血症。
多马克立刻请来了慕尼黑最有名的几位儿科医生和感染科医生。医生们会诊后,一致认为玛丽的病情非常危急,只能通过注射抗生素(当时仅有少量天然抗生素,且效果有限)来治疗,但尝试后,玛丽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陷入了昏迷。看着女儿躺在床上毫无生气,呼吸微弱,多马克的妻子忍不住哭着问:“难道我们真的只能看着她离开吗?” 多马克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但他突然想起了实验室里的百浪多息 —— 那是唯一能杀灭链球菌的药物。
可这个想法刚冒出来,就被他自己压了下去:百浪多息从未在人体上进行过实验,谁也不知道它对人体是否有效,会不会有致命的副作用?如果用在女儿身上,万一出了意外,他该如何面对?但看着女儿逐渐微弱的呼吸,多马克知道,他没有时间犹豫了。“我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个父亲。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死去。” 当晚,他从实验室里取来百浪多息,在自己的手臂上先注射了少量药物,观察了半小时,确认没有出现过敏反应后,才小心翼翼地给玛丽注射了适合儿童剂量的百浪多息。
注射后,多马克和妻子守在女儿床边,一秒钟也不敢离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凌晨时分,玛丽的体温开始缓慢下降,从 39.5℃降到了 38℃;天亮时,她的呼吸变得平稳,还轻轻哼了一声;上午 10 点左右,玛丽缓缓睁开了眼睛,虚弱地说:“爸爸,我饿了。” 那一刻,多马克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 他用自己研发的药物,救了女儿的命!
多马克用百浪多息挽救女儿生命的消息,很快在德国医药界传开。拜耳公司抓住机会,加快了百浪多息的临床实验进度。在随后的临床试验中,百浪多息对链球菌、葡萄球菌等引起的感染都展现出了出色的疗效:原本因产后感染(产褥热)濒临死亡的产妇,注射后几天就能康复;因皮肤感染引发败血症的患者,用药后体温迅速恢复正常。1933 年底,百浪多息正式在德国上市,一经推出就被抢购一空,医生们将其称为 “红色救命药”。
真正让百浪多息享誉全球的,是 1935 年的 “罗斯福之子救治事件”。当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儿子小 F.D. 罗斯福在一次运动中不慎受伤,伤口感染引发了严重的败血症,高烧不退,美国最好的医生们用尽了各种方法,都无法控制感染,小 F.D. 罗斯福的生命垂危。就在全家陷入绝望时,有医生想起了德国刚上市的百浪多息,建议尝试使用。罗斯福总统虽然对这种 “染料药物” 心存疑虑,但为了救儿子,还是同意了。
当百浪多息从德国紧急运到美国医院,注射到小 F.D. 罗斯福体内后,奇迹再次发生:24 小时内,他的体温明显下降;48 小时后,败血症症状得到控制;一周后,他就能下床活动了。这一事件被美国各大媒体头版报道,《纽约时报》更是用 “红色染料拯救了总统之子” 为题,详细介绍了百浪多息的疗效。一时间,百浪多息成为了全球瞩目的 “神药”,各国纷纷向拜耳公司订购,甚至有国家专门派船前往德国,只为尽快运回这种救命药。
0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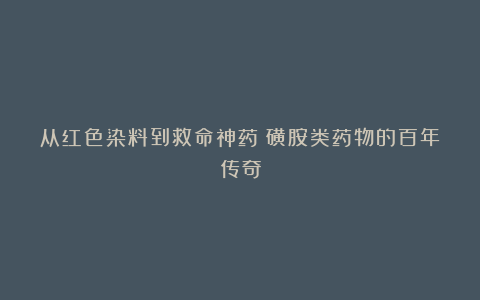
科学揭秘:为什么红色染料能治病?
百浪多息的神奇疗效,让全球科学家都为之着迷:一种红色染料,为什么能在人体内杀死细菌?起初,科学家们普遍认为,是百浪多息分子中的 “偶氮基”(一种含氮的化学基团,也是染料的生色基团,让百浪多息呈现红色)发挥了抗菌作用。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了矛盾:很多不含磺胺基团、只含偶氮基的染料,并没有抗菌效果;而含有磺胺基团的偶氮染料,无论颜色如何,都有一定的抗菌活性。
这个疑问,直到 1936 年才被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解开。当时,巴斯德研究所时任所长是达尼埃尔・博韦(后来因抗组胺药和箭毒的研究获得 1957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带领团队对百浪多息进行了深入的代谢研究。他们将百浪多息注射到动物体内,然后分析动物的血液和尿液,结果在尿液中发现了一种名为 “对氨基苯磺酰胺” 的化合物 —— 这种化合物正是百浪多息在体内分解后的产物。
(对氨基苯磺酰胺)
为了验证对氨基苯磺酰胺的作用,科学家们将其直接加入装有细菌的培养基中,惊喜地发现:它能显著抑制细菌生长,体外实验结果为 “阳性”!而更关键的是,他们在服用百浪多息的患者尿液中,也分离出了对氨基苯磺酰胺的衍生物(对乙酰氨基苯磺酰胺)—— 这说明,百浪多息在人体内会被代谢分解,释放出对氨基苯磺酰胺,真正发挥抗菌作用的,其实是这种分解产物。
这一发现,让科学家们提出了 “前药” 的概念 —— 所谓前药,是指药物经过化学结构修饰后,在体外无活性或活性很小,但进入体内后,能通过酶或非酶的转化,释放出具有活性的药物成分,从而发挥药效。百浪多息就是一种典型的前药:在体外(试管、培养基)中,它无法分解出对氨基苯磺酰胺,所以没有抗菌活性;但进入人体后,体内的代谢酶会 “剪断” 它的分子结构,释放出对氨基苯磺酰胺,进而杀死细菌。这也终于解释了为什么多马克的体外实验总是 “阴性”,但体内实验却能成功 —— 他差点因为 “体外无效” 而错过这款救命药。
更令人意外的是,对氨基苯磺酰胺并非什么 “新物质”。早在 1908 年,这种化合物就被化学家发现了,在随后的 20 多年里,它一直被当作合成染料的原料,没人想到它还能治病。直到多马克的开创性研究,才让这种 “染料原料” 摇身一变,成为了抗菌 “神药”。
那么,对氨基苯磺酰胺是如何杀死细菌的呢?这背后藏着一个 “精准竞争” 的科学原理。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细菌和人体不同:人体可以从食物中直接摄取叶酸(一种 B 族维生素,对细胞生长和分裂至关重要),而细菌无法直接摄取外界的叶酸,必须依靠自身合成 —— 它们会利用环境中的 “对氨苯甲酸(PABA)”、“二氢喋啶” 和 “谷氨酸”,在体内一种名为 “二氢叶酸合成酶” 的催化下,合成 “二氢叶酸”;二氢叶酸再转化为 “四氢叶酸”,而四氢叶酸是细菌合成核酸(DNA 和 RNA)的关键原料,没有核酸,细菌就无法生长、繁殖,最终会死亡。
而对氨基苯磺酰胺的化学结构,与对氨苯甲酸(PABA)非常相似 —— 就像两把 “长得几乎一样的钥匙”。当对氨基苯磺酰胺进入细菌体内后,会 “冒充” 对氨苯甲酸,与细菌的 “二氢叶酸合成酶” 结合。但这种 “冒充的钥匙” 无法催化合成二氢叶酸,反而会占据酶的活性位点,让真正的对氨苯甲酸无法与酶结合 —— 这就像堵住了细菌合成叶酸的 “通道”,细菌无法合成叶酸,也就无法合成核酸,最终只能 “饿死”。
更精妙的是,这种 “竞争” 只针对细菌,对人体没有影响。因为人体不需要自己合成叶酸,只需从食物(如绿叶蔬菜、动物肝脏、豆类等)中摄取,所以对氨基苯磺酰胺不会干扰人体的叶酸代谢,也就不会产生明显的毒副作用。这种 “只杀细菌、不伤人体” 的特性,让磺胺类药物成为了安全有效的抗菌药,也为后来的 “靶向药物” 研发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04
—
从抗菌到多领域:磺胺家族的 “进化史”
百浪多息的成功,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全球医药界掀起了磺胺类药物研发的热潮。科学家们意识到,通过改造对氨基苯磺酰胺的化学结构,或许能开发出抗菌谱更广(能杀死更多种类的细菌)、疗效更强、毒性更低的磺胺类药物。
从 1935 年到 1945 年,短短 10 年间,欧美各国的科学家们合成了数以千计的磺胺化合物(据 1945 年统计,总量超过 5000 种)。他们通过 “构效关系研究”(分析化学结构与药效之间的关系),不断优化分子结构:有的在磺胺基团上增加特定的化学基团,扩大抗菌谱,让药物能对抗革兰氏阴性菌(如大肠杆菌、痢疾杆菌);有的则通过结构改造,降低药物在尿液中的溶解度,减少结晶析出(早期磺胺药容易在尿液中形成结晶,导致肾结石);还有的通过改变分子的代谢速度,延长药物在体内的作用时间。
在这 5000 多种化合物中,科学家们筛选出了 30 多种疗效好、毒性低的磺胺药,其中不乏影响深远的 “明星药物”:
- 磺胺甲氧嗪(3 – 磺胺 – 6 – 甲氧哒嗪)
- 磺胺甲恶唑(新诺明,SMZ)
- 周效磺胺(2 – 磺胺 – 5,6 – 二甲氧嘧啶)
1960 年代,磺胺类药物的发展迎来了又一个 “里程碑”—— 抗菌增效剂甲氧苄氨嘧啶(TMP)的发现。科学家们在研究中发现,TMP 能抑制细菌体内的 “二氢叶酸还原酶”—— 这种酶是二氢叶酸转化为四氢叶酸的关键。也就是说,磺胺类药物堵住了细菌合成二氢叶酸的 “通道”,而 TMP 则堵住了二氢叶酸转化为四氢叶酸的 “下一步通道”,两者联合使用,能从 “两步” 抑制细菌的叶酸合成,让抗菌效果提升数倍至数十倍,还能扩大抗菌范围,甚至对一些原本对磺胺药耐药的细菌也有效。这种 “协同作用” 让磺胺类药物的医疗地位大幅提升,至今仍是治疗某些感染(如泌尿系统感染、呼吸道感染)的常用方案。
虽然在青霉素、头孢菌素等天然抗生素问世后,磺胺类药物的临床应用有所减少,但它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即使到了今天,在国家药监局网站上以 “磺胺” 为关键词检索,仍能找到 1848 条结果,涵盖片剂、胶囊剂、注射剂、软膏剂、滴眼液等多种剂型,用于治疗泌尿系统感染、皮肤感染、眼部感染等多种疾病。比如,磺胺嘧啶软膏常用于治疗轻度烧伤、烫伤引起的感染;磺胺醋酰钠滴眼液则是治疗细菌性结膜炎的常用药物。
更令人惊喜的是,科学家们在磺胺类药物的临床应用中,还发现了它的 “意外价值”:部分磺胺药具有抑制 “碳酸酐酶” 的作用(碳酸酐酶是一种参与体内酸碱平衡和水代谢的酶),还有的磺胺药在服用后,会出现 “降血糖” 的副作用。这些 “意外发现” 并没有被忽视,反而成为了新的研发方向。
科学家们基于这些特性,开始有针对性地合成和筛选化合物:
- 磺胺类利尿药
- 磺胺类口服降糖药
从抗菌到利尿,再到降糖,磺胺家族不断拓展着自己的 “版图”,在更广泛的领域为人类健康服务。
05
—
历史回响:迟到的诺贝尔奖与不朽的遗产
1939 年 10 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审委员会宣布,将该年度奖项授予格哈德・多马克,以表彰他 “发现磺胺类药物的抗菌作用,开创合成抗菌药时代” 的贡献。这是对多马克多年研究的最高认可,也是对磺胺类药物历史地位的肯定。
然而,多马克的领奖之路却充满了坎坷。当时,纳粹德国正处于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之下,而诺贝尔和平奖在 1935 年授予了德国反法西斯和平主义者卡尔・冯・奥西茨基(当时奥西茨基被关押在集中营里),这让希特勒对诺贝尔授奖委员会极为恼火。为了报复,希特勒下令禁止所有德国人接受诺贝尔奖,并以 “德国国家艺术与科学奖” 取而代之。
当多马克收到诺贝尔奖获奖通知,准备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奖时,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 “盖世太保” 找上门来,将他软禁在家中。盖世太保警告他,如果敢接受诺贝尔奖,就会被视为 “背叛德国”,不仅他本人会受到惩罚,家人也会受到牵连。在盖世太保的威胁下,多马克不得不于 1939 年 11 月发表声明,被迫拒绝接受诺贝尔奖。
直到 1945 年二战结束,纳粹德国覆灭后,多马克才终于摆脱了软禁。1947 年,诺贝尔基金会重新向多马克发出邀请,他才得以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迟到了 8 年的颁奖仪式。按照诺贝尔基金会的规定,诺贝尔奖的奖金部分只能为获奖者保留一年,超过一年未领取则充入诺贝尔基金,因此多马克虽然获得了诺贝尔奖奖章和证书,却没有拿到奖金。但对他而言,这份迟到的荣誉,早已超越了金钱的意义 —— 它是对他坚持科学、拯救生命的最高认可。
如今,近 90 年过去了,磺胺类药物依然活跃在临床一线,而它留下的遗产,早已超越了药物本身:
- 开创合成抗菌药时代
- 建立新的药物研发范式
- 推动药品监管发展
- 对抗耐药菌的启示
从 1932 年圣诞前夜实验室里的那瓶红色染料,到如今医院药房里的各种磺胺制剂;从多马克救女的 “父爱赌局”,到拯救亿万患者的 “救命神药”;从单一的抗菌领域,到利尿、降糖的多赛道拓展,磺胺类药物的传奇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