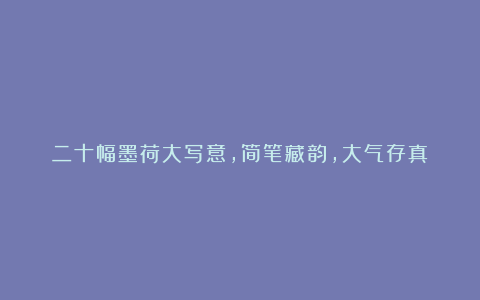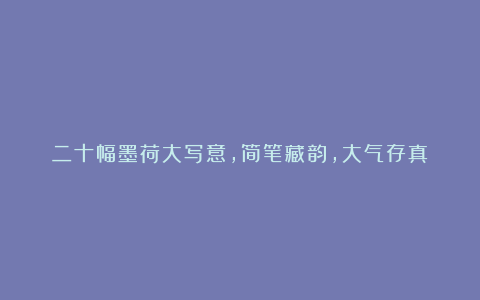|
大写意墨荷的魅力,从不在对物象的精细复刻,而在以笔墨为骨、以气韵为魂的艺术表达。它用最凝练的笔墨语言,将荷花的清绝风骨与自然的磅礴生机熔于尺幅之间,在“简约”中藏大气,在“泼辣”中见性情,让墨色的淋漓与笔触的潇洒,成为超越具象的精神载体——这既是传统文人画“以形写神”的极致延续,也是笔墨自身生命力的酣畅绽放。
从笔墨本体来看,大写意墨荷的“简约”绝非简单的笔墨删减,而是对物象本质的精准提炼。它摒弃工笔重彩对花瓣纹理、叶脉走向的细致描摹,转而以“一笔定形”的魄力构建荷的形态:画荷叶常用“破墨法”,笔锋饱蘸浓墨后略蘸清水,侧锋横扫间,墨色自然晕化出深浅层次,浓处为叶心聚墨,淡处为叶缘散气,寥寥数笔便将荷叶“承露若张伞”的形态与质感托出;写荷茎则用“中锋立骨”,笔锋垂直于纸,提按转折间墨色由浓转淡,似荷茎从淤泥中拔起,上段轻劲、下段沉实,无需多余皴擦,便见“中通外直”的挺拔风骨。这种“删繁就简”的笔墨逻辑,实则是对“形”的减法、对“神”的加法——减去的是无关紧要的细节,留下的是荷的气韵与画者的心境,最终以极简的笔墨,撑起画面的大气格局。
而“泼辣”的画风,是大写意墨荷笔墨张力的核心表达,它体现在笔触的“放”与“纵”上。画者作墨荷时,多以“写意笔法”为基,少用迟疑的描、绘,多用果断的扫、点、劈:画盛开的荷花,常以“点垛法”快速落墨,笔尖蘸浓墨点出花瓣轮廓,笔腹淡墨晕染花瓣层次,墨色未干时稍作勾提,便见花瓣的舒展与灵动;画风雨中的荷叶,更显笔力——笔锋饱蘸墨汁,以“积墨法”层层叠加,重按处墨色堆积如叶心聚雨,轻扫处飞白散落如叶缘翻卷,甚至允许墨汁在宣纸上自然流淌,形成“墨晕成趣”的偶然效果。这种“不管不顾”的笔触,看似肆意,实则藏着对笔墨节奏的精准把控:重笔处见骨力,轻笔处见仙气,疾笔处见动感,缓笔处见静谧,在“放”与“收”的平衡间,让荷塘风雨、四季更迭的意境跃然纸上,酣畅得让人心生畅快。
墨色的“淋漓潇洒”,则是大写意墨荷最具感染力的笔墨语言。它打破“墨分五色”的刻板认知,以墨色的干湿、浓淡、枯润构建丰富的视觉层次与情感表达:画盛夏之荷,多以“湿墨”为主,墨色饱满欲滴,荷叶用淡墨铺底、浓墨点苔,荷茎以湿墨勾写,墨色在宣纸上晕化开来,似满塘水汽蒸腾,鲜活得能闻见荷香;画残秋之荷,则以“枯墨”见长,笔锋干涩带飞白,荷叶边缘用枯笔皴擦,荷茎以枯墨勾勒,墨色干涩中藏着韧性,似秋风中的残荷虽败犹立,萧瑟中自有风骨。更妙的是“破墨”与“宿墨”的运用:破墨时,浓墨与淡墨在湿纸上交融,形成自然的墨色过渡,似荷叶被光影笼罩的明暗变化;宿墨则墨色沉郁,用它点画荷心或莲蓬,能让画面在明快的墨色中多一份厚重,避免流于轻飘。这种墨色的运用,从不追求“形似”的真实,而是追求“意似”的共鸣——墨色浓时,是荷的风骨;墨色淡时,是荷的仙气;墨色干时,是荷的坚韧;墨色湿时,是荷的灵动,一笔墨便能承载万千意趣,潇洒得让人心生向往。
说到底,大写意墨荷的笔墨语言,是画者“心手相应”的产物。它要求画者不仅懂笔墨技巧,更要懂荷的性情、懂自然的规律——只有见过清晨荷塘的薄雾,才能画出淡墨荷叶的朦胧;只有见过暴雨中的荷茎,才能写出中锋用笔的倔强;只有心怀对自然的敬畏与对自由的向往,才能让笔墨生出“大气”“泼辣”“潇洒”的气质。它不追求让观者“看清”一朵荷,而追求让观者“读懂”一份心境:在简约的笔墨里,读懂“大道至简”的哲学;在泼辣的画风里,读懂“不为世俗所困”的性情;在淋漓的墨色里,读懂“顺应自然”的智慧。
这便是大写意墨荷的魅力:它以笔墨为桥,让荷的风骨、画者的心境与观者的情感相通,在一方宣纸上,写出最酣畅的生命赞歌,也写出最潇洒的人生态度。
画家/周墉,字筠溪、老溪,九仙山人。新华书画院特聘画家,独立艺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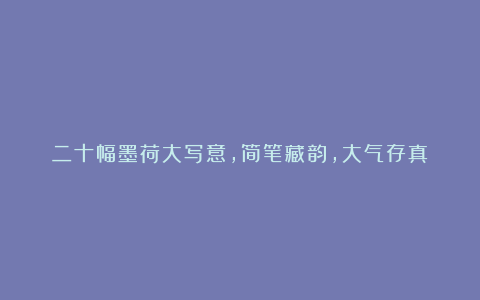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