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触了不少工艺美术和非遗的实物,在传承三百年的苏州“老万年”古法金工坊里,我被一种“极致”深深触动。那种历经岁月,却因极致技艺而愈发璀璨的质感,让我联想到玉雕圈里那个永不过时的争论: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是令人屏息的“极致炫技”,还是直抵人心的“相玉写意”?
回望:玉史长河中的三个高峰
当下玉雕,到底是技重要,还是意重要?说实话,我时常陷入这种两难。
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如果看不清眼前,不妨跳出当下,把时间的轴线拉长。拉到百年、千年之外,再回头审视,此刻的许多迷雾便会消散,历史的脉络也将清晰浮现。
回望中国玉文化的万年长卷,其间公认耸立着三座高峰:战汉、清乾隆,以及我们正在经历的当下。每一座高峰,都烙印着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精神气象。
战汉之玉,以意通天。那时的玉,如玉琮、玉璧,形制古拙,质地浑厚。以今天的眼光看,其工艺或许简朴,甚至“拙”,因为靠的是金刚砂慢慢磨。但其核心价值,在于“礼天地、通神明”,承载的是先民磅礴的宇宙观与虔敬的精神力量。这无疑是“意”的巅峰。
乾隆之工,以技炫世。到了清代乾隆时期,国力臻于极盛,玉雕工艺也随之登峰造极。无论是体量恢弘的“玉山子”,如《大禹治水图》玉山,还是精微仿古的彝器,无不极尽繁复、精巧与严整。这个时代,将人的匠心与帝国的审美意志张扬到了极致,堪称一场“技”的盛大炫示。
当下之惑:谁能跨越时间?我们这个被称为“第三次高峰”的时代,技艺与写意并存,纷呈异彩。那么,试想两百年后,人们会记住什么?是那些精雕细琢、巧夺天工的“炫技”之作,还是那些寥寥数刀、神韵自现的“写意”小品?
我曾将两件玉器并置:一件是极致复杂的青铜化玉器皿,另一件是抽象写意的玉雕老虎。请诸多玉友评判,哪件更可能传世。多数人的选择,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前者。这个朴素的结果,促使我展开更深一层的思考。
权衡:“技”的确定与“意”的弹性
在我看来,“极致炫技”的作品,有一个根本的优势:价值非常确定。
一件玉雕,无论器皿、摆件或人物,只要其工艺达到了某种公认的极致高度——例如悬空雕、薄胎、或复杂的青铜纹饰移植——那么它的价值便坚实地立于那里。作者是谁固然有影响,但更根本的是“做得出来”这个事实。大师可为,一位有绝活的年轻匠人若能达成,同样堪称杰作。
它的美,是肉眼可见、标准相对统一的,就像永乐压手杯、宣德炉,我们赞叹其美,往往不会深究作者是谁。这种确定性,让它在历史长河中更容易被识别、被保存。
而“相玉写意”则完全不同。它源于对一块原材料独到的“相”(观察与感悟),从中读出具象或意象,再以简练刀法“点化”其神,追求神似而非形似。这类作品的价值,充满了弹性,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冒险”。
它高度,几乎完全依赖于创作者自身的认知边界、文化修养和思想深度。同样一块料,樊军民老师做出来,大家叫好;换个无名匠人依样处理,可能就被质疑。这里头掺杂了太多对“人”的判断:作者的声望、品行、甚至他背后的故事,都会影响作品的估值。就像文人画,作者数不胜数,但能被记住的不过寥寥数人。
于是,便形成了玉雕收藏中一个有趣的“扁担两头沉”现象:两头都重,皆价值不菲但一头的价值如磐石般稳固,另一头却可能随风浪起伏。炫技之作,是硬实力的彰显,是工艺时代的物证;写意之作,则是软实力的较量,是个人心性与天地材质的共鸣。
平衡:在时代与初心之间
正因如此,我自己的收藏非常“杂”。极致的青铜化玉器皿、精工细作的人物造像、传统的藏传玉器,我收;樊军民、王一卜、苗烈他们做的那些充满当代感、抽象写意的作品,我也收。
这既是出于爱玉之人的“博爱”之心,渴望体验不同的美感;也是一种审慎的平衡。更深层的原因,是我认可这个“扁担理论”——这两种极致,恰恰共同构成了当代玉雕最饱满、最真实的张力与面貌。
说到底,“技”与“意”从未分离,它们如同玉之双面,共同塑造着玉雕的生命力。
“极致炫技”,是文明的厚度与工艺的荣耀,它确定地告诉后人“我们能做到什么”;“相玉写意”,是思想的闪光与个体的温度,它不确定,却可能直击心灵,留下独特的时代印记。
作为藏家,我乐于拥抱这份复杂与多元。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许那些工艺登峰造极的物证会更稳固地沉淀下来,但那些真正闪耀着智慧与灵魂火花的写意之作,一旦被记住,便是永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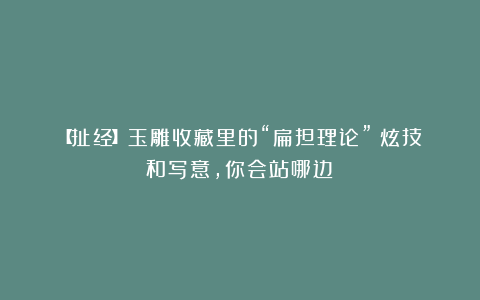
或许,这正是玩玉的乐趣所在——我们不仅在收藏物件,更是在参与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在确定与不确定之间,寻找美的共鸣,等待时光的答案。